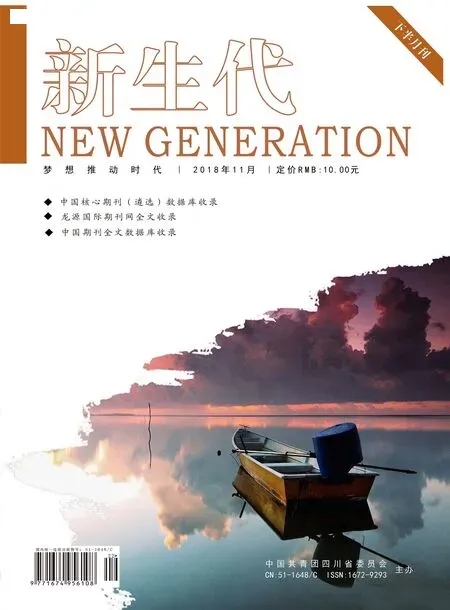“一張白紙”與塞拉斯對所予神話的批判
張兆 李偉 四川外國語大學 重慶市 400000
一、一張白紙
對“所予神話”的批判是塞拉斯哲學的主要內容之一。所謂“所予”,指的是某種通過非推論的方式獲得的東西;而“神話”,根據布蘭頓的解釋,就是“認為一切都可以內在地、自然地或必然地對這個領域有一個具體意謂,即不依靠它對其有那個意謂的人習得或利用概念。”[1]120所予的神話承諾了這樣一種存在:某種直接獲得的東西,我們不必預先學習語言、邏輯或是任何知識,就能知道它是什么,即使我們由于尚未學會語言而不知道如何命名或描述。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所予的神話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它只要出現,就可以作為某種確定的存在。
這個性質似乎很是平常,因為一個出現的、在場的存在,似乎就是確定的,實際不然。考慮這樣一件事,某人說,這是一張白紙。這時如果有人問,真的嗎?則第一個人該如何回答呢?也許他會說,當然是真的,我親眼所見,也許他還會把紙拿出來,讓持有疑問的人自己看一看。而這就是一種所予的神話:出示一個材料,同時,僅僅因為“這一材料被出示”,這個材料的內容就能夠被判斷為真或是為假。
這似乎是奇怪的。從常識上說,如果某人為某一命題出示證據,下一步應該是檢驗證據的真偽,以及這一證據在邏輯上是否支持原命題,這兩點都不能僅憑出示證據這一行為本身就得到滿足。我們不妨設想,當命題中的那張紙被出示后,可能出現兩個結果:其他人看到那張紙是白色的;其他人看到那張紙不是白色的,或是認為那根本不是一張紙。但這兩種結果都是可疑的。在第一種情況下,大家認同“這是一張白紙”,其原因是“看上去如此”。在第二種情況下,有人不同意“這是一張白紙”,其原因是“看上去并非如此”。兩個結論雖然截然相反,卻都是由于“看”這一行為做出的,而這正是證據被出示的過程——拿出證據給人看。也就是說,證據的真實性與邏輯性完全沒有得到檢驗,無論判斷為真或是為假,都僅僅是由于證據被出示這一行為就神奇地獲得了。正因為如此,倘若證據被出示后,有人承認它是一張白紙,有人不承認,但彼此的理由都是“親眼所見”,那么這里的對錯就無從判決了。
如此我們能夠得到結論,在這個事件中證據的被出示過程正是我們去看的過程,雖然這一過程是必須的,但判斷不應該只因這個過程而得出,我們必須遏制這種沖動,而這就意味著當證據被出示時,除了看一看,我們還必須額外做一些事情才能做出有效判斷,我們必須確認證據的真偽,以及分析這個證據能否支持原命題,但這兩點都不是只憑“看一看”就能做到的。
二、看到了什么
在尋找如何辨認證據的真偽以及確定所提供的證據能否支持原命題的方法之前,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一下“看一看”這個行為,目的是為了知道這一行為為何不能滿足以上兩個要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必須知道當我們去看這個被出示的證據——發言者提供的一張白紙時——時,我們到底看到了什么。
由于考慮到這張紙的顏色以及被拿出的究竟是不是一張紙都還有待確定,因此只能說,觀察者看到了具有某種顏色的某個物體。然而我們能否以此認定觀察者看到的是物體本身,或者說是客觀存在的一個事實?傳統經驗論反對這種觀點,理由是一個人所能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覺,而不是外在的物體。一個更為常識性的理由是,如果兩個人同時看到了一個物體,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則我們不能說兩個人看到的是不同物體,而必須說兩個人通過對同一物體的觀察得到了不同的結果。正是由于觀察同一物體卻得到不同結果是可能的,則觀察的結果就不會等于被觀察的物體。
那么,如果觀察者看到的并不是事實,或是不能被當做事實,就只能是某一時刻出現于內心中的某種影像,或者稱為殊相,至少傳統經驗論是這么認為的。但塞拉斯對此表示困惑,因為如果感覺到的內容僅僅是殊相而非事實,感覺內容就不能成為非推論的信念,更不能進而作為知識的基礎,他將這一矛盾的現狀——感覺材料需要同時滿足“殊相”與“事實”兩個性質——稱之為“感覺材料的含糊之處”。在此,本文無意直接討論感覺材料能否作為一般知識的基礎,而是要搞清楚殊相為何不能作為非推論的信念:顯然,“這張紙是白色的”就是一個非推論的信念,如果殊相不能轉化為信念,這個命題又從何而來呢?
問題在于,盡管殊相是某種獨一無二的內在片段,“白紙”卻是某種為數眾多的存在——塞拉斯稱為“可重復項”,那么我們如何能夠聲稱某個殊相是可重復項——“白紙”呢?對于同一張白紙P,根據不同的時間,我們可以獲得殊相P1、P2、P3……對于不同的白色紙張,我們又有殊相Q、R、S……我們如何得知這些殊相全都相等或相似,可以統稱為白紙?又或者,如果“白紙”是某人為歸屬自己的眾多殊相所設計的一個分類,他如何覺知到這種分類,以及如何確定別人不會按照不同的分類來歸屬這些殊相呢?所予的神話將第一個問題略過,又認為第二個問題根本沒有答案,因為這一神話考慮的并不是作為可重復項的多個并列的殊相,而是單一殊相和更高一級的屬的關系,即“覺知某些分類……是‘直接經驗’的一個原始的、毫無疑問的特征”[1]47。然而這并不是毫無疑問的,否則隨意給出一只動物,我們就應該能一眼認出它屬于什么屬什么種。但是顯然,除非我們事先具備了生物學知識,我們并不能一眼識別動物,那我們又憑什么認為自己可以在不具備背景知識的前提下一眼識別某個殊相呢?
現在,如果我們能夠承認將一種非推論且不必預設任何需要習得的知識的殊相先天地歸為一個特定的可重復項是難以成立的話,則我們縱然可以獲得某些殊相,卻并不可能說出這些殊相都是什么。這不僅是由于我們或許還未習得這些分類的名稱,更是由于對可重復項的覺知不可能只因殊相的出現就能獲得。所予的神話要求只要殊相得以出現,它“是什么”就是完全自明的,但這就是在說我們能夠僅僅憑借觀察就能搞清楚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切內容,剩下的僅僅是按照經濟原則的整理和歸類,可事實遠非如此。不如說,如果沒有預先學習的語言和知識,只是看,我們什么也看不懂。
三、感覺片段的真與假
傳統經驗論不承認可能為假的感覺片段,其理由是笛卡爾式的:雖然我對于我所看到的一切可能判斷錯誤,但我看到的東西對我來說是不會錯的。比如夢境,雖然夢境中的一切都不存在,但“我做夢”這件事是不會出錯的。如果我夢到太陽從西邊升起,那么“我夢到太陽從西邊升起”就是絕對為真的命題,不論“太陽從西邊升起”是不是假的。
塞拉斯對此表示了質疑,只是并未展開,他說:“如果說一個經驗真實是有意義的,那么說它不真實相應也一定是有意義的。”[1]20那么,可否存在某種情況,令“我夢到太陽從西邊升起”這句話也是假的呢?答案只能是我并未夢到。傳統經驗論認為,只要我是誠實的,則一旦我說出“我夢到太陽從西邊升起”這句話,它就不能為假(這仍是所予神話的典型形式)。但很明顯,如果我“搞錯了”,則縱使我是誠實的,這句話仍然可以是假的。問題是,夢境姑且不論,我們可能搞錯自己的感覺嗎?可否有這種情況:我感覺我在疼,實際沒有呢?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不論我的神經是否正在受到某種強烈刺激,我感覺我在疼,我就是在疼。但是否我對感覺的分辨可能出現錯誤呢?也許我只是在癢,而我誤當做疼?從概念上,癢和疼當然是有區別的,就像藍和綠是有區別的一樣。而這就會產生一個問題:我現在的感覺到底是哪一個——癢還是疼;或是眼前的顏色到底是哪一種——藍還是綠。既然我們有可能弄錯后者,我們就沒有理由否認我們不能弄錯前者,只是很難有人可以提醒我們這一點。但回過頭來,我們真的能認清我們搞錯了藍和綠嗎?
塞拉斯為此虛構了一篇精彩的歷史小說,某個叫約翰的人在一家領帶商店工作,夜幕降臨,店內由于尚未安裝電燈而光線昏暗,街道上卻燈火通明,這樣就會出現同一條領帶在昏暗的室內和在明亮的路燈下呈現完全不同的顏色的情況,比如在室內看它是綠的,在路燈下卻是藍的。現在,當一個顧客向約翰指明這點之后,約翰陷入了迷惑,因為他難以判斷這條領帶究竟是藍色的還是綠色的,他會對下一個顧客宣稱這是一條藍領帶——這是領帶在白天和在路燈下的顏色,雖然當約翰身處昏暗的店內時,在他的眼里,領帶仍然是綠色的。
經驗論者或許會反駁:既然約翰看到了綠色的領帶,他就獲得了一個綠領帶的殊相,至于他必須將這條領帶說成是藍色的完全是另一回事,這是一個“推論的結論”。這一點塞拉斯也予以承認,但問題是既然如此,約翰又為什么要將這條領帶說成是藍色的,而不是繼續報告自己的感覺?或許我們可以說,約翰知道自己的感覺錯了,他雖然看到了一條綠領帶,但他不信任自己獲得的這一殊相——他獲得它,但同時否定它。又或許我們可以說,約翰意識到綠領帶的殊相是與店內昏暗的燈光聯系在一起的,但在除此之外的“標準情況”下,即光線充足的條件下,這條領帶是藍色的。在故事的后續部分,約翰學會了一種更為聰明的報告方式:“它看上去是綠的,不過,把它拿到外面看一看。”[1]31
塞拉斯試圖通過這個例子證明,那種稱之為“看上去”的表達方式和“是什么”一樣,都是一種報告,前者并不比后者更為基本,其區別在于“看上去”的報告的抑制了承認其報告為真的傾向,或者說,抑制了某種承諾。這是一種巧妙的方法:一個連報告者本人都對其真實性有所保留的報告是不可能作為任何知識的基礎的。不過本文無意討論知識的基礎,在此只需引入報告者可以不承認自己的報告內容這一點就夠了。
如果報告者可以懷疑自己報告的真實性而有所保留,他當然也可以判斷自己的報告內容為假,只要給出足夠的證據。這與如下的心理并不矛盾:在獲得足夠證據之前,雖然有所保留,但報告者更傾向于認為自己的報告為真(否則他就不會如此報告)。塞拉斯試圖表明,獲得一個感覺材料,與認可這個感覺材料完全可以是兩碼事。當一個人認可他的感覺時,他會直接說“S是P”;當一個人雖然獲得了感覺材料但并不認可時,他會說“S看上去是P”——給出一個報告,但是沒有給予認可。這樣一來,感覺片段就是有真假之分的,因為感覺片段的獲得與判斷是完全分開的,而真假對錯是判斷的結果,并非感覺的結果。即使我們不能選擇自己所獲得的感覺,但我們能夠認可或不認可它。因此,當傳統經驗論者試圖通過約翰畢竟獲得了一個綠領帶的殊相而堅持自己的主張時,他們忽視了一個本該被視為不可思議的事實:約翰竟然能夠說出“這條領帶是藍色的”,其原因不是妥協與謊言,而是推論。這就意味著約翰“可以”通過推論否定自己所獲得的殊相。
四、使感覺成為命題
追問感覺材料提供的論據能否支持原命題,實際是在追問感覺材料與命題究竟處于何種關系。如果我們只是將命題當做一個假言句,比如“S是P為真,當且僅當X”,那么我們就需要追問感覺材料與X的關系,但我看不出這比直接追問感覺材料與“S是P”的關系好在哪里。問題在于感覺材料是非命題形式的內在片段,因此不論我們對原命題如何變形,我們都將面臨一個非命題形式的感覺材料與分析命題之間的關系。
傳統經驗論對于知識的關系有這樣一幅圖畫:
物理對象—1→感覺到感覺內容—2→非推論的信念—3→推論的信念[1]103
我們知道,關系1是一種生理學因果論,關系3是邏輯學推論,問題在于關系2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所予的神話,一旦出現一個感覺片段,就會自動生成一個非推論的信念,也就是說,只要去看,我們就能知道我們看的是什么,即使我們由于知識的欠缺叫不上名字,但也僅僅是叫不上名字而已。所予的神話在實際上否定了關系2的存在,暗示著由于某種神奇的力量,感覺內容先天就對應著一個非推論的信念,這最終使我們無從判斷在某一具體的事例中從感覺材料到非推論信念的過渡是否正確,要么盲目地相信,要么盲目地懷疑。
為考察從感覺材料到某一命題的轉變是否正當,我們首先要考察這一轉變是如何進行的。文本在前面提到,如果我們將觀察一張白紙所得到的內在片段視為殊相,則由于這一殊相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必須是無名的,雖然我們可以稱之為殊相P,卻不可以稱之為白紙,因為后者是一個可重復項。因此“白紙”這一概念既非由殊相產生,也非由殊相組成,它是“外來的”,是通過對語言和一般知識的學習得來的。因此從語言上說,“這是一張白紙”更毋寧是對“白紙”這一語詞的一次使用,它與感覺材料之間的關系是否正當取決于報告者對語言的使用是否正確。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指明使用語言的意義——它仍需聯結感覺經驗,用以表明那里有一張白紙,而非為了使用而使用。
必須注意,要想在感覺材料與命題之間不引入殊相之外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不想使用“白紙”一詞,也不想使用任何可以直接指稱相當于“白紙”一詞的所指的語詞,則我們固然可以做到,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具有光亮顏色的長方形纖維制品”,或是“這是一個用于書寫的材質”等等,但在實際上,我們是通過引入更多的非殊相的概念來避免“白紙”一詞的使用。因此,除非我們打算通過語言的實際使用來總結“白紙”一詞的意義,否則刻意回避這個概念以試圖表明我們可以不通過外來概念描述殊相只能是徒勞。既然如此,我們不妨直接使用“白紙”一詞。
這樣我們就引入了“白紙”這個單詞(即使我們并未追問這個單詞的來由)。事實上,同時被引入的還有“這”、“是”、“一張”,這幾個概念哪個也不是殊相本身就能提供的。在我們引入這些概念的同時,我們將這些概念指向某些思想——因為它們并沒有指向殊相,一個可重復項的概念的所指只能是可重復項。根據(后來才標注在字典中的)定義,某一殊相可以歸在“白紙”這一可重復項之下,作為“白紙”一詞的正確使用的一個范例。這樣一來,通過這些可重復項的使用,我們組織起了命題,只是需要注意,這些可重復項的所指并非某個殊相。
為了探明我們究竟如何將“白紙”與某一特定的殊相進行關聯,塞拉斯重新定義了“印象”這一概念。在他看來,印象不是殊相,而是將殊相的復制品用作一個模型,雖然從“實物”(這里僅僅做一個比喻)上說,當我們把一輛汽車的縮小比例的復制品用作模型時,這個復制品的實物就是那個模型的實物,但模型是具有意義的,這一意義由主體提供。因此是復制品在感知者內發生,而非感知者感知到復制品。換而言之,塞拉斯將印象理解為一個理論實體,它是主體的一種狀態,而非殊相。
在此之后,塞拉斯設計了一個“瓊斯的神話”:一個名叫瓊斯的行為主義者將這種作為內在狀態的印象視為外顯語言的原因,并將這種語言傳授他人。但在這一過程中,瓊斯卻將作為內在狀態的印象視為殊相,最終導致了所予的神話。
五、所予的神話與塞拉斯
所予神話具有以下三個特征:“每一個事實被非推論地認識到;不預設其他知識;這個結構中關于事實的非推論知識構成所有關于世界的事實斷言申訴的最終法庭。”[1]56三個特征中,塞拉斯“只是不贊同這個解釋的一小部分”[1]120,即第二個特征。具體來說,塞拉斯可以允許一種非推論的內在片段,無論是作為印象還是作為思想;他也允許其它知識將這種非推論的內在片段作為依據;但他認為這些片段一樣需要以其他知識為依據。換而言之,推論的知識與非推論的知識是互為依據的,因而并不存在一個認識上的基礎。
我們很難判斷塞拉斯畢竟保留了非推論的知識是否正確,以及他對傳統經驗論與基礎主義的批判是否還不夠徹底。根據塞拉斯的說法,如果存在推論的知識,就一定存在非推論的知識,但這個斷言是在承認“推論的知識”與“非推論的知識”的區分的基礎上才能成立的。這個區分現在是存在的,但其合理性卻有待證明,如果我們能夠認為這一區分并不必要,那么也就無所謂非要引入一個“非推論的知識”。而事實上,塞拉斯對所予神話的批判已經顛覆了非推論知識的基礎地位,問題是在這一地位被顛覆后,兩種知識的劃分還有多大意義呢?
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這是一張白紙。所予神話認為,要證明這一命題只需把白紙放在人們眼前,只憑這一行為就足以對這個命題完成證明。其內在邏輯是,感覺行為完全等同于感覺材料,而感覺材料又完全等同于一個非推論的命題,這中間沒有選擇、沒有歧義、沒有變數,因此感覺行為本身就足以產生一個非推論的命題:這張紙是不是白色的,只要看就知道了。
反之,如果我們認為所予神話的這個證明是無效的,我們就要承認這其中有選擇、有歧義、有變數。感覺行為不等于感覺材料,感覺材料既不是概念更不是命題,即使額外引入概念,則不僅概念的具體使用可以出現錯誤,連概念規范性的使用方法,按照奎因的理論,也是可以變化的。個人的意志在其中顯然發揮了作用,“這是一張白紙”并非所予。
現在我們重新審視這些環節。按照塞拉斯的主張,作為感覺材料,殊相是所予的,卻不能加以神化,我們可以認識到殊相與周圍環境之間的因果關系,就像約翰能意識到領帶在室內是綠的在路燈下是藍的。塞拉斯認為,當報告者意識到報告內容的權威性與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時,就會尋找一種“標準環境”,而在標準環境下的報告就是權威報告。但是顯然,并不存在一個先天的標準環境。約翰之所以會把路燈下當成標準環境,是因為他需要這么做,是因為我們需要戴領帶的場合幾乎都是光線充足的環境。因此在領帶的例子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權威性而只有適用性,假使約翰生活在一個光照較地球更弱一些的星球,則同樣的領帶在“標準環境”(已經變成了一種昏暗的環境)下的顏色就不會是藍色而是綠色了。這樣一來,如何選擇報告的內容就會等同于如何判斷所處的環境以及所應該適用的環境。做出正確判斷需要知識,報告者可能會犯錯誤,也可能因為思慮不夠周密導致偶然失誤,最重要的是,正是因為在對感覺材料的報告中存在著錯誤的可能,正確才是有意義的,也只有正確的材料才足以為命題作證。
在對感覺材料的判斷之后是引入可重復項的概念以及對概念的使用,或許按照塞拉斯的想法,對概念的使用可能還會排在引入概念之前。一個被所予神話揪住不放的不問題是:如果概念不從殊相中來,它又從何而來?對此塞拉斯并沒有給出清晰的回答,這或許是因為他認為這個問題在如下的理論中已經無關緊要:感覺材料的獲得和證成可以是不同時的。同理,概念的引入和證成也可以是不同時的。想想“原子”這個概念:它最初被提出時的意義和如今不斷被發現的性質天差地別。既然如此,一個感覺材料是怎樣獲得的,一個概念又是出于什么理由被引入的似乎并不重要,因為對其的合理性證明可以在引入概念之后不斷進行補充。
由于一個感覺材料或一個概念的出現與證成不必同時進行,因此在塞拉斯看來,一個概念可以既是推論的又是非推論的。說它是非推論的,是因為我們可以直接引入某個想象中的存在,比如德謨克利特所談的“原子”;說它是推論的,是因為我們也可以通過其它知識對某個概念進行證成,比如通過布朗運動證實分子的真實性。這樣,在承認了感覺材料是一種所予的前提下,塞拉斯拒絕將其視為一種神話。
至此塞拉斯對于所予神話的批判已經完成,本文也通過該理論順利解決了一個日常問題:如何證明這是否是一張白紙。答案是必須考慮殊相與觀察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對特定語言的理解和運用,只有在兩者都是正確的情況下,證明才能成立。然而全文尚有一處疑點:殊相與可重復項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在“瓊斯的神話”中 ,塞拉斯預先設定了一種“賴爾語”——“其基本描述語匯談及時空公共對象的公共屬性。”[1]74按照塞拉斯所言,即使賴爾語已經可以表達信念、欲望等等,卻不足以表達感覺材料和思想。塞拉斯繼而通過瓊斯的天才創造來解釋賴爾語向日常語言的轉變是怎樣做到的,但他并沒有追究賴爾語是怎樣做到的。確實,或許語言的出現、變化、流行中的各種表達方式等等偶然因素并不是哲學所要研究的內容,但在一個已經被使用的語言中,它所使用的詞匯與殊相究竟處在怎樣一種關系卻是值得追問的。傳統經驗論將“白紙”作為諸多有關白紙的殊相的抽象,塞拉斯的“心理學唯名論”卻將“白紙”作為某種可以存在于邏輯空間中的心理狀態。這是令人擔憂的:雖然為了避免所予的神話,意志必須在認識中承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這不等于這一角色必須以心理主義的方式承擔。如“權威性”、“標準環境”、“印象”等概念中暗示著令人不安的傾向,某種可以存在于邏輯空間的心理狀態雖然確實能夠被證明或證偽,也符合了塞拉斯有關知識的任何一個部分都可以被懷疑的主張,但這一切并不因此就是實際情況。塞拉斯的工作似乎是一種聰明的處理方法:既避免了重新設想殊相的性質,又破除了所予的神話——懷疑一處而保留大部分傳統。但如上文所言,在所予的神話被破除之后,對殊相的保留是否還有意義,或是將推論知識與非推論知識繼續做與傳統并無大異的區分是否還有意義,這都是需要額外思考的問題。或許從心理殊相到邏輯命題的過渡只能通過引入另一個心理維度作為中間項,但或許我們并不必須把最初獲得的感覺當做心理殊相。問題在于,如果這一切的起點真的只能是心理的、個人的,則主體間性所面臨的問題就應該遠比實際情況更為復雜。對所予神話的批判雖然在邏輯上成功了,在效果上還有待時日,但總歸還不夠真實。瓊斯的神話真的如塞拉斯所言就是“人類自己”嗎?這一點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