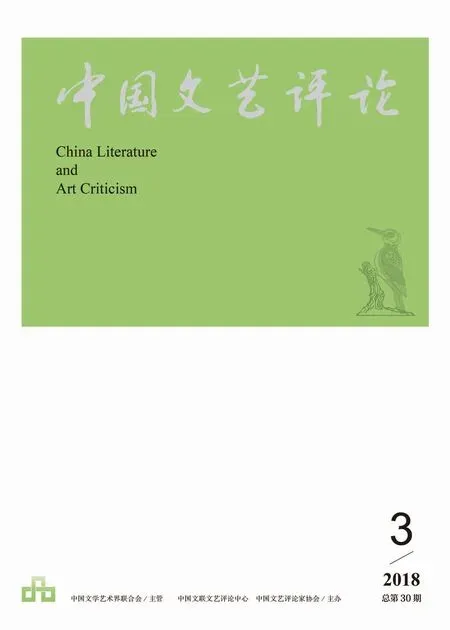“后理論”時代與文化詩學批評思潮的流變
陶永生
作為20世紀文藝理論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紀念事件和標志性思潮,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批評學派能夠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獨特的景觀表征出:人們曾如何蹣跚地走過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他們為后世留下了幾多可圈可點的痕跡,或濃墨重彩的印記、或痛徹心扉的遺憾,這其實也就是從直指本心、直達歷史深處的終極層面來觸摸、理解和捕捉人類精神發展的歷史。而任何一段精神的歷史,即便初始時還很微弱、渺小,甚至往往會無疾而終,倏忽而逝,但對于未來都將具有不可替代的定格和不可磨滅的價值。躬逢其盛,中國傳統“詩論”思想博采眾長、自我揚棄,同“無論是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闡釋語境,還是文化詩學(Cultural Poetics)批評視域”都生成了一系列的蘊涵交集與視域融通,從而為文化詩學整體形態平添了更多中國元素與中國氣派。
似乎再度呼應了“以全球為架構思考,以本土為關懷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流行語,當今世界的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多元文化競相迸發的繁榮格局,為不同區域兼容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雙重維度的“國別體”文化詩學批評形態同步粉墨登場準備了時代契機和資源優勢。尤其是進入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理論之后(After Theory,2003)》提出的“后理論”時代,落實在“通過比較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的方法論層面上,要實現這些異域及異質文化——包括作為文化范疇中的一種特殊構成的文學形態在內——之間的批評交流與商談溝通,就更需要我們去尋求它們之間的共通之處和共性所在,尋找它們之間平等對話和有效溝通的載體與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