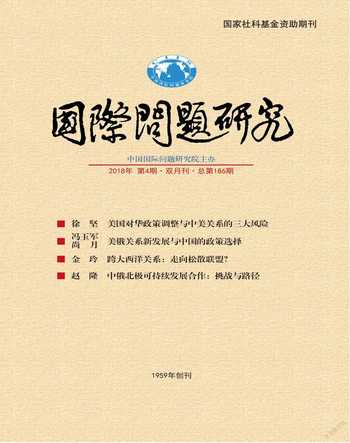跨大西洋關系:走向松散聯(lián)盟?
金玲
〔提要〕美歐關系當前表現(xiàn)出明顯的兩面性特征。一方面,特朗普上臺以來雙方圍繞安全、經(jīng)濟以及多邊主義等一系列問題的沖突反映了美歐的觀念和利益分化,矛盾具有內(nèi)生性特征;另一方面,維持雙方關系的支柱性基礎未根本動搖,雙邊關系仍具韌性。上述兩種特征的發(fā)展變化將左右美歐關系前景,跨大西洋傳統(tǒng)聯(lián)盟關系將日益走向松散的“議題聯(lián)盟”。松散聯(lián)盟狀態(tài)下,雙方的盟友關系將更多表現(xiàn)為“議題主導”,在不同議題領域?qū)⒊尸F(xiàn)沖突、競爭與合作的多面形態(tài)。
〔關鍵詞〕美歐矛盾、跨大西洋關系、議題聯(lián)盟
〔中圖分類號〕D8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2 8832(2018)4期0034-16
特朗普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引發(fā)美歐多領域矛盾,跨大西洋關系面臨自伊拉克戰(zhàn)爭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當前圍繞跨大西洋關系走向的核心辯論是:雙方圍繞全球化、安全合作等問題的沖突究竟是“特朗普現(xiàn)象”還是雙方的結(jié)構性矛盾所致。將沖突歸因于特朗普政策的觀點認為,跨大西洋關系中的安全依賴、經(jīng)濟依存、價值觀共享的結(jié)構性支柱沒有發(fā)生改變,“特朗普現(xiàn)象”具有臨時性特征。短期內(nèi)雙方雖有沖突,但在美國建制派力量的平衡下,“跨大西洋關系會維持原狀”,中長期亦不會發(fā)生質(zhì)的改變。[1]與之對應的觀點認為,“特朗普現(xiàn)象”是跨大西洋關系“惡化”的癥狀,在特朗普政府以前“美歐已疏離”,美歐矛盾具有結(jié)構性、內(nèi)生性和必然性的特征,是各自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以及安全利益日益分離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