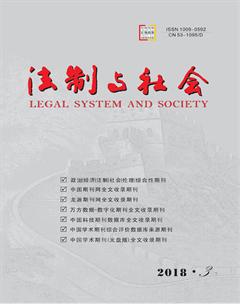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及其推廣
于青 趙書博
關鍵詞 治安管理 處罰標準 一般證明標準
作者簡介:于青,中國航發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部長,高級經濟師,研究方向:民商法;趙書博,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科員,研究方向:民商法、證據法。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3.311
一、問題引出:如何理解治安管理處罰的證明標準
2015年某天,王某與同村村民玩麻將,與旁觀者董某發生口角,口角過程中,王某受傷住院。后王某報警,但公安機關以“王某被毆打一案,沒有證據證實董某對王某進行毆打”為由,向雙方出具了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王某提出行政復議但被維持,遂就健康權糾紛提起侵權之訴。
經審理,法院認為董某毆打了王某的可能性更高,遂支持了王某大部分的訴訟請求。
為什么在本案中民事法官會作出與公安機關相反的事實認定?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95第(二)項的規定,公安機關作出不予處罰決定的情況有兩種:一是依法不予處罰;二是違法事實不能成立。其中,對違法事實不能成立的理解又分兩種情況:一是經公安機關調查核實,行為人確實未實施違法行為;二是公安機關未能搜集到足夠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違法行為。本案中,公安機關對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正是因為后者。
因公安機關未能搜集到足夠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違法行為而作出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人民法院是否亦應當認定行為人未實施侵權行為?筆者認為并不盡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30條對于行政處罰決定提出的一般要求是:“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簡言之,作出治安管理處罰的標準至少應當是“違法事實清楚”。
而在民事訴訟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確定了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是高度蓋然性,即“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相比之下,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顯然低于違法事實清楚的證明標準。雖然公安機關未能在較高的治安管理處罰證明標準之下證明董某毆打了王某,但在較低的民事訴訟證明標準中,承辦法官根據現有證據已經形成了董某很可能毆打了王某的內心確認。
本案引發的思考卻沒有停止:該如何看待公安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或不予處罰決定書的證明效力?如何理解治安管理處罰的證明標準?
二、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
(一)尋找一般證明標準
治安管理處罰的證明標準是指公安機關在治安管理處罰程序中利用證據證明違法案件實體性事實和程序性事實所要達到的程度。從法律文本角度來看,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條及《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上位法《行政處罰法》第4條第2款之規定,公安機關設定和實施治安管理處罰的標準可以被濃縮為“應當以事實為根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相當。”《行政處罰法》第30條從相反的角度還特意強調:“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
關于如何理解事實清楚,《行政處罰法》在簡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中又分別作出規定。對于簡易程序,其33條規定的標準是“違法事實確鑿”;對于一般程序,其36條規定的標準是“必須全面、客觀、公正地調查,收集有關證據”。從司法審查行政行為合法性角度來看,根據《行政訴訟法》第70條第(一)項之規定,主要證據不足時人民法院應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為。
根據上述法律文本來看,無論是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規定還是行政處罰一般規定,甚至是司法審查行政行為的一般規定,都是以事實為依據,要求違法事實清楚。因待證違法事實清楚與否根本上取決于相關證據是否充足,故落實到實際操作角度(證明角度)而言,違法事實清楚的證明標準意味著反映違法事實的主要證據要充足。
(二)反思一般證明標準
不可否認,“主要證據充足、違法事實清楚”的證明標準過于抽象。每一個人對于證據的證明力的感受都來自于其獨特的生活經驗與邏輯,這就注定每個人對“主要證據充足、違法事實清楚”證明標準理解無法一致。
目前有一種主流觀點對“主要證據充足、違法事實清楚”理解與法律文本字面意義不同。該觀點認為:“由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類型多樣化,與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相比,行政訴訟證據的證明標準也不是單一的,因此因具體行政行為性質的不同而應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行政案件證明標準的高低,原則上取決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對原告權益影響的大小。”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錯誤的適用了比例原則,證明標準高低與否并不在“比例”之列,用比例原則的思想來解釋對當事人權益影響大小的治安管理處罰措施與證明標準高低之間的內在聯系未能切中“關鍵要害”。而且,《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8條、第75條即為“證明標準高低與具體行政行為對行政相對人權益影響的大小正相關”的典型反例。
但是,為什么我們總能實在感受到公安機關做出對原告權益影響大的治安管理處罰時,所承擔的證明責任更重?完成證明更加困難?筆者認為,提高證明標準固然會增加證明難度,但增加待證法律要件事實數量,也同樣會增加證明難度,簡言之,證明責任更重或完成證明更加困難的主觀感受并非源自更高的證明標準,而是更多的待證事實。因為公安機關幾乎對《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涉及治安管理處罰的每一個法律要件事實都要予以證明,但是對當事人權益影響較大的治安管理處罰方式(如行政拘留10-15日)所涉及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條文中往往包含多個法律要件事實,因此公安機關面臨的待證事實同樣也是多個,證明難度相對較高;而對原告權益影響較小的治安管理處罰方式(如警告)所涉及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條文中往往僅有單一法律要件事實,公安機關面臨的待證事實相應也只有一個,證明難度相對較低。
(三)確認一般證明標準
由此觀之,詬病“主要證據充足、違法事實清楚”的證明標準過于機械、不靈活,進而提出“以治安管理處罰行為對原告權益影響的大小為原則構建相適應的治安管理處罰證明標準體系”的改良方案,不僅突破了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原則性或總則性規定,對治安管理處罰證明標準做了越權解釋,也未找準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過于籠統、較難適用的癥結所在。
另外,從立法技術上來說,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客觀上只能是抽象式或概括式的表述,難以全面反映出各類治安管理處罰證明標準的所有特征。這都提示我們直接或以治安管理處罰行為對原告權益影響的大小去解釋“主要證據充足、違法事實清楚”是行不通的。
其實不同類型、性質的待證法律要件事實才是檢驗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的試金石。只有將證明標準與具體的待證事實聯系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細化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并在不同條文中對比感受出“主要證據充足、違法事實清楚”的具體意義。筆者認為應該跳出探討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到底應該如何理解,其證明標準有多高的怪圈,將視線轉向如何將一般證明標準推廣到《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三章54個條文(自第23條至第76條)中去。
三、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之推廣
(一)定罰證明標準之推廣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三章分別從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妨害社會管理四個方面用了54個條文(自第23條至第76條)規定了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模式、行為后果和處罰方式。
從行為模式來說,只要行為人作出一定的行為而不要求產生具體后果即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條款有41條。公安機關擬對行為人定罰時,其核心待證事實為行為人是否實施了相應的違法行為,應充足收集行為人是否實施了所涉違法行為的相應證據。
以違法行為+發生實害后果為處罰前提的條文有12條,公安機關擬對行為人定罰時,其核心待證事實為行為人是否實施了相應的違法行為、發生的實際損害結果以及其中的因果關系,公安機關應充分收集上述證據。因此綜合對比來看,此類定罰的證明要求和難度明顯要高。
(二)量罰證明標準之推廣
在治安管理處罰中,除了定罰之外還有量罰的問題需要解決。涉及治安管理處罰的全部條文,幾乎都需要考慮違法行為是否惡劣,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嚴重等影響量罰輕重的情節問題。因此情節事實亦是公安機關需要證明的一項待證事實,只是情節事實較之于違法行為、發生的實際損害結果以及其中的因果關系而言屬于次要待證事實,證明要求更模糊,更依賴于基于經驗的價值評價。
四、結語
關于證明標準的探討歷久彌新,本文嘗試以證明標準與待證事實特性關系為中心,以《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為文本,以法律要件事實性質、理解方式、價值判斷三重因素為研究進路,探討治安管理處罰的一般證明標準及其推廣適用,旨在說明不同待證事實之上的證明標準如何形成,增強不同領域執法辦案人員對治安管理處罰證明標準的認識,促成治安案件中公安機關獲取的證據向其他類似訴訟合法轉換。民事審判中遇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當注意從《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法律要件事實性質、理解方式、價值判斷角度綜合判斷其證據意義。
參考文獻:
[1]晏山嶸.行政處罰實務與判例釋解.法律出版社.2016.
[2]李國光.努力開創行政審判工作新局面,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