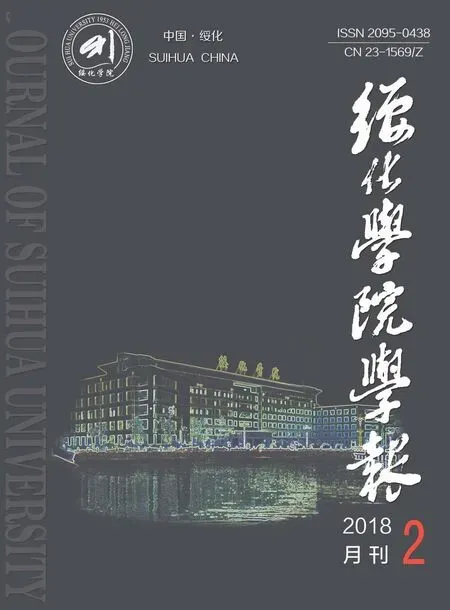展滿族文學風采 傳清代社會文化
——評《語言文化視域下的子弟書研究》
周忠元
(臨沂大學文學院 山東臨沂 276012)
王美雨的《語言文化視域下的子弟書研究》以現有公開出版的子弟書為語料,在對子弟書起源、作者以及研究現狀做出詳細論述的基礎上,從語言文化的角度出發,對子弟書中的滿族男性形象、女性形象、服飾文化、飲食文化、社會風俗百態、百工行業文化及俗語等內容進行了詳細而全面的研究,最終建構了語言文化視域下的相對完整、隸屬于子弟書的清代中后期文化世界。
一、文化的視野,細膩的筆觸
就目前可見文獻而言,對子弟書進行研究的最早成果,可以說是李鏞(1797)在顧琳的《書詞緒論》中所提及聽聞子弟書的時間和地點。據此,我們可以說子弟書的研究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兩個多世紀以來,學界既有對子弟書的文本內容、語言模式、藝術價值、文化內容的研究,也不乏從語言本體出發對其進行研究的成果。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鮮有從語言文化的角度出發對子弟書進行研究者,這種缺憾恰恰為王美雨從語言文化的角度對子弟書進行研究提供了契機。
語言是為了滿足人們的交際需要而產生,任何一個語言符號甚至是語法規則的產生都與人們的心理需求密切相關,同時也反映了其產生時代人們的文化心理,具體而言,“語言和文化水乳交融,任何一個詞語、語法結構甚至是語音的選擇都體現了一定的文化現象,從小的方面講,體現了一個人的文化心理;從大的方面的講,體現了一個地域、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因此,要研究好語言,需要注意語言背后的這種文化現象;要研究好文化,同樣也要注意負載這種文化的語言”[1]。即是說,身為滿族人,子弟書作者想要準確地使用漢語進行文學創作并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選擇漢語詞語時比起漢族人更為慎重,這也是子弟書作者多使用漢語方言詞語進行創作的原因。這種選擇,使得書中有了大量的反映當時京津一代地域文化的詞語。所以,王美雨在研究子弟書中的文化現象時,注意從語言角度出發,闡釋詞語背后的文化現象,如在研究子弟書中所涉及的服飾文化現象時,她先是將其分為男子服飾文化和女性服飾文化兩種,做了全面的論述;后從面到點,從服飾文化詞的角度,對子弟書中的“主腰”“套褲”“草上霜”“褂襕”“汗褟”“蝴蝶夢”“困秋”“涼帽”“高底鞋”“靴掖”“鞋拔”等做 了個體研究,建構了獨屬于子弟書的服飾文化世界,即是說子弟書對我們了解清代當時的“民俗,大眾的審美趨向都提供了一定的材料”[2]。
王美雨以女性獨有的細膩情懷,從子弟書中出現的顏色詞解讀出了作者的心理世界,她認為子弟書中的景色描寫所用顏色詞,看似是在描寫自然景色,卻是每種顏色都蘊含著作者獨特的審美意識及篇中人物無法直訴的情感。子弟書作者樂用顏色詞,與滿族原為游牧民族的特質密切相關,游牧民族對大自然中的一切較之于農耕民族更為敏感,也更能把握自然界相似景物的不同,更能準確地用顏色詞將自然景色的細微差別予以呈現。子弟書作者使用顏色詞不僅僅只是描寫自然景色或者人物的服飾,他們能夠將顏色詞和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及人物心理等完美地進行結合,將顏色詞所體現的文化意蘊做出了深度的闡釋,使得子弟書中的顏色詞具有了獨特的生命力。
子弟書作者除樂用漢語方言詞語以及富有典型文化特征的通用漢語詞語進行創作外,同時善用漢語俗語,眾所周知,俗語根植于民族、地域,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蘊,它為本民族、本地域的人所精通。離開民族、地域去談俗語,很多時候會給人一種不知其所云的感覺。故子弟書作者身為滿族人,能夠在子弟書中熟練地使用漢族的俗語,既顯示出他們在語言學習方面的天賦,也顯示出在當時滿漢文化的沖突、融合過程中,滿漢語言和文化的融合與妥協。在《語言文化視域下的子弟書研究》中,王美雨以子弟書中大量的俗語語料為基礎,注重對其文化內涵的揭示,為研究者了解清代中后期滿族人的文化心理以及社會流行的俗語提供了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活人眼里下白蚱”“擲報子”“裝在套褲里攄殺”“口外的姑娘騎駱駝”“人來二拍風”“紙錢兒樣的朋友,到底薄啦”等地域特征明顯的俗語的研究,對今人了解這些基本已退出歷史舞臺或即將推出歷史舞臺的俗語提供了幫助,也為保存這些文化意蘊深厚的俗語做出了學術研究角度的貢獻。
二、研究內容全面,典型性突出
清代中后期的滿族人入關已久,對關內文化已經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無所事事的他們,為了尋找苦悶精神的宣泄口,并重新獲得一種充滿生機、別具一格的藝術享受,他們別出心裁地創作了說唱文學子弟書,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但采用了為關內人們所熟悉的北方十三韻轍和京津一代的方言詞語構建子弟書語言,而且注意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最終成就了語言和藝術價值都極高的一種藝術形式,正如邱志紅所言子弟書“雖然是在八旗子弟手中創造起來的文學藝術,但觀察其創作主體、語言形式以及表現內容,可以發現‘子弟書’既不是滿洲人獨有的藝術活動,也不是完全浸潤于漢文化、被漢化了的文化形式,而是以漢文化為主體、滿文化為主導、滿漢文化相互交融但又保存有各自文化特征痕跡的產物”。[3]雖然語言和文化不可分,但是掌握了語言不代表能掌握其所代表的文化,也不代表作者在書中就一定要反映漢族文化,這一點也可以從子弟書中除改編自元雜劇、漢族傳統小說及戲曲等篇目中涉及到漢族男性、女性外,原創篇目中很少涉及到漢族男性、女性的事實中看出。上文已指出,子弟書作者創作子弟書的主要原因在于尋找傾瀉苦悶精神的通道,如果說改編漢族以往作品是為了迎合市場需要,那么原創的作品則主要是為了通過描述旗人的生活現狀和精神感受來為自己的精神尋找一個隱秘的傾瀉通道。王美雨在研究中充分地注意到了這一點,她注重從全面的角度出發,力求對子弟書中的文化現象做出語言文化角度的研究,但又著重對其中的滿族男性形象和滿族女性形象進行了研究,并通過對這兩類人物的研究,延伸到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及俗語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一種既全面又不失典型的研究模式。
三、豐滿滿族文學價值,具有現實性
滿族在入關之前,其文學以說部為主、崇尚神化、信封薩滿教,帶有游牧民族的鮮明特征。入關之后,受關內傳統文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逐漸加大,形成了一種早期以滿語為主后期以漢語為主的文學語言模式,內容則是以滿漢文化兼有為特征,即是說入關之后的滿族文學既有漢族文學的影子,又不失其為滿族文學的特征,我們可以說滿族文學“是滿族本身歷史生活、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面鏡子,是一部形象化、藝術化的清代滿族歷史”[4]。就子弟書而言,其特征更加鮮明,“從民俗角度看,子弟書作者多為京城八旗子弟,因而其描寫不自覺地帶有滿族風情;從通俗文化角度講,因子弟書多寫京城市井人物的生活,因而又帶有濃郁的市井風情”[5]。由此,從語言文化的角度對子弟書進行研究,無疑為豐滿滿族文化的價值、挖掘清代滿族人眼中清代中后期的社會文化、語言文化等提供了幫助。當前的傳統文化建設、中華夢的建設中所強調的文化傳承,不是只包括對漢族經典文獻中所記錄文化的傳承,還包括對各少數民族文學中優秀文化的繼承。歷史不能復制、社會建設包括人們的心理狀態也不能復制,在這種狀態下,對優秀的文化作品進行研究,系聯現實文化,通古貫今,在體現這些文化作品價值的同時,也能夠使得優秀的傳統文化為今世所用,進而使得對傳統文獻作品的研究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橫看成嶺側成峰”,同樣的內容,不同的人去進行研究所得必定各不相同,子弟書作為文學價值、語言價值及文化價值極高的滿族說唱文學,內蘊極其豐富,王美雨選取從語言文化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審慎地解讀語言所代表的文化現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可以算是為子弟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隨著更多子弟書篇目的發現以及學界對它的逐漸重視,子弟書的研究必定會走上新的高度,而王美雨對子弟書的研究也可以更加全面、深化,繼續為學界及普通人了解清代滿族說唱文學子弟書、透視清代滿族作家視野中國的清代社會及民俗文化等提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1]王美雨.語言文化視域下的子弟書研究·前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2.
[2]王美雨.車王府藏子弟書方言詞語及滿語詞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15.
[3]邱志紅.從“子弟書”看嘉道時期滿漢文化關系[C].//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清代滿漢關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643.
[4]董文成.清代滿族文學史論[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41.
[5]崔蘊華.書齋與書坊之間——清代子弟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