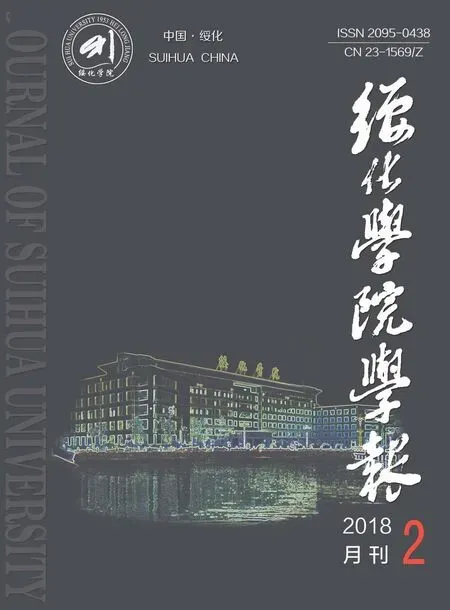試析毛姆《尋歡作樂》中創作的審美情趣
彭 禹
(湖南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 湖南湘潭 411101)
與不斷攀升的讀者人氣指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英國作家毛姆始終徘徊在西方批評視野的邊緣地帶,其作品離所謂的“經典”似乎隔著一步之遙。毛姆的小說深受讀者喜愛,絕非一部“膚淺”作品所能達到。作為一名職業作家,毛姆毋庸置疑善于投讀者之所好,精于編排故事情節,再輔以幽默簡潔的敘事方式,他的作品便吸引了大批讀者。然而,正如其作品的推崇者德萊塞(Dreiser)所言,毛姆的小說引人入勝之處著重在于一種“對信仰的尋求”[1]。那么,在《尋歡作樂》這部小說中,作者揭露了怎樣的人情世態?作者筆下嘲諷的文人圈子象征著何種時代風貌?通過對比、諷刺的寫作手法,作者做出了何種反思?又抱有何種堅定的藝術信仰呢?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這部作品。通過《尋歡作樂》,毛姆對當時商品化的文學市場虛偽的一面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時,也表達了他對文學創作的反思以及藝術中真善美的理解和詮釋。透過小說文本幽默詼諧的敘述表層,展現的是作者對藝術創作及人性美的深層探索與思考。
一、商品化的文學社會
《尋歡作樂》講述了維多利亞時代末期一位虛構的“天才”作家德里菲爾德的創作以及成名歷程。故事從羅伊準備為這位時代“最偉大”的作家寫傳記開篇。受作家第二任太太埃米的邀請,他打算為已故的德里菲爾德充滿和諧和美的一生作傳。為了投合讀者的心理,滿足他們心中所期待的完美作家形象,羅伊試圖忽視兩個事實。一是德里菲爾德的第一任太太羅西對她丈夫創作的成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二是作家在晚年時生活邋遢、酗酒、不愛衛生,這些與其儀表堂皇的公眾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羅伊看來,要想追求藝術的和諧美,就必須舍棄這些不調諧之音;而要追求藝術的真實性,又無法扭曲事實。此處,對這兩個細節的處理體現出作者毛姆對創作真實性這一要素的思考。在商品化的社會中,市場需求成了主導因素,文學社會也不例外。
同時,不難發現,德里菲爾德晚年聲名鵲起并非因其作品蘊含著美或詩意的描寫,而是與文學“經紀人”特拉福德太太的營銷策略密不可分。后者以文學評論家自居,卻熟諳市場運作模式,更懂得如何打造一位令人喜愛和尊重的文學大師形象。文學的審美標準不是基于客觀事實,即作品本身的美,而是受到了一系列主觀的、外在的因素影響,那么這種審美標準背后的審美情趣必是發生了嚴重的偏離。康德曾對審美的本質進行過界定,他認為審美是“非功利而生愉快”[2](P377)。然而,在《尋歡作樂》中,文學作品的創作和評論都顯著地打上了功利的印記。
純樸、自然和真實的狀態,是藝術活力和想象力得以集中展現的必備條件。正因為對故鄉的熟悉和熱愛,黑馬廄鎮的生活構成了德里菲爾德早期作品中的重要主題,在這些作品中他的思想和情感也獲得了最充分地自由表達。故事敘述者多次強調這位偉大作家的早期作品之所以成功離不開他的第一任妻子羅西的影響。在率性真誠的妻子陪伴下,德里菲爾德在黑馬廄鎮度過了人生中一段最自由快樂的時光。妻子的熱情和活力給他的小說注入了靈感,為其提供了創作素材。可是當他們搬到倫敦后,生活居家方面雖更顯精致富足,但是城市里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和充滿功利的思想卻禁錮了他的創作,遏制了其想象力和創造力。當他逐漸融入倫敦的文學圈,名聲越來越顯赫,還贏得了特拉福德太太的青睞和提攜時,德里菲爾德卻再也沒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在失去了羅西之后,他創作的源泉和激情便不復存在了。敘述者評論道,雖然德里菲爾德的后期作品具有一種含蓄的美和古典式的嚴謹,但它們缺乏早期作品當中的“風味、活力和喧鬧的生活氣息”[3](P126)。
二、文學創作中的真實性
“生活氣息”是激發藝術美的活力所在。小說中,羅西才是真正具有這種生活氣息的代表,她總是竭力為家庭的日常生活增添自然的美和活力。這首先體現在家居擺設上。羅西喜歡給窗簾配上流蘇和花飾,挑選金色的家具,使整個房間充滿了色彩。室內還擺放著瓷器、木雕、印度銅器,以及畫著峽谷、雄鹿、游獵場面的大幅油畫,使家里蕩漾著異域風情和與自然親近的和諧之聲。每星期六下午作家在家中舉辦茶會,款待客人。茶會上羅西真誠爽朗的笑聲沁人心脾,使客人們不由自主地卸下了平日里的“面具”,由衷地感受到了輕松自在。不妨說,羅西精心營造的富有生活氣息的美剛好印證了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瑟斯通教授所提出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念[4]。審美場所不再僅僅局限于藝術館、博物館等藝術成果的聚集地,而是囊括進家裝擺設、待人會客的私人空間。由此,審美的理念也浸潤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羅西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她有著一頭閃著銀光的金發和泛出金光的銀白色皮膚,再加上迷人的微笑,她仿佛和“黎明一樣純潔”。小說里仰慕羅西的人當中有名叫希利爾的畫家,他曾為羅西畫過一幅肖像畫,作畫前他便一語中的地指出,羅西獨特之處在于“她的色彩”,并把它稱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奇跡”[3](P157)。她即像“青春女神”,又像“一朵白玫瑰”[3](P224)。羅西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脾氣溫和,慷慨大方。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有句名詩“真即是美,美亦即真”。羅西用真實為我們詮釋了美的深刻內涵。她的舉手投足、待人接物無不體現出其質樸、真誠的美好心靈。羅西與人交往自然率性,從不扭捏作態,說話時口氣總是很熱切,仿佛孩子般地洋溢著對生活的熱情,同時她的眼睛總是流露出迷人的、天真無邪的笑意,這些品質使得每個與她交往的人都感到安心自在、輕松愉悅。盡管她和德里菲爾德的物質生活并不富有,但羅西竭盡全力為生活營造出歡快的氣氛,她的真誠和熱情感染到身邊的每一個人,使他們內心充滿了幸福感。
羅西衣著簡樸,不愛濃妝艷抹,在特拉福德太太的眼中,她是個粗俗的鄉下女子,但在敘述者眼中,這種“俗氣”卻蘊含著一股真性情。然而這種率真隨性的性格也易導致其他人的負面評價。因與喬治勛爵、希利爾等人交往過密,她被認為是個粗俗、道德敗壞的女人。羅西的行為可能僭越了婚姻的倫理綱常,但無法忽視的是她看待這種人際關系時真摯誠懇的心態。她追求的并非是金錢利益,而是期望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努力為別人帶來最大的幸福和快樂。敘述者不禁如此描述她給人的感覺,仿佛“太陽發出熱量、鮮花發出芳香一樣的自然”[3](P226)。
藝術的真實同樣需要接受道德的評判。不可否認,羅西與喬治勛爵的私奔違背了婚姻的倫理道德,但如果讀者了解了她的隱衷,換個角度看,她又是一個值得同情的生活不幸者。羅西在幼小的女兒被病魔奪去生命之際,感受到了人間的孤寂和漠然,體會到被人遺忘、拋棄的痛苦,因此當喬治勛爵破產時,她選擇了幫助這個生意場上的失意者重新活在希望和幸福之中。備受毛姆推崇的維多利亞時代思想家和美學家羅斯金曾表示,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但道德只有一個。這個道德,“它曾經是,現在是,將來永遠都是,所有文明人心中的本能,如同他們的身體外形一樣是確定不變的,道德從宗教那里獲得的不是規則,也不是地位,而是希望和幸福”[5](P20)。
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中,思想家阿諾德倡導要通過文化的力量使世界充滿“美好與光明”[6](P115),他尤為重視希臘精神對純樸人性的塑形作用。阿諾德認為希臘精神能幫助人擺脫蒙昧狀態、看清事物真相,并由此認識事物之美。尼采也認為希臘時期的藝術之所以能夠得到繁榮,正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意識到了人生的悲劇性質,從而產生出日神和酒神兩種藝術沖動,并提出用藝術來拯救人生。于是在希臘酒神祭上,人們有機會打破一切禁忌,狂飲爛醉,釋放欲望,以此來表達真實的自我。在尼采看來,崇尚酒神精神,表達自我,是為了擺脫社會對個人的束縛,使人回歸本能體驗。它不是教導人們回避痛苦,而是引導他們正確面對人生的殘酷和無情。羅西就是用一種酒神狂歡般的精神來體驗生活,享受生活,從而直面生活的困難和挫折。通過對現存的價值體系和道德標準進行質疑、顛覆和重估,她依靠原始自然的本性擺脫了商品社會形成的種種束縛,不僅堅守了真實的自我,也為丈夫的藝術創作帶來了清新和活力。
三、一種審美感受力
關于藝術創作,毛姆有過很多思考。他不止一次地談到精神依憑的重要性,一次借筆下人物愛德華·巴納爾德的墮落,指出,“假如一個人得到整個世界,卻丟失了自己的靈魂,那是沒有意義的”[7](P102)。人活著需要依靠某種精神,藝術的創作同樣需要注入精神的力量。這種精神可以是一種審美感受力(sensibility),它是對美的感受,對自然的熱愛,并且這種感受和熱愛能促成“一種特別心智的形成”[8](P432)。《尋歡作樂》中,羅西真摯、自然、淳樸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激情給偏見、保守的維多利亞晚期社會帶來了希望的曙光。透過這部作品,毛姆似乎啟示我們,審美感受力才是激發藝術創作的原動力。
羅西借由自己對美的領悟和感受,給家庭營造了一種原始、純樸、天然的生活氣息,給丈夫帶來了創作上的靈感和啟迪。這種美的感受力也是一種原始生命本能的訴求。藝術之所以打動人還在于它往往是對人生悲苦的赤裸裸揭示。人對悲劇總有一種深度的認同感。德里菲爾德在《人生的悲歡》這部作品中描繪過一個孩子死亡時的慘景,讀后讓人難以忘懷。孩子死后,面對殘酷無情的現實,母親為了排解憂愁和巨大悲痛,竟無意識地選擇了遵循“快樂原則”。她選擇放縱自我,在尋歡作樂中度過了那令人悲痛欲絕的一夜。然而這種出軌的行為卻極大地挑戰了維多利亞社會的傳統道德。小說中那段叛逆的描述毫無疑問使十九世紀末期的公眾感到極為震驚。批評家認為小說中描寫的那一幅幅令人痛心的畫面不真實,將給英國青年一代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殊不知,這些敘述恰恰是基于德里菲爾德的親身經歷。套用羅斯金評論透納的《販奴船》時說過的一句話,畫作撼人心魄之處就在于其“大膽構思是建筑在純粹真實的基礎之上的,而且飽含著對生活的深切理解”[9](P1330)。德里早期作品的美就來源于其真實性,并飽含著對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于是,能否欣賞這種赤裸裸的真實反而成了判斷一個人有無敏銳審美力的標志。
藝術應來源于生活的真實體驗,真實是藝術永不枯竭的生命力。羅伊的早期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原因正在于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家庭資源和所受到的學院教育背景。年輕時他曾擔任過一位政客的私人秘書,這使他有機會掌握上流社會的人情風俗和社交習慣。因此,當他在描述王公貴族時,那種輕松活潑的筆調便具有了極大的吸引力。羅伊自信、愛整潔、陽剛氣十足,具有運動員般的強健體格,他將這些品性都融合到了他的早期創作中,因此那些作品獲得了讀者的認可和喜愛。然而,他的后期作品逐漸脫離了熟悉的環境,關注焦點也轉向律師、會計師一類人群時,其描寫便不再那么得心應手了。小說人物的真實在于他們擁有喜怒哀樂的情緒,是一群有血有肉、獨具個性的個體,缺乏了真實性,藝術也就喪失了活力。
道德的養成也依賴于藝術的真實。羅斯金曾指出藝術的道德旨歸在于給人帶來“希望和幸福”。他在演講中還曾提到,一個人必須擁有正確的精神狀態,否則就無法擁有藝術。“技巧和美感”是最高的精神要素,除此之外,創作還必須具有“真實性和實用性”[5](P48)。《尋歡作樂》這個故事的緣起在于羅伊期望借助為德里菲爾德作傳來提高自己的聲望。為了否定羅西對她丈夫創作的影響,他不惜扭曲事實,以達到塑造完美作家形象的目的。殊不知,羅西才是德里菲爾德文學創作成功的法寶。生活的真實賦予了她靈性和美,其象征的“希望和幸福”,展示出了人類的純潔、善良和活力美。藝術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夠在情感上引起人們的共鳴,從而使人的道德情操得到洗禮。
結語
毛姆作為一位創作時間長達65年之久的職業作家,深知從事這一行業的艱辛,以及職業生涯中種種無法避免的憂慮和煩惱。一個作家的生活可謂是“飽經憂患”。入行之初,作家必須謙遜、好學,能夠“忍受貧困和世人的冷漠”;取得一定成就,鋒芒初露之時,他仍然需要謹小慎微,以做到“神色欣然地應付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形”[3](P243)。同時在日趨商品化的社會中,毛姆也體會到作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投公眾之所好,關注其審美情趣也就成了必然。當然,作家也將充分感受到寫作的樂趣,這種趣味來源于創作使他成為一個“自由的人”[3](P243),毛姆本人就深有感觸。對他而言,最真實的自我發現和自我肯定往往是在藝術之旅中實現的,因此他筆下的故事或人物常常與藝術結緣。
[1]Dreiser,Theodore.“AsaRealistSeesIt”[C].TheMaugham Enigma.NewYork:CitadelPress,1954.
[2]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威廉·薩默塞特·毛姆.尋歡作樂[M].葉尊,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4]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J].浙江社會科學,2002(1),165-71.
[5]約翰·羅斯金.藝術與道德[M].張鳳,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6]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M].韓敏中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7]威廉·薩默塞特·毛姆.毛姆短篇小說集[M].馮亦代,等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
[8]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9]Ruskin,John.“Modern Painters”[C].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Vol.2.Ed.M.H.Abrams.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