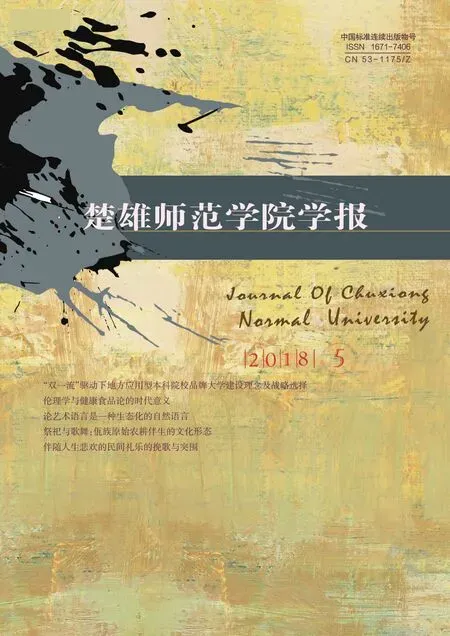伴隨人生悲歡的民間禮樂的挽歌與突圍*
——簡析電影《百鳥朝鳳》中嗩吶禮俗和傳承困境
程波濤,任家松
(安徽大學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電影是近代隨著科技發展而衍生出的綜合性藝術,能夠全面地表達人們對生活的認識,也成為傳達電影制作者的情感、觀念和深層文化心理的重要媒介。電影所反映的視角是多層面和多棱角的,也是能夠與時俱進的,在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電影藝術自然也會有自身的社會擔當和文化功能。在科技文化迅猛發展的今天,我國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正面臨著新的挑戰,而一些優秀的導演能夠自覺地抵制那些商業片和娛樂片的誘惑,最大限度地在電影中投向對于傳統民間藝術的關注中,反映出很多瀕臨消亡的民間藝術的現實困境,以及社會和民間藝人們的心聲、吁求。去年熱播的《百鳥朝鳳》是我國第四代導演吳天明的晚期電影力作,講述了陜西無雙鎮的傳統嗩吶藝人在時間流變中的生活狀態和嗩吶的民俗應用,以及傳承嗩吶技藝面臨瀕危的現實困境和新一代年輕藝人苦苦堅守的故事。影片直面現實,故事情節層層推進,藝術感染力強,喚醒了更多國人對民間藝術的關注與保護意識。
一、影片中嗩吶藝術承載的禮樂傳統與道德判斷
影片中的嗩吶曲《百鳥朝鳳》具有復雜的象征意義,曲譜扉頁上題有:“百鳥朝鳳,上祖諸般授技之最,只傳次代掌事,乃大哀之樂,非德高者弗能受也。”由此也點明了該曲目獨特的情感關懷和道德表達范式。《百鳥朝鳳》注重“哀”的表現,而“哀”時則通“愛”,《管子·侈靡》中說:“國雖弱,令必敬以哀。”《淮南子·說山》言:“各哀其所生”都從情感方面積極肯定“哀”中之愛。“大哀”即“大愛”。“哀”中有“愛”,才使得“哀”真正地成為有人性溫度和社會關懷的“哀”。“大哀”如果納入美學心理范疇,強調的是一種情感關照與情感聯系,不僅包括簡單感性層面上的悲哀憐憫,更涉及理性層面上道德判斷的靜態之“愛”,是飽含深情的“詠嘆”,一詠一嘆皆成曲。在《百鳥朝鳳》這首“大哀之樂”中,體現的是人們對逝者的深切哀悼與真誠尊重,也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所崇尚和遵循,并融入精神血脈中的一種人倫美德。火莊竇老村長的葬禮上,焦三爺說“百鳥朝鳳,敬送亡人”,在身體嚴重不適的情況下,依然親自為德高望重的竇老村長吹奏了一曲《百鳥朝鳳》,由于焦師傅肺部病況嚴重,演奏中鮮血順著嗩吶管流出,整個場面哀傷中自有一份莊重和肅穆之感,在大禮致哀的同時,還含有一份對于亡者生命價值的社會貢獻肯定。
經典嗩吶曲《百鳥朝鳳》是一首有著鮮明禮樂傳統的民間樂曲,具有嚴格的形式規范。“禮”起源于遠古社會的巫術禮儀活動,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系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指出:“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1](P53)“禮”是已經理性化的巫術禮儀,保存著最初的神圣性和禮儀的規范性,是遠古氏族維系生存而自然形成的社會行為規范,對每個成員具有普遍的強制作用,“每個個體以其遵循的行為、動作、儀式來標志和履行其特定的社會地位、職能、權利、義務。”[2](P16)《百鳥朝鳳》作為禮樂傳統文化的載體,在傳承和演奏時限制頗多,如“只傳次代掌事”,游天鳴通過“傳聲”儀式后,才能從焦三師父那里學習到《百鳥朝鳳》。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禮儀之邦,而傳統意義上的“禮”是我國早期社會敬天、事神儀式的產物。因為“禮”本身的特殊性,儀式固化成一套觀念和具有深刻內蘊的文化行為,超越了“禮”的對象而逐漸走向人的內心世界,修正人們對生死和天地自然的認識,參與人們內在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建構,直接影響人們對世間萬物、神靈、生死等終極問題的深度思考和理性認知。這種思考與理解融入到禮俗之中,使人類自覺脫離動物情感而賦予了社會心理內容,認同“禮”的載體所表現出來的心理形象。因此,“禮”在古代社會中,具有神圣的意義和崇高的地位。游天鳴拜師后第一次回家,夏夜納涼時,游本盛就對他年幼的兒子游天鳴說:“《百鳥朝鳳》只在白事上用,受用的人要口碑極好才行,一般的人是不配享用的。”這說明“禮”在情感和行為上對人類的養護,內部驅動力是“德”,當“禮”的儀式完備后,人們在內心深處才能產生“敬”,敬畏和敬仰之情,在行為和思想上則要求所受用的人必須是有德者。
也可以說,“德”是“禮”在社會個體心理和行為上的細化要求而產生的結果。《樂記》說:“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不僅指思想、政治、精神等方面的客觀標準,也指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內容。《百鳥朝鳳》是大哀的曲子,哀的是喻指有德者的“鳳”,“禮”的儀式感和精神性更強,“德”的現實要求最直接,“禮”也是“德”得到肯定的形式轉換和載體。如“傳聲”是嗩吶班班主確定接班人的儀式,是對嗩吶藝人人品和藝品最好的肯定;金莊查老村長過世,查家族人跪地懇求焦三爺吹奏一曲《百鳥朝鳳》,焦三爺搖頭不允,因為“嗩吶一響,百鳥為王”,《百鳥朝鳳》“乃大哀之樂,非德高者弗能受也”。
禮樂傳統中的“樂”是“禮”實體化的載體和傳達樣式,《呂氏春秋·古樂篇》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在古代社會,禮中有樂,樂中有禮,禮樂并存。“樂”可以陶冶性情、塑造人的情感模型,在促進人性的覺醒方面,比“禮”直接和關鍵,追求人與萬物的一種自然和諧,滋養人的內心。焦三爺得意時便會心地提示徒弟天明:“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是吹給自己聽的。”可見,他把自己的情感和才華,乃至對于生命價值的理解全部寄托在心愛的嗩吶之中。音樂通過節奏和旋律訴諸于人的官能,它與自然界的規律性運動和人的情感變化,都在一個場域,彼此相互對應,形成了一個在人類深層意識層面上的同構系統。以焦三爺為代表的嗩吶藝人早已把嗩吶曲看成自我情感的象征,把“嗩吶吹到了骨頭縫里”,他的嗩吶不僅是用情的,也是“走心”的。也只有真正的行家里手才能說出這種表達音樂“極境”和“至境”的話語,它入情入理,而又能“從心所欲”。另外,“樂”可以說是一系列情感性文化符號的集合,情感依附于音樂的抽象形式,在形式的不斷組合和轉換中凝聚著人類最本真的感受,在或高或低、悠揚短促的曲調中飽含著人類超越動物性的思想觀念和審美層面。隨著歲月的流逝,在樂曲的形式中積淀了社會群體的文化心理結構與普遍的情感意識。
二、影片反映出儒家文化傳統中的生死觀與喪俗中嗩吶的民俗文化承載
自古以來,國人是“重生”的,即注重對人性的養育與終極關懷,積極肯定人的現實價值,“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3](P101)也相信“靈魂不死”,“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人的魂魄充盈于天地之間,人與天是一體的,敬人也就是事天,這在國人的意識里根深蒂固,把天與人在一起考量,面對生死,天是不變的對象,變化的只是人的生與死。對于死亡這個問題,古人認為一個生命的逝去,只是歸于天地之間,以另一種方式存在,生死是順應自然規律的事。《百鳥朝鳳》作為“大哀之樂”,一則“事死”,再則“敬天”。面對死亡與天地,國人充滿了敬畏,同時也有一份難以言說和無法挽留的愛,因為敬畏,產生了一系列的行為規范和禮儀制度,“愛”則在這行為規范和禮儀制度中傾注了人們難以言說的復雜情感。這種情感,對于藝術的誕生具有促進與推動的力量,原始先民們不單單希望得到天地和亡人的雙重庇護與福佑,還在迷幻的感情想象中體驗到自身與生死和天地溝通的力量。
儒家傳統的人生觀價值觀是積極入世和充滿社會擔當的。他們以“立德、立功、立言”作為“三不朽”,這種積極的生命態度和向死而生的精神,賦予了生命以積極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對于個體生命來說,生和死是大事,而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關鍵人物的生死也是重要的。例如,像六出祁山的諸葛亮之死,對于蜀國來說損失之大難以估量,難怪唐人杜甫感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此,對于“重于泰山”之士和國之重器者的逝去,實際上就是一種國哀。作為一種自然生命過程,古人也曾感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時間的流逝不可逆轉,人的死亡問題終須積極面對。儒家提倡“未知生,焉知死”的觀點,著重在“生”的問題上,認為“生”是我們最該考慮的問題,“生”的提問得到了解決,我們才能更坦然地面對死亡,也才可能在生死的問題上保持著達觀、通脫的態度。《百鳥朝鳳》作為一首象征意義的民間樂曲,“非德高者弗能受也”,儒家的仁義思想規定了它的外在形式和使用規范。道家也重視個人的價值,出發點不在功名和道德,而是順應自然,生死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唯一不變的就是“道”;另一方面,道家又提倡“樂死”和不朽,“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生。故善吾生者,乃善吾死也。”(《莊子·大宗師》)偏向于人死之后精神世界的模擬重建,顯得更為超然和崇高。在一定程度上說,生與死、人與神的分別在國人心中始終沒有較明顯的界限,在相依相偎,相互之間發生著微妙的內在聯系。像影片《百鳥朝鳳》中也營造一種百鳥歡騰的虛幻景象,使得另一世界不至于那樣的陰森恐怖,而這樣的“大哀之樂”,實際上是有德的逝者喪俗中才配吹奏的,因此,也是“大愛之樂”了。在悠揚自然、緩急并重的曲調中多方面地體現著人們對死的哀嘆、生的留戀,如泣如訴、似曲非曲,通過低徊哀婉的樂曲表達生者對逝者亡靈的尊重和國人“視死如視生”的態度。
三、影片主題中所折射的“五行”觀念和民間嗩吶面臨的現實困境
影片中虛構的無雙鎮,位于陜西漢中平原,由水莊、土莊、金莊、木莊、火莊組成。我國古代哲學家認為金、木、水、火、土是構成物質的五種基本元素,古人經常以“五行”相克相生、相依相存的理論和認知方式,來解釋世界萬物的構成因素、演變趨勢及其運動關系。古人認為正是通過五種物質之間的規律性互動,這個物質世界才能生生不息。無雙鎮作為這種哲學觀念的一種實體表達或文化隱喻,在過去的時光里它有著自身存在的價值和規律,保持著穩定的內部聯系和生存狀態。五個村莊中的任何一個村莊發生變化,都會影響無雙鎮的整體性質,改變五個村莊之間相生相成的微妙關系。嗩吶藝術作為無雙鎮的精神符號和一種禮樂形式的存在,和無雙鎮具有某種文化共生性的復雜而奇妙的關系,無雙鎮在現實社會中的發展變化對嗩吶藝術的生存與傳承至關重要。影片中,最先發生變化的是木莊,長生結婚時請游家班第一次出活的時候就沒有行接師禮,對于這種“失禮”的行為,焦三爺氣憤之余,也只能無奈地說:“哼,沒規矩了,沒規矩了。”影片選取無雙鎮作為典型,指代逝去的中國傳統村莊形象,“牽一發而動全身”,無雙鎮社會風俗的快速變化,是嗩吶藝人焦師父為代表的民間藝人的生存空間和嗩吶藝術興衰的真切見證。
此外,在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無雙鎮似乎成為了值得關照和反思的典型客體,以此來對標外部世界的變化,突出兩者的對比,在敘事進程中為影片后半段的激烈沖突埋下伏筆;再者,無雙鎮作為民風古樸和正在轉型時期傳統村莊形象的典型象征,這種帶有詼諧與隱喻性質的“無雙鎮”,顯然被附加了“范本”和“化石”的特殊寓意,對當代觀眾會產生既新鮮而又有神秘感的強大吸引力與暗示性,觀眾在欣賞影片時易于被帶入預先設置的情景中,引發觀眾對無雙鎮的嗩吶藝人在時代變遷時所做的選擇產生深入的思考。另外,影片的內在線索似乎也在不斷地暗示觀眾,不變的就是有意義和值得保護的,無雙鎮是唯一的、自在的,它是傳統社會中無數民間古鎮的縮影。影片前段竭力為無雙鎮營造出一種時空停滯感和隔離感,著重表現無雙鎮民風的完整和淳樸,主要作用在于加深我們現代人對鄉土形象的識別和記憶,激發觀眾對無雙鎮上傳統嗩吶藝人的人性理解和關懷。
禮樂傳統作為嗩吶藝術內在精神形式表達的隱形內核和文化背景,推動著嗩吶藝術不斷發展,它傳達的自然內容和社會情感共同構筑成嗩吶藝術背后的精神來源,藝人們傾注到嗩吶藝術中的觀念和神圣的情感也投射到了嗩吶這種樂器身上。嗩吶個頭兒越小,調門越大,它由哨、氣牌、侵子、桿和碗五部分構成,每部分的作用都不同。
焦師父把自己學藝時第一個使用的嗩吶送給了游天鳴,特意交代游天鳴裝嗩吶的布袋是師娘縫制的,嗩吶在藝人心中飽含著情感溫度。嗩吶作為一種樂器為嗩吶曲的形成提供了物質方面的外在尺度和根據,主體意識和嗩吶這種樂器的相互交織磨合,讓嗩吶藝人在吹奏的過程中更具有目的性和表達上的自由。《百鳥朝鳳》是大哀之曲,樂調低沉,焦師父只用一只使用過五六代的金嗩吶去吹奏;游天鳴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嗩吶時滿眼淚水,焦師父告誡他嗩吶離口不離手,要好生護著;在傳聲儀式上,游天鳴接過焦師父的金嗩吶,流下了激動的眼淚,這是一種對嗩吶藝術背后集聚著的禮樂傳統和情感積淀的深刻認知。游天鳴有了金嗩吶,焦師父才會教授他《百鳥朝鳳》,金嗩吶這時不僅僅是一種樂器,似乎也成為一種禮器和道器,也可以說是《百鳥朝鳳》這首嗩吶曲的物質載體和實體象征。
以焦師父為代表的嗩吶藝人對嗩吶曲的深情、執著和堅守,著實讓人為之動容。游天鳴出師后回來看望焦師傅,師徒相飲盡歡,飯后微醺的焦三爺用小個子的嗩吶吹奏了一首激昂澎湃、情緒飽滿的曲子,對天鳴神采飛揚地說:“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是吹給自己聽的。”可見,在焦師父心中嗩吶是有靈魂的,這說明“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焦三爺把情感全部寄托在那具有生命力的嗩吶曲中。可是,面臨時代的發展變遷,嗩吶藝術的傳承卻承受著極大的現實壓力。焦師父希望無雙鎮的嗩吶匠們把《百鳥朝鳳》這首曲子世世代代傳下去,在竇村長的葬禮上,焦師父泣血吹奏《百鳥朝鳳》,更是把這種禮樂的道德判斷和他對于嗩吶曲的莊重之情、崇敬之意推向一個極致。影片對焦三師父一心不忘傳承嗩吶藝術的場景著墨甚多,可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流行文化的廣泛傳播,傳統的嗩吶藝術面臨嚴重的生存考驗。在新時代,農村的文化生態和經濟結構都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人們的精神娛樂和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已經多樣且急迫,不同娛樂方式的不斷出現又為這些需求提供了多種選擇。當天鳴在馬家的葬禮上第一次聽到長號的低鳴時,他顯得那樣的茫然無緒,暗示了傳統藝術將在新時代面臨何等嚴峻的挑戰。“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4](P227),面對山寨西洋樂隊的低俗表演卻又得到年輕人熱烈圍觀這種陋俗的嚴重挑戰,為了維護嗩吶藝術的尊嚴,嗩吶班藝人甚至和一幫社會閑散的小混混們發生肢體上的直接沖突。最讓游家班班主游天鳴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一直摯愛、敬重、堅守,甚至認為原本在鄉民心中很神圣的嗩吶藝術,在現實面前似乎那樣的脆弱和不堪一擊。時代在變,但傳統民間藝術保存著很多國人共同的記憶,一項民間技藝的消失會給我們留下無盡的遺憾和難以言說的酸楚與焦灼,而民間技藝中沉積的歷史文化、情感、匠心等傳統因素,在當代社會可以滋養、慰藉鄉下人貧瘠的精神生活,促使我們在新時代可以和過去的歷史文化產生情感上的聯系和共鳴,從而顯得彌足珍貴。影片結尾的一幕更是讓人不勝唏噓,游天鳴在焦師父墳前孤獨而莊重地吹奏著《百鳥朝鳳》這首具有深刻文化內涵的民間樂曲,濃郁悲涼的生命意緒在蒼茫大地間回蕩,曾經紅火千百年的嗩吶經典曲此刻竟然顯得那樣的沉重、悲愴和蒼涼,又似乎是那樣的孤獨、迷茫和無助,但仍不失金色嗩吶應有的嘹亮和鏗鏘,它暗示和提醒著人們傳統嗩吶技藝在傳承和發展中所面臨的現實困境,發人深思。
四、結語
嗩吶藝術保存著中華民族諸多原鄉的“記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轉型,很多民間藝術日趨式微,電影《百鳥朝鳳》結尾時的畫面和哀樂,使其籠罩在無奈、悲涼和低徊的基調中。重點選取嗩吶曲中的哀樂來表現嗩吶藝術特色的同時,也真實地反映出它被社會接納空間的狹小與傳承的困境,似是農耕時代那些傳統民間技藝日趨式微的凄涼挽歌。影片對傳統技藝的形象描繪功能和情感關懷作用做了極致的刻畫,也表現了民間藝術的行規和對于亡人所吹奏嗩吶曲式中“禮”的堅守。影片中也能夠見到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情感變化以及嗩吶藝術在現代社會中所面臨的種種窘境。嗩吶藝術演奏中蘊含的復雜技藝、文化基因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素是我們先人精神生活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延續形式,我們應保持對傳統文化技藝的敬畏之心,理解和傳承那份持之以恒的匠心精神。影片的結尾,夕陽下,游天鳴在焦師父墳前吹奏的《百鳥朝鳳》是悲壯的,但愿這種悲壯不是悲涼的、孤獨的和迷茫的,它不應當只是古老民族文化中嗩吶的回聲和悲鳴,而應喚醒社會大眾對傳統民間技藝的關注和保護、傳承意識,這才是這部優秀電影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