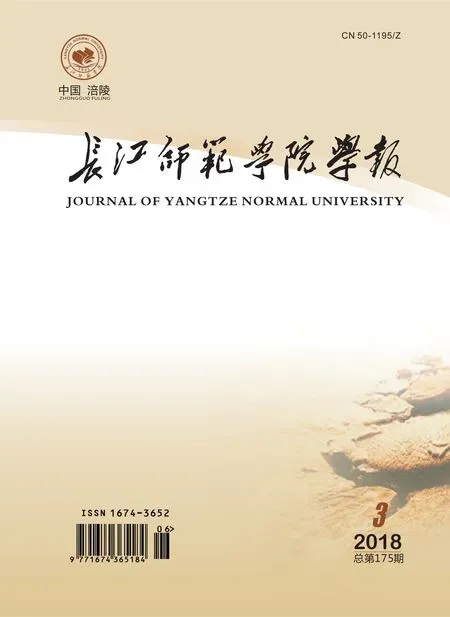新舊《五代史》關于吳越錢氏家族記載的異同
苗夢穎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吳越國,一在春秋戰國,一在晚唐五代北宋初。這里所研究的是后者,因其開創者和后來的即位國主分別是錢镠及其子孫,故在“吳越國”前加“錢氏”二字。史書對于錢氏吳越國均有記載,這里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比較新舊《五代史》關于吳越錢氏家族記載的異同。
一、錢氏吳越國
吳越是五代時十國之一,錢镠作為吳越國的建立者,發跡史頗具傳奇色彩。唐末追隨石鏡鎮將董昌,為其副將,擊敗黃巢起義軍的進攻。乾寧三年擊敗董昌,盡有兩浙十三州之地。后梁開平元年封吳越王。歷經三代傳至錢俶,立國80多年。
吳越錢氏政權在江浙地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政治上,宋太宗稱譽錢俶:“卿能保一方以歸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1]蘇軾同樣盛贊錢氏給吳越居民帶來的福祉,云:“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2]在經濟上,錢俶納土使百姓免于戰火,更使江浙得以發展。入宋后,江浙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為全國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在文化上,錢氏奉行“向學重文、禮賢下士”,文人學士聚集于此,如皮光業、林鼎、沈菘、羅隱等。錢氏廣建佛寺、佛塔等佛教建筑,弘揚佛教文化,佛教的信仰使處于動蕩社會中的人們有了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促進了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這些貢獻都被宋朝統治者所認可,同時也為錢氏在宋朝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新五代史》(以下簡稱《新》)的編撰者歐陽修與錢氏后人錢惟演關系密切。歐陽修在中進士后,便在錢惟演的幕府中工作,與錢惟演、謝希深等人終日飲酒賦詩。歐陽修在其《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中明確地記錄了這段快樂的時光:“(錢惟演)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3]386
錢惟演也將歐陽修視為英才,優待有加,如《澠水燕談錄》就記載:“天圣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4]40在歐陽修離開錢惟演幕府后,仍念念不忘恩公,甚至在錢去世后,還努力為他請得美謚,記載于《邵氏聞見錄》,以反映錢惟演禮賢、愛賢的品質[5]。
二、新舊《五代史》記載的異同
《舊五代史》(以下簡稱《舊》),原名《五代史》,也稱《梁唐晉漢周書》,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的官修史書。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書中可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五代各朝均有實錄。《新》原名《五代史記》,為北宋歐陽修私撰。始撰時間大約在宋仁宗宋景祐三年,至宋仁宗皇祐五年成書為止,歷時18年,比薛氏《舊》晚出近80年。后人依薛史、歐史問世之序,以“新”“舊”相別,故薛氏《舊》、歐陽氏《新》為后世沿稱。
北宋時期,兩書并行于世。在南宋,興行《新》而廢止《舊》,后人據《永樂大典》及眾多史料,重新恢復《舊》大致原貌。同處一時代,共記一時期,兩書的命運卻大相徑庭,至于原因,前人多有研究,這里主要探討作為十國之一的吳越國在新舊《五代史》中的記載,尋其異同之跡。究其緣由,亦希有所發現,以求正于方家。從整體來看,新舊《五代史》關于吳越國錢氏記載有異有同,然是異多同少。
第一,相同之處。《舊》將中原政權以外的地方割據政權,分為《世襲列傳》和《僭偽列傳》。對于五代,《新》《舊》均持肯定態度。然十國就另當別論了,《舊》視其為獨立之國,《新》則認為十國是“并起爭雄的鯨先盜販”。可見,在對待十國的態度上,《新》《舊》大體相同,均視其為正統。對待五代和十國兩者之間截然不同的態度,究其原因,是因為宋朝承襲后周政權,尊“五代”也是為了維護北宋政權的正統地位。“實際上,十國與五代在當時并立于世,不分正偽,何況,五代立國都非常短促,加起來不過53年,而十國政權立國皆比五代時長,最短的北漢也有28年,而且它們都是自建國號制度,有的表面服從中原王朝,實際完全獨立。”[6]作為十國之一的吳越國當然亦不能免俗,相對于五代,新舊《五代史》記載內容較少,但記載內容大體相同,這是因為兩書皆是來自于《五代史錄》。錢镠作為吳越國的第一任君主,兩書都花費大量筆墨進行描寫,其發家史大致如下:跟隨董昌(討黃巢、滅劉漢宏)→割據兩浙(占浙西、討伐董昌、平定徐許之亂)→建國吳越(封越王、吳王、吳越王)。經歷三代四傳,至于其他各君主,記載較少,大多幾筆帶過。這與新舊《五代史》的編纂者們的態度是密切相關的。
第二,材料之不同。《舊》共150卷,《新》共74卷,然后者的史料相較于前者,有增無減。歐史增補了薛史所無的史事,如王鳴盛所言:“僭偽諸國,皆歐詳薛略,蓋薛據實錄,實錄所無,不復搜求增補,歐則旁采小說以益之。”[7]709不可否認,歐史對薛史的增補確是事實,特別是對十國政權的記載,《新》比《舊》更加詳細完備。具體原因有三:1.歐陽修修撰《新》時,十國政權消失數十年,各國的史籍尤其是南唐和后蜀史籍匯集京城;2.在此期間,《九國志》等已經問世,歐陽修曾參加過《十國志》的撰寫;3.歐陽修比薛居正等修史晚80年,這期間又出現許多薛史所未能見到的新材料。據學者考證,歐史所據文獻材料大約有60種之多,除文獻材料外,歐陽修還注意從金石及社會調查中獲取材料。
在兩書中,有些關于吳越國錢氏家族的記載也是不盡相同,取其一例:《舊》記:“镠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庀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剎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8]1771《新》載:“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勝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9]843
由此可見,《舊》側重于描寫錢镠的窮奢極欲,而《新》不僅描寫了錢氏的淫奢,還描寫了苛政嚴法。此外《五國史補》中也提到錢氏的奢侈之風。曾在雍熙年間任蘇州長洲縣令的王禹偁對吳越的情況較為熟悉,說:“錢氏據十三郡,垂百余年,以深賜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民自奉者久矣。屬中原多事,穩小利而忘大義,故吊伐之不行也。洎圣人有作,錢氏不得己而納其土焉。均定以來,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弊猶多。”[10]錢氏吳越國在水深火熱的五代十國時期,再加上錢镠出身貧苦家庭,發跡之后免不了興起愛奢之風。不單單是吳越國,五代十國君主沒有一個可以避免。這從側面反映了吳越國經濟的繁榮,地區的富庶。然而《吳越備史》稱錢镠“自奉節儉,衣服裘被,皆用綢布”[9]。這與《新》《舊》兩書記載截然不同,究竟哪個更為接近歷史,就如司馬光所說那樣:“按錢镠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11]這種說法無疑得到更多的認同。關于吳越的賦斂苛政現象,宋人內部多存在爭議。對此,司馬光也說:“吳越雖重稅斂以事供貢,然椒多寬民之政,下令租賦多所通滯,歲杪必命鐲蕩。又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于是境無棄田。或請糾遺丁以增賦,椒杖之國門。故終于邦域之內悅而愛之。”[12]其實無論真實與否,都不會影響世人對吳越的正面評價。
史書之所以備受后人重視,其重要原因在于留下了豐富的史料,這也是衡量其文學價值的重要因素。相對于唐宋這些悠久且重要的朝代,對五代十國的記載就相對略少。新舊《五代史》作為研究五代十國的重要史書,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相對于薛史,歐史增加了不少材料,然歐史也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點,即一味地追求言簡意駭,刪除了大量的原始資料。《舊》150卷,直接引用了許多皇帝的詔書、敕令和大臣的奏疏。這些材料源出五代歷朝實錄,彌足珍貴。所謂“奏疏”,即奏與疏,“奏”意謂臣子向君主進言或上書;“疏”意謂官員向朝廷的建議。據統計,《舊》直接引用官員“奏”原文有87條之多,直接引用官員“疏”原文6條。如新舊“五代史”均提及由于烏昭通的關系,錢镠被貶,其子錢元瓘為父上書陳情的事情。《舊》摘錄了錢元瓘奏章的具體內容:“竊念臣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臣镠,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天復之初,已封茅土……謹遣急腳,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8]1769-1770
而《新》以“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一句話概括之。此外,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稱:“歐史喜采小說,薛本多本實錄。”[7]677
歐史記載其事,較薛史詳盡,因為歐史利用小說、筆記等材料,補充了不少傳記中的史事或者細節,但卻刪除了較多寶貴的原始材料,因此就史料價值而言,《舊》高于《新》。
第三,作者思想的差異體現。其一,10世紀的中國,南北紛爭、五代更迭、十國割據,而偏安東南一隅、國狹勢弱的吳越國卻休兵息民,社會安定,國富民強,以及后來入宋后的隱忍態度,這與其實行崇尚佛教的政策都是有一定聯系的。如廣建寺院,其中有著名的靈隱寺擴修,修建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功臣塔等。錢氏吳越國歷經三代五王,錢謬、錢元瓘、錢弘佐、錢弘徐和錢弘俶皆崇釋禮佛,大力提倡佛教,王室成員更是帶頭禮佛、供佛,從而在全社會蔚成習佛風氣,且在歷代帝王之中,鮮有出其右者。因此新舊兩書在記述錢氏家族時必然要提及,然《新》并未提及此事,令人不免生疑。《舊》在文后摘錄《五代史補》,云:“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珝所禮,謂之國師。”“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8]1775《舊》記述了君王與僧人的往來,由此看出其皇族崇釋禮佛。撰者薛居正所處的宋代初年,在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及價值體系領域還都處于過渡階段,重武輕文依舊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士大夫們不受重視,對于國家民族命運淡漠,因此其編纂過程中自己的思想流露較少。《新》對于此事卻只字未提。細究原因可發現,歐陽修是北宋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是復興儒學、排斥佛教的有力倡導者。歐陽修反對天命、佛、道及各種迷信的思想在一些史著和史學論文中也早有論及,如《原弊》一文中指出,佛教勢力的發展與“農本”追求背道而馳,已成為危害社會的一大弊端,“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3]870。且“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3]872。慶歷三年,歐陽修完成了《本論》3篇,其中《本論》中、下兩篇集中論述佛教的危害,闡發歐陽修的排佛理論。因此他在史料取舍時,對相關記載棄而不用,很好地表現了歐陽修的反對迷信思想。
其二,《新》云:“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镠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自愛’。”[9]835此言錢镠自小骨法非常,有貴人之才,不免有重天人之嫌。又云:“元瓘字明寶,少為質于田頵。頵叛于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后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9]841此關于錢元瓘的記載也不免增加了神秘色彩。《新》撰者為歐陽修,他主張樹立儒家傳統,反對天命和各種迷信思想,對于此等史料,作者都是棄而不用,為何作者卻一反傳統描述了關于天命的事情。探而觀之,則不難發現,這就是歐陽修修史所采用的春秋筆法。北宋中期的社會面臨著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的爆發引發了士大夫強烈的責任感,歐陽修等人積極倡導政治變革,其意識形態在《新》中得到鮮明的體現,因此歐陽修選擇用“春秋筆法”來宣傳王道大一統的思想,用春秋義法來結構史書。《春秋》宗旨和筆法是歐陽修史學實踐的基礎,他通過對錢镠及錢元瓘的讖應占卜之言的記載來對這種迷信思想加以深刻批判。王辟之則在敘事之末評價歐史曰:“文約而事簡,褒貶去取,得《春秋》之法,(司馬)遷(班)固之流。”[4]70
相比之下,《舊》史料基本來源于歷代實錄,五代實錄由五代、北宋初年人撰寫,于政權建立者的神化、溢美之詞不言而喻,然對于吳越國,薛史卻一反傳統,只字未提,相比于歐史借史書來宣傳自己的思想,《舊》作者更是客觀陳述,個人思想融入較少。其實關于這些靈異傳說,《通紀》《吳越備史》《太平廣記》等書均已提到,如八百里退兵、錢镠射潮等,更多地表現出百姓們對錢氏功績的褒揚。
第四,史論之不同。史論列為一文之末端,較能反映編撰者的觀點思想。對于吳越錢氏家族,兩書有不同的評論。《舊》云:“史臣曰:自唐末亂離,海內分割,荊、湖、江、浙,各據一方,翼子詒孫,多歷年所。夫如是者何也?蓋值諸夏多艱,王風不競故也。洎皇宋之撫運也,因朗、陵之肇亂,命王師以遄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瑤琨筱簜,咸遵作貢之文;江、漢、雎、章,盡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有歸,人寰允洽故也。惟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大勤王之節,與荊楚、湖湘不侔矣。”[8]1775-1776
薛的觀點顯而易見,認為錢氏不是節儉之人,但對其功績還是表示認可的,贊賞的是錢氏歷代君主與眾不同的“蓋事大勤王之節”,奉中原為天子,稱臣納貢。然《新》稱:“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竊亦多自托于妖祥,豈其欺惑愚眾,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于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9]844
由此可看出,歐陽修在前面引用大量讖應占卜之言,是為了更加有力地進行批判,這與他反對符讖災異迷信也是相吻合的。此外歐陽修對錢氏大加苛責,認為其苛政嚴法,沒有造福于一方百姓。對此,我們不甚贊同。錢氏在位84年,保境安民,興修水利,發展農業,最后一代君主錢俶更是納土歸宋,使萬千百姓免于戰火。怎么能說其無德澤施其一方呢?表明歐陽修此種偏見的,還有《新》卷61《世家序》中的一句話:“駁剿弗堪,吳越其尤。”[9]747
錢氏家族至今在兩浙地區都深受百姓的愛戴,這與錢氏“納土歸朝”是密不可分的。《十國春秋》論曰:“錢氏據有兩浙,幾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巨矣。”[13]由此可見,對于錢氏家族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
總之,新舊“五代史”對吳越國的記載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可以看出其鮮明的不同態度,以及新舊《五代史》編纂的異同。
[1]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13904.
[2]蘇軾.蘇軾文集編年箋注[M].李之亮,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11:587.
[3]歐陽修.歐陽修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
[4]王辟之.澠水燕談錄[M].呂友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
[5]邵伯溫.邵氏聞見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3.
[6]姜海軍.新舊《五代史》編纂異同之比較[J].史學史研究,2013(3):27-36.
[7]王鳴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8]薛居正,等.舊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9]歐陽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9]錢儼.吳越備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1:.
[10]曾棗莊,劉琳.全宋文[M].成都:巴蜀書社,1989:349.
[11]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8880.
[12]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宋元浙江方志集成[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1113.
[13]吳任臣.十國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2010:1184.
——雷峰塔與吳越國佛教藝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