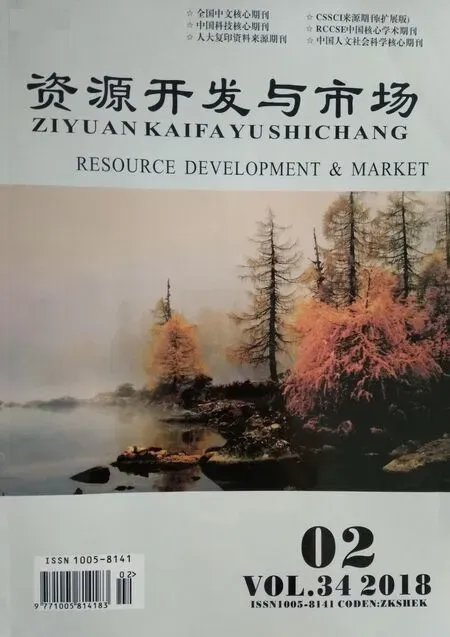川甘青毗鄰藏區農牧民生計困境調研
——基于川甘青三省八縣的調查實證
桑晚晴1,柴劍峰
(1.四川農業大學 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2.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科研處,四川 成都610074)
川甘青毗鄰藏區是我國生態安全重要承載區、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也是國際關注的特殊跨行政區。該區域集自然環境惡劣、生態系統脆弱、社會問題復雜、經濟發展滯后于一體,在自然和人為雙重因素的影響下,地區草場退化沙化、沼澤面積急劇下降、水土流失、自然災害頻發等生態問題不斷吞噬著農牧民賴以生存的資源與環境,生態退化與生計衰微交互影響,從而陷入逆向累積循環的因果鏈條中。近年來,國家和國際都給予該地區足夠的關注,因地制宜實施了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退牧還草、生態補償、牧民定居、“9+3”等生態工程建設,地區生態功能有所修復,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得到了改善,但農牧民貧困問題和生態惡化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社會矛盾與沖突依然嚴峻,地區發展面臨著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現實生計生態困境問題。精準扶貧戰略提出農牧民要與全國人民同時步入小康,必須診斷農牧民在脫貧奔康路上存在的問題,尋找破解困境之策。
本文選取川甘青三省八縣為調查對象,分析農牧民生計模式與生態環境的依存關系,從農牧民生計資本特征出發,通過個人訪談、抽樣調查等方式,分析當地農牧民可持續生計框架的搭建,探究在此生態環境背景下農牧民的自主發展權和決策權,了解不同生計模式的農牧民對生態環境變化的感知,農戶環保參與意愿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化對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農戶生計模式的變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診斷生態治理運行過程的突出矛盾、關鍵問題和原因所在,揭示農牧民生計困境與生態困境交織共生的動態衍化規律,探索生態困境背后的社會土壤,以期尋找破解地區生計生態困境的現實路徑,實現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 農牧民可持續生計困境差異化統計分析
川甘青三省八縣作為典型的生態環境脆弱區,農牧民生計活動與生態環境緊密相關。實踐和實證研究表明,農牧民不合理的生計模式是導致該地區生態環境退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時,地區生態環境又是農牧民生產生活有效依賴的自然資源。在上述生態資源困境的大背景下,農牧民可持續生計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基于此,本文從影響農牧民生存的主客觀因素——生計資本進行考察和研究,并對其差異化進行統計分析。
1.1 數據來源與說明
根據川甘青毗鄰藏區區域的劃分,選取四川的若爾蓋、紅原,甘肅的碌曲、夏河、卓尼、迭部,青海的共和作為調查對象,通過以下渠道來獲取相關的信息:①通過與地方政府等相關部門的座談,從整體上把握地區基本發展情況;②從地方院校視角了解地區農牧民發展情況、生態環境變化情況等;③從寺廟角度了解傳統宗教文化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作用;④從農牧民視角,通過深入訪談和問卷調查等方式具體了解目前農牧民的生計狀況。
1.2 農牧民生計資本框架
對農戶生計資本的調查,本文基于可持續生計框架,從人力資本、自然和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四個方面來了解農戶的生計模式和生計策略[1],具體為:①人力資本。在農牧民的生計資本中,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直接影響著農牧民駕馭其他資本的能力和范圍,決定了個人和農戶應對風險的生計策略,從而決定了其家庭生計模式。基于地區現實情況,本文對人力資本的測量主要從以下指標來體現:一是基于年齡和健康狀況為主要標志的家庭成員勞動力指標;二是家庭成員的文化程度和就業方式所體現的生計能力指標。②自然和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包括土地資本和水資源等為其提供最基本生存保障的資源資產,土地資本主要通過農牧民擁有或長期使用的耕地、草地、林地及其質量狀況來衡量土地資源情況,水資源狀況主要通過水資源獲得的便利性、水資源污染情況兩個指標來衡量;物質資本主要從農戶住房面積、現代化家用電器、家庭飲水來源3個指標來體現。③金融資本。金融資本主要是指農戶可自由支配的貨幣資本,本文以農業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包括從事交通運輸、批發、零售等第二三產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土地流轉、利息等)、轉移性收入(包括各項補貼、親友贈予、子女匯款、低保等)5個指標的3年變化來衡量農戶的金融資本稟賦。④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主要指農戶生產生活所形成的可利用的社會網絡以及可得到的社會支持,測量指標包括人情往來支出、借款渠道、家庭中干部和公職人員數、教育、醫療獲得的便利性等指標。
1.3 農牧民生計資本的統計分析
人力資本:在人力資本方面,調查對象家庭戶均規模為4.96人,戶均勞動力2個,家庭成員健康的占樣本總數的73.2%,26.8%的家庭都有慢性疾病或傷殘病人。從文化程度看,父母輩及以上的家庭成員為小學或文盲的占78.1%。由于地區傳統文化的影響,男性的文化程度高于女性。子女輩的文化程度為初中或高中的占26%,大專及以上的占59.3%。受教育程度呈上升趨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為其生計多樣性提供了可能,由過去依賴勞動力數量轉變為依靠勞動力質量來獲取人力資本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是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農牧民可持續生計平衡的重要策略。通過對受訪家庭生計方式進行分析表明(圖1),家庭收入來源以務農為生的占27.3%,以放牧為主要的占42.4%,務工和經商分別占15.2%和9.1%。從目前來看,當地生產活動仍以農牧業為主,但生計模式正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農牧業已不再是農牧民唯一的生存技能。
自然和物質資本:在自然和物質資本方面,據調查結果分析,在半農半牧區目前受訪家庭戶均草地面積13.33hm2,包括自家和租用的草地面積,戶均耕地面積為0.33—0.4hm2,平均每戶家庭有40—50頭牛(多的達200—300頭)、139頭羊。相對于前幾年,78%的家庭牲畜的養殖都處于減少態勢,主要是因為草場質量下降降低了牛羊養殖。同時,也體現出隨著生態環境的轉變,農牧民生計模式發生變化。水資源方面,92%的農戶認為家庭飲水來源的獲取較容易,目前有66.1%的農戶家庭有自來水,取用河水的僅占23.2%。在物質資本方面,受訪家庭戶均住房面積為121m2,約91.7%的家庭都擁有現代化的家用電器(圖2),其中電視、洗衣機、冰箱占多數,2%的農戶家庭裝有空調,可見農牧民家庭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
金融資本:在金融資本方面,被調查家庭的年均收入9925元,農牧民的收入普遍較低、可利用的資本較少,使生計模式轉變較困難。具體來看,在家庭年均收入結構中,農業性收入為10809元,大部分家庭收入仍以畜牧業為主,生計方式單一,對生態環境的依賴性強,生計模式轉變成本較大;經營性收入為8067元,工資性收入26606元,外出打工、非農牧業經營等受到年齡、健康狀況、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制約,加重了生計模式轉變的難度;財產性收入為992元,在大部分農牧民家庭中,對土地的依賴性非常強,使土地流轉困難、鮮有利息等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為1311元,其中退耕還林補貼占比51.3%、生態獎補占比29.2%,占到家庭總收入的13.0%,各類補貼的額度低、覆蓋面窄、政策效果不太明顯。政府扶貧對農牧民家庭收入沒有影響或影響較小的占76.9%。
社會資本:在社會資本方面,半農半牧區、純牧區農戶的社會資本以封閉而狹窄的親緣和地緣關系為主,家庭成員中如果有擔任村組干部的,他們的社會資本相對較富裕、獲取信息的渠道相對較廣,社交圈也有所擴大。從地緣資本來看,通過對受訪地區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本的調查分析顯示,90.6%的受訪者表示教育資源的獲得較為便利,90.3%的受訪者指出農牧區或社區附近都有相應的衛生所,醫療較便利。從其家庭支出來看,基于地區特殊的人情文化,受訪者家庭平均人情往來支出約占家庭總支出的41%,充分體現出地區豐富的地緣社會資本。從親緣關系來看,通過對受訪者金融借貸分析,發生過金融借貸的農戶為75.5%,其中通過親戚朋友借款的占34.1%,說明親緣關系在當地社會資本建立過程中的重要性;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借款的占65.9%,說明地區農牧民社會資本正在不斷擴大。
農牧民的生計資本影響決定著他們采取的生計模式,人力資本的不斷提升使農牧民逐漸擺脫了以往單純“靠天吃飯”的生計活動,能較好地把握經濟機會,將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生計模式更加多樣化。農牧民擁有的金融資本、自然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變化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生計策略路徑;現代化信息和技術的進入,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地區“低水平均衡陷阱”,為地區農牧民打開了一扇通往新型活動領域的大門,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環境,降低了農牧民對自然資源環境的直接依賴;同時,社會資本的豐富也為農牧民生計模式的轉變提供了新的可能。從以上分析可見,農牧民的生計資本在他們的生計模式選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要改變地區生態環境和貧困問題的雙重惡性循環,生計資本的提高是基礎。通過生計資本的提高,可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生態環境改善,實現地區經濟和生態發展的雙贏。
2 農牧民生計模式對區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分析
2.1 農牧民生計模式日趨多樣性

問卷分析顯示,農戶家庭的生計多樣化指數達2以上的約有86%,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地區農牧民家庭在應對生計風險的能力在不斷增強,其中生計多樣化指數為2的達到49%(圖3)。農牧民家庭多樣化生計指數的提高,一方面表現在農牧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脆弱性不斷降低,農牧民有能力應對自然資源的變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體現在地區生態環境壓力釋放,有利于地區生態環境的恢復和建設。

圖3 農牧民家庭多樣化生計指數
2.2 畜牧業經營代際傳遞意愿降低
根據相關研究,目前牧民的草原畜牧業經營代際傳遞意愿總體是較弱[3]。調查發現,農牧民家庭生計多樣化呈現隔代特點,父母輩以農牧業生產為主,占主要就業方式的45%,外出打工約占32.5%。目前子女代繼承原有傳統農牧業方式的僅占20%,子女在接受教育的占71.7%,其中43%為大專及以上文化水平。分析這一現象發現,農牧業子女代際傳遞意愿較低,一方面是畜牧業經營收益低,另一方面是農牧民尋求其他生計模式的能力變強。調查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代化思想的進入,農牧民的社會價值觀念在轉變,希望通過教育來轉變“靠天吃飯”的生存生活方式。同時,通過現代化教育,農牧民子女有了除畜牧業經營之外的其他生計能力和更多的就業選擇,很少愿意去經營農牧業[3]。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地區未來人口的流動趨勢,為牧區現代化、城鎮化發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政策空間。通過人口轉移,可有效緩解地區生態環境承載人口的壓力,降低農牧民的生活方式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沖突和矛盾。
2.3 農牧民對生態環境感知與適應意愿增強
不同區域的農牧民對生態環境變化的感知見表1。從表1可見,半農半牧區、牧區、城鎮的生態感知方差在0.05的水平上不顯著,說明不同區域的農牧民對生態感知沒有顯著的差異(P1=0.207、P2=-0.136),也說明生態環境變化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農牧民的生產生活[4]。數據分析表明結果顯示,不同區域的農牧民對生態環境變化的敏感度不同[5],半農半牧區的農牧民對氣溫、降雨的變化敏感,認為氣溫呈升高趨勢的占68.8%,無變化的占6.3%,說明生計模式依賴于自然資源的農牧民對生態環境變化關注度更強也更敏感。

表1 不同區域的農牧民對生態環境的感知狀況
基于地區濃厚的宗教文化和特殊經濟發展背景,分析川甘青地區農牧民的生態保護認知度(表2)。占54%的農牧民認為發展經濟和生態保護同樣重要,其中71.4%的人愿意為了地區生態環境的改善而相應的犧牲家庭經濟收入,只有28.6%人有點抵觸情緒;44%的農牧民認為保護環境比發展經濟更重要,80%的人愿意為了地區生態環境的改善而相應地犧牲家庭經濟收入,反映了生態環境惡化已經使農牧民自身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因為生態環境惡化已經嚴重困擾了農牧民的生產生活。同時,農牧民對生態環境變化的適應意愿也在不斷增強,大部分農牧民認為生態環境改善是以今后的經濟發展為前提的,因為只有生態環境改善了,地區經濟發展才能提高;也有部分農牧民反映,他們之所以弱化生態環境保護的意愿,是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對基本生活的需求,如果有更好的生計模式,他們也不會無節制地索取生態資源,造成生態環境的惡化。從以上的分析可見,目前生態環境的變化已經足以提高農牧民應對生態環境變化的意識,也增強了農牧民自身對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認識,間接減低區域生態外部環境的脆弱程度,促進區域發展良性循環。

表2 農牧民生態保護認知
2.4 農牧民生態環境參與意識提高
在農牧民對生態環境變化和生態保護的認識,通過電視、網絡等現代化設備了解的農戶為46.4%,通過當地喇嘛、寺廟等活動宣傳了解有關生態方面知識的占25%。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現代化文明的相互交融并沒有改變地區的傳統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寺廟等宗教活動在人們生產生活領域仍然占據著一定的主導地位(圖4),如禁忌殺生,忌對神山、圣湖等傳統生態保護習俗仍然發揮著作用。進一步深入探析發現,傳統宗教文化雖然仍是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作用已大不如前(圖5)。

圖4 農牧民生態環境認知渠道

圖5 各級主體生態環境保護作用的發揮
農牧民認為政府在生態環境保護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占比為41.7%,30.6%的人認為生態保護需要政府、寺廟文化、個人的共同參與,三種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僅11%的人認為目前政府在當地生態環境保護中比寺廟的信仰教義更具有引領力。分析其原因:一是隨著外來文化、生活方式和理念的進入,宗教文化傳承在下一代身上已有所弱化;二是在寺廟、行政和金錢的博弈中,寺廟力量仍處于劣勢;三是隨著旅游產業的開發,外來流動人口的進入帶來了更多的“現代化垃圾”,已不是宗教力量所能控制的。因此,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善,需要政府部門、環境保護組織、地方性傳統民俗組織和群眾的共同參與。
進一步了解居民生態活動參與和環保意識(圖6),56.3%的居民會積極參加地區組織的生態保護活動,如村里、寺廟成立的生態環境保護協會,政府組織村民下村撿垃圾,農牧民的生態環保意識在不斷提高。一方面配合政府的相關規定主動減畜;另一方面成立了生態文明志愿隊,大家每年或固定期限組織開會討論如何保護環境,還建立了相應的監督管理機制——村規民約,通過村規民約來解決草場超載問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圖6 生態參與情況調查
2.5 農牧民可持續生計困境
一般而論,生計模式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人與環境相互平等,過分向自然界索取資源的行為將打破自然界運行的平衡狀態,結果并非人與自然的利益最大化。經過研究發現,川甘青三省八縣農牧民的可持續生計困境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共同影響,呈現出空間差異性、長期性和代際傳遞等特征。
可持續生計資本稟賦低:大量研究表明,各資本要素是農牧民應對風險策略最顯著的因素[7]。從目前來看,雖然農牧民資本稟賦有向好的趨勢,但還不足以提高農牧民的可持續抗風險能力。從人力資本看,地區教育水平仍處于低水平均衡狀態,綜合素質整體偏低、人才匱乏,呈現明顯的斷層現象,父輩及以上文化程度較低,使其轉產就業、尋找新的生計途徑面臨較大的困難;從自然和物質資本看,農牧民所依賴的自然資源稟賦逐漸降低,進入“資源詛咒”困境,傳統的生計模式難以延續,而重新搭建又顯得異常困難;從金融資本看,農牧民不但自身的金融資本薄弱,而且可利用的社會金融資本較少,不能滿足其生產生活貸款需求。從社會資本看,雖然外來經濟和文化流通打開了地區與外界交流的渠道,但基于地區農牧民居住較分散,傳統農牧民可利用的社會資本趨于邊緣化。
轉產就業困難: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呈現較復雜的互動影響機制,基于代際公平的視角,當前農牧民生計模式應是與生態環境的修復和保護相適應的過程,轉產就業就顯得至關重要,但區域缺乏一定的轉產就業機制。一方面,隨著地區生態環境約束和牧區城鎮化的推進,大量牧業勞動力開始向第二、三產業轉移,但僅限于在本地市區。加之受限于年齡、健康狀況、文化水平等,少數民族外出打工面臨著技能問題和語言不通的障礙。同時,區域內經濟發展緩慢、容納就業能力低,農牧民轉產就業面臨著一些困難。另一方面,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義務教育的擴大,地區教育水平不斷提升,以知識水平提升為平臺的牧民子女逐漸遠離農牧區經營。在調研中發現,教育水平提升上去后又面臨著新的就業問題。從對甘南師范學院的師生訪談中了解到,目前大學或大專畢業后的學生傾向于回到自己家鄉,報考公務員或到高校當老師是他們就業的最好選擇,但由于職位少、競爭激烈,一定程度上存在就業困難。
政策“擠出效應”:除了上述因素,政府政策也是影響農牧民生計的重要因素。政府政策在區域系統適應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6],如政府采取的禁牧休牧措施,一方面促使農牧民不斷減畜,使他們面臨生存壓力,脆弱性加強;另一方面促使農牧民逐漸向非農產業轉移,尋找多元化的生計模式,但相關經濟政策的延時性效應加劇了環境變化對農戶生計的影響。同時,政府的政策還會涉及到與農牧民之間的利益均衡,使當地農牧民被動接受政策調控的影響,無法將擁有的有限生計資本轉化為新的生計資源,產生政府政策對農牧民的“擠出效應”,從而出現“生計困境”。
社會保障不健全:社會保障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最后的兜底政策,是我國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防線,調節社會公平。就目前民族地區的發展來看,基礎設施落后、社會服務水平較低、因病因災返貧程度較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主要體現在:一是醫療體系不健全,覆蓋水平相對較低,保障能力弱。據衛生部數據顯示,目前少數民族地區的醫療保障還遠遠不能滿足其需要,“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還普遍存在。統計資料顯示,在精準扶貧建檔立卡戶的統計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貧困戶約占建檔立卡貧困戶總數的1/2,在各種致貧原因中,因病致貧在各地區都排在首位。在調研中發現,形成家庭貧困及欠債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家里有病人。據了解,有些家庭為了給病人看病買藥都要花費數十萬元,這對當地農牧民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而這些費用并沒有醫療保障兜底。二是養老保障機制缺失。我國老齡化人口現象在少數民族地區不可避免,目前該地區還是家庭養老為主,依托于土地(耕地、草場)作為家庭居家養老的直接經濟來源,但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自然災害頻發等經濟社會因素,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在不斷弱化。加之民族地區家庭規模在不斷變小,老年贍養比例在不斷提高,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重要而緊迫。
3 政策導向
構建農牧民內源式發展動力機制:①政府的前期引導是關鍵,社會組織的互動參與是助力,農牧民自身能力提升是核心[8]。建立川甘青跨區域政府定期聯絡制,統一規劃道路的互聯互通,旅游線路聯動,具體業態錯位發展。②充分社會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的職能和市場缺陷。③強化農牧民自身技能培育,包括其轉產就業技能、市場參與能力、組織能力和心理適應能力。如在區域濃厚的傳統文化下,農牧民應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意愿和對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接受能力。
構建科學合理、運行有效的農牧民可持續生計資本框架:①保護和提高自然與物質資本的生態環境恢復和建設模式,如繼續加強綜合治理和生態保育,加強生態系統功能恢復的人工培育。②推進金融資本提升的綠色產業發展模式。加大地區生態農牧業的發展,探索農業規模化經營、畜牧業品種改良、農牧產品深加工等現代化模式。在產—經—銷一體化的產業發展模式下促進農牧民的深度就業,擴寬農牧民的收入渠道。③完善人力資本提升的創新就業模式。如開設“農家樂”、“藏家樂”等,通過住宿餐飲一體化服務,引導農牧民對地區蟲草、野生菌類等進行合理采集,對生態藏豬等進行培育和養殖,在增加農牧民收入前提下提高其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④強化社會資本提升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充分尊重牧民意愿, 因地制宜地進行散居、聯戶、小區聚居、城鎮聚居等多種模式的定居點建設;完善勞動力市場,為農牧民提供開放的就業信息平臺等。
完善雙重困境共治的政策群落:①完善地區生態環境補償政策群。探索開展國家、跨區域和本區域三個層面的補償,提高補償系數和補償標準。②規范多元主體復合參與政策群。向寺廟、農牧民和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征求意見,尤其要重視地區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力。③強化要素支撐政策群。強化科技引領,促進“官產學研”科技聯盟的形成。強化人才支撐,實施人才支援計劃、培訓計劃,將本土人才的培養與外地人才使用結合起來。強化信息服務,以信息技術深刻變革該區域的發展方式。④完善社會保障政策群。構建以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救助為基礎,以商業保險為支撐的城鄉社保體系,對長期在城鎮務工的農牧民實現養老、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應保盡保。
[1]陳艾,李雪萍.脆弱性—抗逆力:連片特困地區的可持續生計分析[J].社會主義研究,2015,(2)∶92-98.
[2]趙雪雁.不同生計方式農戶的環境感知——以甘南高原為例[J].生態學報,2012,(11)∶6776-6787.
[3]孔德帥,胡振通,靳樂山.牧民草原畜牧業經營代際傳遞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內蒙古自治區34個嘎查的調查[J].中國農村觀察,2016,(1)∶80-85.
[4]吳孔森,楊新軍,尹 莎.環境變化影響下農戶生計選擇與可持續性研究——以民勤綠洲社區為例[J].經濟地理,2016,(9)∶141-149.
[5]譚淑豪,譚文列婧.氣候變化壓力下牧民的社會脆弱性分析——基于內蒙古錫林郭勒盟4個牧業旗的調查[J].中國農村經濟,2016,(7)∶67-78.
[6]任新民.“政策催化”: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中一個被忽視的問題[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7)∶33-38.
[7]史月蘭,唐卞.基于生計資本路徑的貧困地區生計策略研究----廣西鳳山縣四個可持續生計項目村的調查[J].改革與戰略,2014,(4)∶83-87.
[8]趙鋒.可持續生計與生計動態能力分析:一個新的理論研究框架[J].經濟研究參考,2015,(27)∶81-87.
[9]張銳,張寶成.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及政策分析[J].前言,2011,(7)∶15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