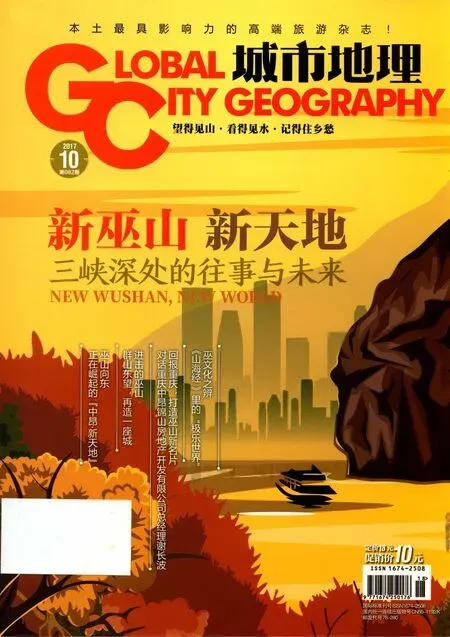詩歌筑城記
城市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當然這其中也有對詩歌的影響。但我想說的是,在城市影響詩歌之前,首先是詩歌影響了城市。城市對詩歌的影響,實則是詩歌自身遇城之后的反作用。因為在沒有城市的年代,詩歌已然存在了——她存在于廣大鄉村的巫語中、廣大勞作的歌謠中。為此,那時城里的采詩官就紛紛出城,為君王采擷或美麗憂傷,或壯懷激烈的詩歌。
采詩官應該知道,他們棲居的城,也是詩歌筑出來的。城市是文明的產物,而文明之所以為文明,在它的幾個基本構成要素中,宗教祭祀和文字堪稱重要的兩項。在沒有專職詩人的時代,巫師,亦即最初的兼職詩人,是中國原始宗教的呈現與布道者,當他們與后來發明的文字相遇后,口口相傳的詩歌便在植物和動物皮骨上,成為書面詩歌。
比如,成都城最先的形態是巫。因為巫師是那個時代的導師和知識集大成者,所以巫師在哪里搞祭祀活動,人眾就跟到哪里。這樣,人眾的聚落就產生了。最先的聚落叫“里”,如成都的赤里、錦里、石犀里等。里,也就相當于現在的村落。有了里,自然就有了市,集市的市,市場的市,有了交流與走動。里、市一發展,就成了片,成了邑。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就將邑變成了都。由此,成都就有了“一年成聚,兩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筑城發展脈向。二三千年來,這座唯一不更城名、不變城址的都城,竟沒人能夠確證是誰主持的筑城事體。但其實,成都就是詩歌筑的,除此無二。
我們再去翻一翻記載這一時期的重要文獻《華陽國志》《蜀王本紀》,就會看見詩歌的神思漫天飛揚——其中諸多片段,哪一個不是詩?
但這還只是詩歌對城市的基本建設,因為畢竟巫對詩歌的提純還不夠高。成都要想成為大城,必須要在時間的流動中煉功、養神、聚氣,必須要等待大詩人從天墜,棲于城。古蜀過了,秦過了,終于等來了西漢,等來了譽滿全國的大詩人、大學者司馬相如、文翁、嚴君平、揚雄。跟著的事實是,西漢中晚期,成都便一躍成為僅僅略次于國都長安的全國第二大都市,以及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唐宋的成都,當是詩歌繁榮的朝代。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稹、薛濤、蘇氏父子、陸游等等大詩人,無不與成都有關。有一個術語,叫“揚一益二”,說的是唐宋的工商業中心,揚州第一,成都第二,兩座城市的繁華富庶地位,超過了長安、洛陽、汴京、臨安。宋以降,元、明、清三朝,成都就出了個楊升庵,成都城的地位,自是一落千丈了。這真是詩興城興,詩衰城衰。
我們對司馬相如之前的成都缺乏地標對位,缺乏真相,弄得滿眼滿腦的朦朧與迷霧,那就是因為在時間的清場中,詩歌的不作為,尤其是詩人的籍籍無名。比如,我們要了解籌邊樓,還必須吟哦薛濤的“平臨云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要找諸葛亮的祠堂,順著杜甫的詩行就可以了:“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讀一讀陸游《梅花絕句》:“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就明白了宋代成都的梅花方位與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