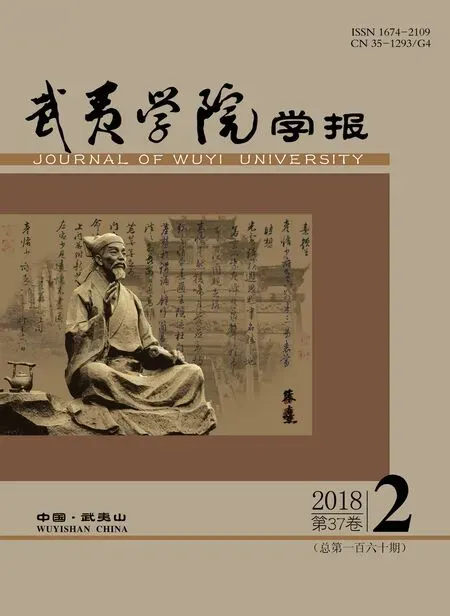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的思考
黃曉娟
(福州大學 法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并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它的實施將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各類民事主體保護起到重大作用,是我國法治化建設的一大進步。《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了救助人實施救助行為免于承擔責任的情形,以及《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三條救助人有請求受益者適當補償的權利,這些規定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救助人對救助行為的顧慮,鼓舞了救助人救助的信心。然而這一規定與社會復雜的現實情況相比仍過于簡單,第一百八十七條僅從反面免除了救助人責任,第一百八十三條的適當補償僅起到彌補救助人損失的功能,對救助人救助行為的倡導力度不夠,筆者認為應當從正面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肯定救助人對救助成功的行為享有酬勞,更有利于對見義勇為美德的發揚。
一、關于救助人“報酬”請求權制度的概述
(一)現行“報酬”請求權制度規定及評價
1.法律對“報酬”請求權規定存在不足
我國目前對見義勇為的法律規定主要集中在《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三條、《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十五條、《侵權責任法》第 二十三 條以及《民法總則》第一百二十一條,《民通意見》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五十七條。救助人的請求權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通過無因管理制度索取費用,二、通過法定補償義務求償。然而我國立法關于救助人“報酬”請求權沒有涉及,《民法總則》第一百二十一條對無因管理提起的費用請求權僅僅為管理人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支出的必要費用,這些必要費用即《民法總則》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的在為管理或服務他人事務直接支出的費用,以及在該活動中受到的實際損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十五條及《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三條、《侵權責任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僅當救助人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受到傷害的,受益人在受益范圍對救助人補償,可見,無論是利用無因管理制度還是法定補償義務救助人都無法享有“報酬”請求權。也就是說當救助人成功避免了他人人身、財產受損或擴大,且自己也遭到損害的情況下,只能根據以上法條索取自己為救助行為付出的必要費用,以及實際損失,救助人通過付出辛勞的行動避免了受益者的人身、財產損失,卻無法獲得一定的“報酬”,這不僅有違常理,而且會使得見義勇為人的積極性大打折扣,受益人的權益無法得到實時維護,不利于傳統美德的發揚。
2.條例對部分救助行為存在獎勵空白
有人認為我國各地相繼出臺見義勇為保護條例來獎勵見義勇為行為,這足以鼓勵救助人積極實施救助行為[1],但縱觀這些條例,如《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第二條指出見義勇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義務以外,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與各種犯罪行為作斗爭或搶險救災的行為。《山東省見義勇為保護條例》第二條指出本條例所稱見義勇為,是指非因法定職責或者約定義務,為保護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與違法罪行為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各地對見義勇為行為的概念及獎勵標準不一致,首先救助行為基本上僅包括與制止違法犯罪或者搶險救災等協助公權力機關行使維護公共利益的行為,對于意外事故的救助或救死扶傷,搶救貴重物品的行為不僅沒有獎勵,也沒有救濟[2]。因此,對于意外事故的救助和救死扶傷等條例沒有說明的行為存在公法激勵空白。另外,從實踐中來看,公法對獎勵見義勇為的前提條件十分苛刻,大部分地區只在見義勇為對公共利益有重大貢獻的前提下才嘉獎見義勇為者,且見義勇為人申請獎勵的程序也十分復雜,通過公法來達到鼓勵社會見義勇為的效果不明顯。
3.工傷保險、見義勇為基金適用困難
工傷保險僅適用于職工見義勇為受到傷害,適用范圍非常有限,對于非職工見義勇為則不在此列。且工傷認定難度大,保障標準低。見義勇為基金在我國尚處于嘗試階段,財政投入少,社會捐贈不積極,實踐中適用的情況很少。首先,通過上述行政救濟或工傷保險保障或見義勇為基金都無法完全保障見義勇為人的權益,或無法保護所有見義勇為人,或無法實現充分救濟。而且,由于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經濟水平尚有不足,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對見義勇為者的全面救濟仍然需要很長時日。因此,將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作為這一時期的過渡手段,也不失為一種良策。其次,受益人接受了幫助并挽回了損失,卻只需要在無侵權人或侵權人無力償還的前提下,僅對救助人付出的必要費用和直接損失部分補償,受人救助卻坐享其成難道就是傳統美德的體現嗎?最后,還有人認為受益人的適當補償義務尚且無法完全履行,“報酬”答謝顯得沒有意義。筆者認為,適當補償義務是根據損益相當原則對救助人損失的彌補,而“報酬”具有恩謝的性質,是受益人對救助人無私幫助的感謝,二者性質不同。因受益人履行不能而否定確立“報酬”請求權的立法,長此以往,也會令受益人對于他人的救助行為視若無睹、認為理所應當。又或者將本應由自己表達謝意的責任推卸給公權力機關或者公共機構,同樣不利于傳統美德的發揚。因此,筆者主張救助人除獲得必要費用償還、實際損失補償以外,還應當享有對其實施救助行為成功的一定比例的“報酬”請求權。
(二)理論界存在對救助人“報酬”請求權的片面認識
學界對是否賦予“報酬”請求權的觀點持截然相反的態度,否定“報酬”請求權的理由如下:一是認為從各地實行的見義勇為保護條例對救助人的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來看,以公法獎勵實質上是在強調救助行為本身的道德屬性。二是認為如果對救助人“報酬”請求權予以法律上的確認容易導致一些人以獲取“報酬”為目的進行活動或者利用救助行為之名行謀取利益之實將不利于我國傳統道德觀念的發揚[3]。三是認為救助行為是基于利他主義心理而實施,理當不得請求“報酬”[4]。四是認為此種可能取得而未取得之利益,屬于消極損害,為管理人自始甘愿犧牲,應不得請求賠償[5]。筆者認為這些理由不夠合理,第一,各地條例對見義勇為的獎賞其實只調整國家與見義勇為者之間的關系,即規定國家機關對見義勇為者的行政保護和獎勵措施,與見義勇為者、侵害人、受益人之間的民事私法關系有所不同,這些民事私法關系應由民事基本法來調整,從而實現對見義勇為公法和私法調整的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第二,法律的制定以道德為參考標準,道德規范在某些程度上是法律更高層次的追求,而法律順應社會的發展,不可能超越社會現實去保護一切為社會道德所倡導的文明要求。因此,法律的制定又有其獨立性,應當與社會發展相適應[6]。首先,重視道德的發揚與事后獲取“報酬”并無沖突,按照常理,救助人在面臨其人身、財產遭受損害的危境之下,自己無法妥善解決這一困難,通常會尋求最近的幫助,而此時救助人對其提供幫助,這不僅符合救助人尋求幫助的愿望,同時通過幫助行為使受益人避免了人身、財產受到損失或進一步擴大,救助人實際上付出了勞動,而受益者獲得利益,理應給予一定比例的“報酬”,這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則,因此賦予其“報酬”請求權具有一定意義[7]。其次,救助人雖然救助他人之時主觀上有為他人事務服務的心里,但這并不妨礙其在成功救助他人之后請求一定的“報酬”答謝,即使救助人事后期待“報酬”回報也不能因此否定其傳統美德的缺失。傳統的助人為樂、做好事不求回報的道德觀念固然應當發揚,但過于重視道德的約束卻不關注人的正常需求,反而以道德的名義綁架個人內心需求,長此以往難免造成普遍的虛偽,不利于個人內心自由的表露。最后,從見義勇為的本義觀來看,見義勇為強調的是救助人在他人人身、財產面臨危險之時,不顧個人權益可能受損的危險,以英勇的態度去幫助他人。這一概念以救助之時救助人心理狀態為核心要件,認為其應當具備英勇幫助他人的決心,而沒有強求救助人在事后不可以就自己的成功救助行為獲得“報酬”,況且,權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救助人的“報酬”請求權可以選擇事后請求“報酬”也可以選擇不求回報,這樣的法律規定并沒有背離追求美好道德的目標,而且,對于遺失人而言,支付“報酬”也符合“受人點滴,涌泉相報”的傳統美德的要求。
二、賦予“報酬”請求權的法理基礎及依據
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不僅具有法理上的根據,也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
(一)公平原則的根本要求
首先,依據現行立法,受益人負擔的償還必要費用及實際損失僅僅針對見義勇為人行使救助行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非對應于見義勇為者成功避免受益人權益受損的行為,這無疑違背了公平原則。公平原則要求民事主體雙方權利義務相一致,任何一方主體都應當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作為個體的市民都有追求個人利益的自由,每個個體在實施救助行為時都會考慮是否可以得到公平對待。雖然《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七條免除了救助人因過失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民事責任,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救助人利益,但對于過失造成受助人損害的行為尚可通過該規定免除其責任。那么,對于在救助行為中謹慎又盡責的救助人卻沒有任何的肯定,容易使救助人之間產生不公的心理,從而不愿意在救助行為中全力幫助受助人,長此以往也不利于見義勇為風氣的健康發揚。其次,我國理論界存在普遍認可拾得人報酬請求權的觀點,僅對財物提供照管幫助的人尚可享有報酬請求權,更何況拯救更高法益的救助人卻無法獲得報酬,也不符合公平原則的要求。因此,法律有必要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平衡各方權益,每一個見義勇為人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義。
(二)尊重人性私欲的正常表達
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的人是合理追求自已利益的經濟人。救助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保護了受益人的利益,理所當然期待得到受助人的回報,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每個市民內心的價值追求,即使救助人索取“報酬”是出于私欲,也不能因此以道德觀念譴責其合理表達自己需求的自由,而去肯定受助人不給于回報的獲利行為,給予其法律上的依據。同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合理追求自己利益的人和一個理性的,能夠獨立地、自由地表示自己意思去設定權利義務關系的民法人是一致的[8],法律應當保護一切人表達追求自身合理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忽視人性私欲的法律既沒有價值也沒有生命力,因此,應當充分尊重個人對私欲的合理期待,肯定“報酬”請求權的正當化。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不僅能使見義勇為者個人利益得到實現,而且通過從正面肯定其救助的價值,增強人們的社會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然更能鼓舞見義勇為行為,這樣的良性循環應是我國法律追求的目標[9]。
(三)符合法律對效益的追求
隨著經濟的快速運行,效益價值在社會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這不僅體現在市場交易中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也充分體現在市民社會基本的活動中。救助人“報酬”請求權恰恰實現了法律對效益價值的追求,具體可從以下角度體現:首先,賦予“報酬”請求權會使得救助人追求合理利益的愿望得到肯定,極大提升救助人行使救助行為的積極性,救助人毫不猶豫的救助行為彌補了受助人尋找幫助所浪費的時間,比如受助人心臟病發等待救援,下班途中的醫生及時采取緊急措施幫助其度過生命危險。又或者孤身一人的溺水受助人在路人的營救下順利上岸等等,諸如此類的救助行為都在幫助受助人與死神爭分奪秒,顯然提高了受助人獲救的概率。其次,賦予“報酬”請求權能促使救助人更加謹慎合理地實施救助行為,沒有“報酬”的激勵,救助人通常在考慮自身安危的情況下不會盡力去搭救受助人,而其“報酬”的數額與救助人救助行為的合理性及效果相關聯,救助人顯然會更加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行為,避免造成受助人進一步損失。最后,救助人提供救助行為往往與其自身利益有所沖突,如耽誤救助人上班時間或其他商業活動,因此,對救助人適當的“報酬”給付也彌補了救助人利益損失,長此以往,有助于社會形成互幫互助的風氣,提高社會活動的效益性。
(四)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不會令雙方利益失衡
受助人在救助人受損的范圍外額外給予其 “報酬”,不會令雙方利益失衡,也不會使其成為救助人獲取利益的手段。首先,從近年來的司法案例來看,提起見義勇為訴訟的基本上涉及救助人重大人身損失或傷亡,見義勇為或挽救生命,或避免造成重大財產損失擴大,法院通常會考慮救助人受損程度、過錯大小和受益人受益情況及經濟情況,以及救助人所獲得的行政獎勵、社會救濟或工傷保險等等,判決受益人適當補償救助人損失,盡量將受助人的補償降到最小。參見陶小波訴閩侯縣博來工藝品有限公司見義勇為受害責任糾紛案①,救助人實際受損僅醫療費就有156767.87元,而且還因救助行為喪失部分勞動力,法院最終僅判決受益人承擔50000元的部分補償。且不論法院的判決是否合理公平,僅從補償數額來看,受助人最終補償的數額都不會違背最低限度補償原則。即使補償救助人損失后,又賦予救助人“報酬”請求權也不會過分增加受益人負擔。其次,地方獎勵見義勇為者的金額也不足以令救助人財富增值,如杭州市對犧牲的見義勇為者的最高獎勵金額也才10萬,這與見義勇為者所受損失相比仍然杯水車薪。因此,見義勇為者的“報酬”請求權給予法律上的肯定并不會誘使救助人以此謀取利益。
(五)符合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
近年來我國漠視見義勇為的現象頻頻出現,為重振社會風氣,我國諸多學者主張立法肯定該“報酬”請求權,這不僅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也是提高國民素質的途徑。國外認可“報酬”請求權的行使,但對其主體限制嚴格,承認專業人士享有“報酬”請求權,如美國判例法規定醫生和護士在保護生命、身體的情形才享有就其時間、努力和專門技能提出的“報酬”請求權,《歐洲統一私法框架》認為專業人士若以其職業標準和能力完成救助活動有權依據無因管理制度獲取“報酬”。國外出于反對好管閑事原則,對“報酬”請求權的認可仍十分謹慎,不贊成除職業人士以外的一般人享有“報酬”請求權,而且西方大部分國家工業化程度高,階層等級分明,給予職業人士“報酬”請求權容易為市民所認可。這是由一個國家特有的歷史傳統和國民接受度所決定的。我國自古以來推崇“他人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美德,而且從民國人人平等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不以職業區分報酬請求權的主體,適合我國現實條件。與國外不同,我國具備發展救助人“報酬”請求權的社會土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鑒于這些國家對“報酬”請求權的規定,我國應當確立適合本國社會風俗的法律規定。從將救助行為規定為法律義務的困境中轉換思路[10],以明確救助者的“報酬”請求權迂回地實現公眾對救助行為的自覺遵守,實現法律真正的引導價值。
三、“報酬”請求權制度的設計思路
當前很多學者提出要把救助行為設定為法律義務,對于不救助的行為應當施以法律懲戒,筆者認為以強制性規范達到社會積極救助的目的有些操之過急,不妨用賦予“報酬”請求權這一倡導性規范,讓市民自由選擇是否施以援手,更為妥當,也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在構建“報酬”請求權制度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一)“報酬”數額的具體標準
確立“報酬”請求權,首先應當考慮“報酬”數額如何確定問題。無論是英格蘭的法律規定,還是美國的判例法都認為“報酬”應當要固定數額[11],筆者認為,固定的數額縱然能避免法官自由裁量的隨意性,但不分救助的法益之價值,機械地判定固定數額,無論救助何種法益,最終獲得的“報酬”都一樣,會導致救助人放棄救助價值更大、更需要救助的法益,而選擇那些救助難度小的法益。另外,不同的法益具有的價值也不盡相同,若適用統一的數額給付,也不符合價值規律,容易形成僵化的判斷標準模式。而且,救助人提供救助的方式根據被救助人法益損害的程度而變化,如果僅僅以提供服務的“合理的”或公平的市場價值確定,必然無法完全概括所有的救助方式。根據救助的法益可以將救助行為歸為兩類,一是挽救財產損失,二是救助生命。當事人可以協商的,以協商的數額為準。若協商不成的,以該行為對整個救助活動的作用力判斷。對于挽救財產損失的“報酬”以救助人挽救成功的財產為上限,參照日本民法按比例原則規定拾得人“報酬”來確定救助人“報酬”[12]。由于生命、健康的價值無法估量,見義勇為與救助行為在救助生命這一法益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可以參考當地見義勇為獎勵條例對不同程度的救助行為的規定確定“報酬”的數額。但是,無論挽救財產或人身損失,最終受益者所給付的數額都不得超過其受益范圍。
(二)“報酬”請求權的適用條件
由于經濟主體的偏私性和追求權利最大化必然帶來損害他人權利、違背社會公德等一系列社會問題[13],故應當明確行使“報酬”請求權的前提條件,才能最大限度發揮法律的引導作用,同時又不會任由救助人濫用救助行為索取“報酬”擾亂社會秩序的安定。
1.主體類型
國外普遍認可職業人士或在營業范圍內從事救助行為享有“報酬”請求權,這一觀點也被我國大部分學者所接受[14]。賦予職業人士或營業范圍內從事救助行為的人“報酬”請求權符合市場交易規則,但同時也應當賦予其他救助主體“報酬”請求權。應當注意的是,公權力機關人員由于負有維護公共安全的職責,特定義務之人如父母子女之間存在救助義務,若被賦予“報酬”請求權有違法律的規定,因此這兩種類型之人從事的救助行為無權獲得報酬請求權。但并非完全無法獲得“報酬”請求權,可以借鑒意大利救助法關于救助行為時間的確定,若負有法定職責、特定義務之人行使了與其職責、義務不同的救助也可以享有“報酬”請求權,這同樣彰顯法律的人文關懷,如警察在非上班期間救助困于火災中人。
2.主體的限制
行使“報酬”請求權的主體只能是見義勇為中的救助者本人(本人為未成年人的由其監護人行使,本人已亡的為近親屬),給付“報酬”的只能是受益人,從“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延伸,被救助人受益與救助者的幫助行為具有因果關系,因此在“報酬”給付這一法律關系中受益人與救助者才是真正的當事人,二者之間形成權利義務的對等關系。若存在真正侵權人,受益者可通過另訴向真正侵權人追償損失。
3.適用前提條件
大部分國家基于對他人事務不得隨意干涉的理由否定救助人享有“報酬”請求權,賦予“報酬”請求權有可能會被利用謀取私利,因此,應當明確“報酬”請求權適用的條件。(1)面臨財產、人身受損的危險且不違背受助人可得而知的意思。《德國民法典》明確規定,只要進行救助行為符合本人(受益人)利益或者可得而知的意愿,救助人可以與受托人一樣有權要求償還其支付的費用,該費用包括管理人應得到的酬金費用。對于是否面臨危險與受助人意愿的判斷應以一個理性人的標準為根據,考慮到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不應當被隨意打破,故對普通的無因管理行為不適用“報酬”請求權。因此,對于人身、財產并無面臨損失的風險,或違背受助人拒絕幫助的意思,不適用“報酬”請求權。(2)遵循“無效果,無‘報酬’”原則。應當承認救助人實施救助行為有一定的能力局限性,主張效果論可以阻卻救助人過于沖動施救的行為,使其冷靜分析危險狀況,不盲目施救。另外,《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無論救助是否有效果,受益人都應當對救助人的必要費用和實際損失適當補償,這一規定已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救助人的權益。為了平衡救助人與受助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同時提高救助人救助行為的效益,對救助人“報酬”請求權的行使前提僅限于在救助人的救助行為挽救了受助人的人身、財產,或避免了人身、財產損失的擴大,救助人才可以行使“報酬”請求權,否則,受助人沒有給付“報酬”的義務。
“報酬”是對救助者的體力支出的一種報償,具有恩謝的性質。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之下,賦予救助者“報酬”請求權有利于社會效率的提高,縱然有可能會存在為謀取報酬而提供救助的行為,但這畢竟屬于少數,不能因此因噎廢食而舍棄對多數人權益的保護。另外,由于當前我國精神文明建設存在不足,國民素質有待提高,以賦予“報酬”請求權這一選擇性規范,有助于提高市民見義勇為的積極性,同時,對“報酬”請求權的條件加以限制,規范以救助的名義謀取“報酬”的行為,有利于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循序漸進發展,彰顯法律的引導作用。因此,筆者建議可以在《民法總則》確立救助人“報酬”請求權,規定如下:救助人實施救助行為避免受益人利益受損或擴大的,有權獲得“報酬”。另外,可以在適用《民法總則》的司法解釋里規定救助人享有“報酬”請求權的適用條件,以供法官作為裁判依據。
注釋:
① 福建(2016)閩0121民初2357號。
參考文獻:
[1] 陳楚楚.淺析見義勇為及其行為人法律救濟 [J].鄂州大學學報,2016(5):11-13,2.
[2] 曾大鵬.在民法與正義之間:對見義勇為的三重分析[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49-56,3.
[3]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2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3:88-89.
[4] 黃茂榮.債法各論(第一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394.
[5]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27.
[6] 張文顯,李步云.法理學論叢(第1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8.
[7] 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M].臺灣:三民書局,1985:82.
[8] 章禮強.民法何為:對民法本質追求的思考[J].河北法學,2006(8):20-23,3.
[9] 李玲.論見義勇為中“報酬”的法律調整[J].東方企業文化,2012(1):133-134,2.
[10] 張曉蓮.我國見義勇為立法問題探析:以美國法的比較和借鑒為視角[J].福建法學,2010(4):65-70,4.
[11] 李昊.論英美法上的“好撒馬利亞人”[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4):58-81,15.
[12] 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條文、說明、理由與參考立法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88.
[13] 李瓊.權利邊界、沖突及其衡平[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2012(1):135-138,4.
[14] 賈邦俊.見義勇為行為的民法透視 [J].河北法學,2003(1):28-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