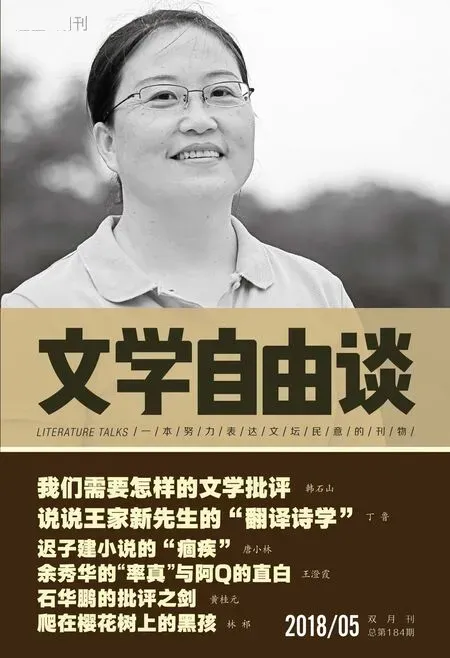石華鵬的批評之劍
2018-03-07 15:38:06黃桂元
文學自由談
2018年5期
關鍵詞:小說
黃桂元
何為批評?批評何為?我估計,石華鵬從事文學批評之初,未必會有多少學理性思考。最近,他把自己的文集命名為《批評之劍》(此書為作家出版社“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之一),讀之,仿佛有劍光逼來,令人炫目。石華鵬把批評視為一種“亮劍”行為,只是隱喻而已。這里,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他習慣于散兵游勇,單槍匹馬,拒絕團伙行為;他不喜歡笨拙的重兵器,文字以輕功見長,不大適合于“核心期刊”;他注重的不是武器,而是“故事”背后隱藏著的“秘密”;最重要的,即使他刀劍出鞘,也只與自己的興趣點——“文學的魅力”——有關,而不會傷及非文學的種種“無辜”。
石華鵬的老家在湖北天門,大學畢業后在福建當文學編輯,現已出版了三部批評文集,并以《故事背后的秘密》入選“閩派批評新銳叢書”。這個過程難言傳奇,卻也絕不尋常。這涉及到了具有文化地理學意義的淵源問題。我想,如果對40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和寫作版圖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對福建這塊“風水寶地”另眼相看,乃至肅然起敬。福建算不上“小說大省”“詩歌大省”“散文大省”,卻絕對是影響深遠、有口皆碑的文學理論批評大省。且不說從古代到近現代,這里曾誕生過朱熹、嚴羽、李贄、嚴復、辜鴻銘、林紓、林語堂、洪業、鄭振鐸這樣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巨子,就當代文學而言,正如王蒙說的,“閩派批評堪與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勢”。“閩派批評”大旗主要是由閩籍批評家扛起的,除許懷中、魏世英、孫紹振、劉……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