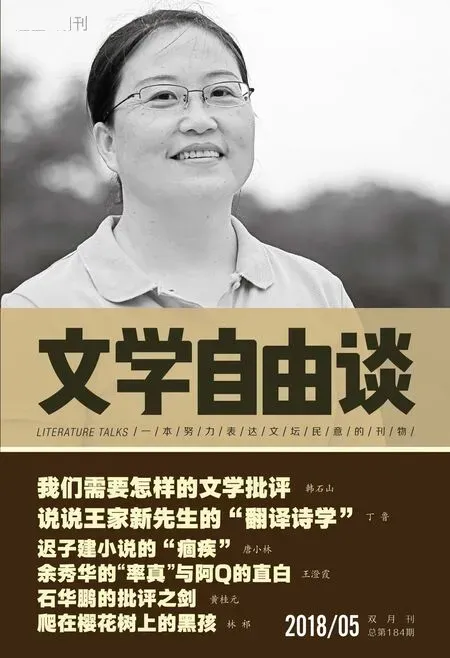銅官窯里詩文瓷
2018-03-07 15:38:06[美]江嵐
文學自由談
2018年5期
[美]江 嵐
古岸陶為器,高林盡一焚。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云。迵野煤飛亂,遙空爆響聞。地形穿鑿勢,恐到祝融墳。
——[唐]李群玉《石潴》
上世紀中期以來,長沙銅官窯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這個名不見正史記載的南方民間瓷窯,為中國古代陶瓷史、對外交流史、湖湘文化發展史,以及唐代文學、商業文化、音樂、書法、繪畫、民俗……等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自五代之后沉寂千年的遺址,用數量驚人的實物證明,這里是世界彩瓷的起點,率先創燒出模印貼花、釉下彩繪,率先在器物上明碼標價、銘文廣告。這個小小古鎮上產出的彩瓷儼然曾經走遍大半個中國,曾經跨洋過海抵達世界許許多多國家。
1998年“黑石號”沉船在印尼勿里洞外海被偶然發現,從沉睡海底千余年的船艙中打撈起中國外銷器具六萬余件,見證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連接東西方的歷史。其中除少量的白瓷、青瓷和金銀器之外,逾五萬余件瓷器出自長沙銅官窯,現大半藏于新加坡。長沙銅官窯,作為與浙江越窯、河北邢窯齊名的中國唐代三大出口瓷窯之一,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在去長沙銅官鎮的遺址博物館參觀途中,我們一行人已經很興奮,嘰嘰喳喳談論了一路。等進了館內,目不暇給,反倒安靜下來。踏過厚厚的陶瓷碎片堆積層,沿依山而建的斜坡式窯床一步步走上去,磚砌的火膛、火門、風道、煙道歷歷依然。模擬的窯火無煙也無聲,卻有光有溫度,烘托著窯底燒結的層層黝黑和殘存的窯具,讓時光急遽錯亂、回溯、轉接——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