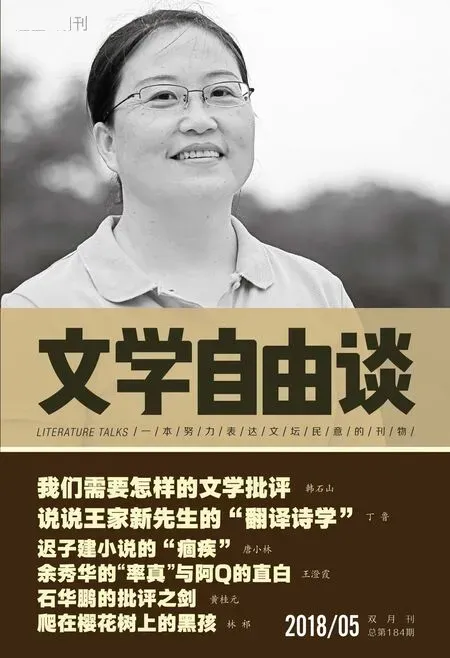在愛丁堡,司各特、彭斯還有J.K.羅琳
狄 青
從格拉斯哥到愛丁堡,直線距離只有80公里,然而,至少給我的感覺是:兩座城市卻是代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蘇格蘭。格拉斯哥實際上更像是一座英格蘭城市,街道的布局走向、房屋的建筑格調,以及時尚的商業化程度,基本上與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翰那些英格蘭城市差別不大。愛丁堡卻不然,它更像是一座中世紀的古老城池被直接平移到了當下,那斑駁的古老城堡的墻面,還有那些仿佛凝滯固化了的傳統文化遺存,都像是一件件歷經歲月浸泡的標本。格拉斯哥這座城市能夠令我想起的文學人物似乎并不多,大約只有英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旗幟性人物、詩人托馬斯·坎貝爾與格拉斯哥有著難解之緣。我曾經起意想尋找詩人在格拉斯哥的故居,遺憾的是,周圍人似乎沒有誰了解這件事。我不清楚,比起街頭的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樂部的巨幅海報,格拉斯哥的文化抑或說文學仿佛都還被局限于那些古老大學的圍墻里。
但愛丁堡不是這樣的,你幾乎在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看到高達61.11米的黑色外檐、通體頗具巖石堅硬質感的司各特紀念塔,感受到這位偉大作家無時無刻不在思考著你的思考、關注著你的關注。作為2004年即被聯合國命名為全世界首座“文學之都”的愛丁堡,文學,無疑便是這座城市的重要標識了;而詩人兼小說家司各特呢,無疑又屬于愛丁堡這一重要標識的標識性人物,盡管這座在我看來至少算不上很大的城市,同樣誕生了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柯南·道爾以及J.K.羅琳這些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家和詩人,但如果沒有司各特,對于愛丁堡這座“文學之都”而言,也難說會是一種圓滿。
在倫敦的時候,我就聽說愛丁堡有一座“作家博物館”,卻不是在愛丁堡的熱門旅游路線上,如果想去瞻仰的話,多半只能自己想辦法前往。不過好在它就位于市中心,就隱藏在“皇家一英里”上的一個小巷子里,顯得是那樣的不起眼。皇家一英里是愛丁堡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同時也是愛丁堡著名的商業街。也正是因為其古老,在逛皇家一英里的時候,是要抱著一種讓自己迷路的心態的,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哪一扇門洞的后面就隱藏著難得一見的風景。愛丁堡的作家博物館便是如此,它就設在曾對文學極度熱愛的史戴爾夫人的古老宅邸內,而這一古老宅邸與皇家一英里之間連接的小巷入口的確太普通了,稍不留神就會錯過。
說是“作家博物館”,但里面其實只有三位作家的作品展示以及相關紀念物,這三位作家便是蘇格蘭歷史上最偉大的三位詩人和作家:羅伯特·彭斯,瓦爾特·司各特以及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博物館內,到處都展示著他們的手稿以及他們曾經使用過的物品。我在羅伯特·彭斯曾使用過的一張書桌前停了很長時間,我仿佛看到了年輕的彭斯坐在這張桌前奮筆創作的情景。還有斯蒂文森穿過的一雙鞋子——應該算是靴子吧,我想,這雙靴子是斯蒂文森在他的家鄉愛丁堡穿的呢,還是在他最后的歸宿地——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上穿的呢?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說的手稿,保存得十分完好,感覺離現在似乎并不久遠,而筆跡則多少有一些模糊了。比起我在英格蘭的霍沃思小鎮看到的勃朗特三姐妹的手稿筆跡,司各特的用筆無疑更加用力且顯得比較豪放。
司各特屬于愛丁堡這座城市的“土著”,其小學、中學就讀的都是當時全愛丁堡最好的學校,大學則上的是愛丁堡大學。考上大學時,司各特只有12歲。我所看到的資料表明,12歲的年齡也并非愛丁堡大學新生中最小的,大約只能算是最小的學生之一,至少另一位愛丁堡人,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大衛·休謨就是在他12歲那一年被愛丁堡大學錄取的。
司各特降生于如今的愛丁堡大學的喬治廣場一帶,那曾經是司各特的父母家所在地,當年應該尚沒有被劃入愛丁堡大學的教學區。如今的喬治廣場,分別屬于愛丁堡大學的商學院、信息學院、法學院以及大衛·休謨樓所在地。早在司各特降生之前,司各特母親所生的六個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據說,司各特才一歲半時,還是得了一場大病,類似于小兒麻痹癥吧,結果便是其右腿肌肉萎縮,終身都成了一個瘸子。說起來這多少像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宿命:偉大的英格蘭詩人拜倫也是天生跛足,而司各特與拜倫屬于同一時期的文人,他們分別被作為蘇格蘭與英格蘭文學的代表人物。司各特往往喜歡在清晨起來創作,而拜倫則是喜歡在夜晚寫詩;這一點頗具有象征性。從二人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燦爛的清晨或者黑夜對他們各自作品的深刻影響,而這種影響至今仍是英國許多大學的文學課師生所共同探討、爭論的話題。
雖然至今已無法確認哪一座房子曾經降生了瓦爾特·司各特這位偉大的作家,但是可以確認的是,目前愛丁堡新老城區的絕大多數地方,都曾經留下過司各特的足跡。
據說,司各特被當時的愛丁堡人認定是蘇格蘭唯一能夠與英格蘭的拜倫勛爵PK一番的文學人物,甚至在英國議會里都有這樣的議論。但就司各特而言,他只是滿足于自己在愛丁堡和蘇格蘭的文學地位,無意與英格蘭的拜倫去一決伯仲。這除了性格使然,還在于司各特十分崇拜拜倫,多數時候他都是以拜倫粉絲的面目出現。沒錯,有關拜倫的故事與傳說,在當時的英倫三島都是上流階層閑暇時議論的話題。拜倫的年齡、地位以及超乎常人的英俊,無疑比他的作品更加迷人。關于拜倫的魅力,司各特當年在愛丁堡對友人所講的一段話最有分量,他說:“至于講到詩人,我相信,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國家所有最優秀的詩人我都見過——可是,盡管彭斯有一雙能夠想象得出的最有神采的眼睛,我卻認為,除去拜倫以外,他們的容貌都稱不上是藝術家心目中的出色人物。神采是有的,但是夠不上光彩照人,唯有拜倫的容貌才是人們夢寐以求的那種最美的形象。”
1802年,司各特在愛丁堡出版了《蘇格蘭邊區歌謠集》并大獲成功,同時又擔任了愛丁堡高等法院的院長。雖然有錢有勢,司各特卻因為腿瘸,而未被自己所愛的姑娘的家庭認可,只得作罷。于是他娶了法國女郎夏洛蒂·夏潘特,二人直到終老。靠著寫詩和小說,1820年,司各特被英國王室封為男爵。靠寫作獲得王室爵位,司各特在英國歷史上是第一個。不知是因為崇拜拜倫的緣故,還是因為的確自嘆弗如,司各特公開表示,他終其一生也無法在詩歌創作上超過拜倫,所以決意放棄詩歌創作,而專注于小說寫作。之后,他斷斷續續創作了30部歷史題材長篇小說,是迄今為止創作歷史題材小說最多的歐洲作家,其勤奮程度與巴爾扎克有一拼。當然,司各特創作小說也是為了多拿稿酬。
司各特在投資上可謂乏善可陳。僅在愛丁堡一地,他就多次投資失敗,并欠了一屁股債。這些債務,司各特直到去世也沒有還清。
羅伯特·彭斯的年齡比司各特大十二歲。彭斯進入愛丁堡上流社會視野的那年,司各特剛剛考上愛丁堡大學。二人僅有兩次見面。我們不清楚彭斯對司各特有什么印象,但司各特無疑是興奮的,尤其是他在愛丁堡大學哲學教授佛格森的家中見到彭斯之后,總是見人就要“吹噓”一番。12歲嘛,怎么說都是個孩子。
司各特曾經愛過的那位姑娘的家,就在愛丁堡王子大街旁。如今,這條大街的一側,矗立著一座非常雄偉的紀念碑,碑身就是彭斯的雕像。
愛丁堡人對彭斯極為崇拜,甚至將每年1月25日(彭斯的生日)作為民族節日來過,并命名為“彭斯之夜”。“彭斯之夜”的主角是“蘇格蘭國菜”哈吉斯,這道由羊肚包裹著羊內臟制成的美食幾乎成了民族象征。在吃哈吉斯之前,人們通常要事先誦讀一遍彭斯的詩篇《致哈吉斯》。
18世紀末的蘇格蘭曾是歐洲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雖然地處歐洲邊緣,人口只有100多萬,但蘇格蘭高度繁榮的教育體系卻孕育了不計其數的文壇巨匠與科學巨人。這得歸功于16世紀的一場宗教改革運動。該運動由馬丁·路德以反對羅馬天主教會腐敗的名義發起,曾席卷全歐洲。其中,約翰·諾克斯作為蘇格蘭教會創始人之一,認為男女都應有受教育的權利,人人都應該讀圣經》。1583年,蘇格蘭便建立了四所公立大學,成為名副其實的教育重鎮。這讓農民彭斯得以有機會受到比較系統的基礎教育。彭斯為人津津樂道的,不僅是他的才華,還有他的英俊風流、浪漫多情。詩歌、自然、美酒、女人,就是彭斯人生的寫照。除了天生的貴族身份,在其他方面,彭斯與拜倫倒是有些相像。
彭斯最優秀的詩歌作品產生于1785—1790年間。他從農民生活和民間傳說中汲取素材,憑真情實感描寫大自然及鄉村生活。在當時蘇格蘭上層都崇尚英語的時代,他卻始終堅持用蘇格蘭方言寫作。這些作品多數收錄在詩集《主要以蘇格蘭方言而寫的詩》中。該書出版后,彭斯得稿費20英鎊。他原打算用它買船票去牙買加,從此離開英國。恰在此時,愛丁堡傳來喜訊,請彭斯到愛丁堡接洽出版詩集的事宜。彭斯喜出望外,隨即于這年的11月27日找鄰居借了一匹馬,快馬加鞭地趕往愛丁堡。翌年4月,《歡樂的卡利多尼亞詩神》在愛丁堡出版發行。彭斯名利雙收,既得到多達400英鎊的稿酬,還得了100枚金幣的版權費。
農民彭斯在愛丁堡過得風生水起,社會名流、大家閨秀競相與他相識,雖然他的穿戴完全就像個進城的鄉巴佬。當時的愛丁堡沙龍女主人戈登公爵夫人說,彭斯在與女士們交談時總是彬彬有禮,他的言談既傷感又幽默,令人為之傾心。
彭斯拿著賺到的稿費開始在蘇格蘭漫游、吟唱,但在愛丁堡,有一個女人卻在等著他,這個女人名叫艾格尼斯,其丈夫在中美洲的英國殖民地服役,與艾格尼斯關系緊張。彭斯于是與她成為了情人。這段感情持續了四五年之久,這也是彭斯與愛丁堡緊密相連的四五年。在此期間,彭斯出入于愛丁堡上流階層舉辦的各個沙龍,對所有文學活動都積極組織、參與,儼然成了愛丁堡的一位文學領袖。
1789年,彭斯回到他的家鄉加洛韋,并謀得了一個小稅務官的職位;這一點他倒是與之后的華茲華斯十分相像。彭斯每天都要騎著馬去上班。就在那一段飛揚馳騁的日子里,他有了靈感。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寫出了《友誼天長地久》;一個半世紀后,它成為電影《魂斷藍橋》的主題歌,被人們傳唱至今。
沒有證據表明,羅伯特·彭斯與隱居在湖區的華茲華斯兄妹相識。華茲華斯兄妹到湖區隱居的那一年,彭斯已經去世了。
在離彭斯雕像不算很遠的地方,有一家不大的咖啡館,名叫大象咖啡館,J.K.羅琳的《哈利·波特》最初就是在這間咖啡館里寫出來的。
我不是很愛湊熱鬧的那類人,而且對羅琳也談不上喜歡,但既然來了愛丁堡,大象咖啡館總還是要去瞧一瞧的。我的第一印象是,大象咖啡館多少有一些局促,人稍微一多就感覺到擁擠。里面的桌椅則普遍有一點點新中式的味道,不清楚老板當初是怎樣的設計想法。羅琳在這里寫作的時候,正在愛丁堡大學進修,也經常會帶著她不大的孩子一起。說實話,同樣是作為寫作者,我是不太好想象當年羅琳是怎么在這里“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只是我覺得她最大的勝利不是成為億萬富翁,而是她由此成為了愛丁堡大學的“杰出校友”。
創立于1583年的愛丁堡大學是愛丁堡這座城市的驕傲。在愛丁堡逗留期間,我有幸赴愛丁堡大學參加了一次與學校管理層的交流活動。我記得我問到了這所大學的兩位校友,一位是阿道爾夫》的作者、法國作家龔斯當,另一位就是J.K.羅琳。對于龔斯當,他們表示,一百多年前,愛丁堡大學的法國學生相當多;而對于羅琳,他們似乎不太樂意展開談論。說實話,我不太清楚羅琳對于愛丁堡大學而言意味著什么。與該校其他著名校友——如查爾斯·達爾文、亞當·斯密、大衛·休謨、亞當·弗格森、亞歷山大·貝爾、溫斯頓·丘吉爾、柯南·道爾,以及被稱為“怪杰”的奇才辜鴻銘等等——相比,J.K.羅琳成為“巨匠”或許還需要時間,而且這與她以她母親的名義捐給愛丁堡大學一千萬英鎊無關。
身為英格蘭人,愛丁堡無疑是J.K.羅琳寫作生涯中最最重要的一站:1993年年底,剛剛經歷了離婚打擊的J.K.羅琳帶著還在襁褓之中的女兒,揣著三章《哈里·波特》的手稿,走出了愛丁堡威弗利火車站的出站口。而威佛利火車站的名字就來源于瓦爾特·司各特的小說《威佛利》。
說實話,我之前對于J.K.羅琳的認識基本上都來自于各種媒體。而這些媒體所共同描繪的是:一個生活拮據的單親母親為了節省暖氣費,只能帶著孩子到大象咖啡館去“蹭”暖氣,一邊寫作一邊借此度過漫長的冬日。而事實呢?如今看來卻并非如此。愛丁堡出版的一本有關羅琳的書籍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J.K.羅琳實際上并沒有她自己所說的那么窮,就目前所知,羅琳曾經申請到了每周103.5美元的政府失業救濟金,她還申請到了一份每周70英鎊的政府低保金。她拿著政府給她的這些救濟金,除了不可以出國消費之外,在英國國內還是可以自由旅行的。錢的確不多,但倘使省著花,偶爾去一趟北海邊消遣也是沒問題的。
1997年2月,還是因為羅琳自己的申請,蘇格蘭藝術協會給了她一筆13000美元的費用,以資助她未完成的寫作事業。之后的事情想必大家也都清楚了。總之,女作家一夜之間紅遍了全世界,她的個人財富早已經超過了英國女王。
愛丁堡顯然是J.K.羅琳的福地。就像大象咖啡館與羅琳的關系在愛丁堡不是秘密一樣,如今J.K.羅琳位于愛丁堡郊區莫切斯頓的家庭地址在愛丁堡也不是什么秘密。那里屬于愛丁堡的富人區,從大象咖啡館步行半個小時便可以到達那里,有不少人專程趕過去“探秘”。聽說羅琳為她的兩個孩子在院子里花27萬英鎊蓋了一座城堡,結果被鄰居告到了愛丁堡市政廳,不等“城管”來,羅琳就自行拆除了。
走在愛丁堡的大街上,抬眼便是險峻高聳的城堡、古老冷硬的教堂,低頭便是數百年馬踏車輾的路面與草地上橫臥豎躺的人們,一切關于中世紀、關于公主與王子的想象仿佛都在這里漸漸成形。和燦爛與冷冽相間的白晝相比,我還是更喜歡有熒熒燈火烘托起夜晚的愛丁堡,它總是令我想起司各特,想起彭斯,想起以寫作《金銀島》而馳名的愛丁堡人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被刻在愛丁堡老城和新城交界處那塊地磚上的詩句:“沒有任何一顆星星,如愛丁堡的街燈般閃亮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