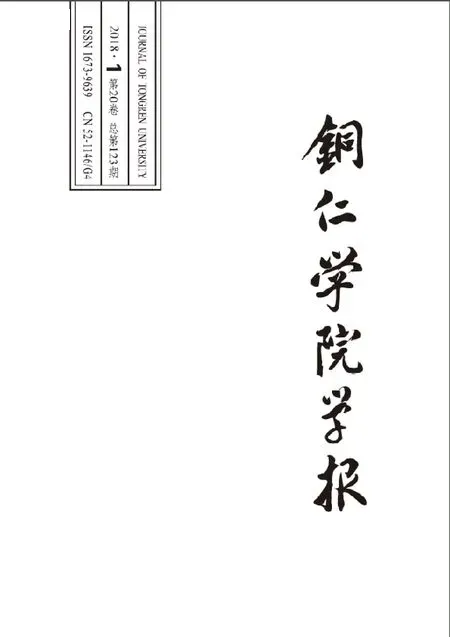淺論鄂爾泰的改土歸流策略
邊 莉
( 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
清雍正年間在西南地區開展的改土歸流,是西南民族史、西南邊疆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學術界有關研究成果很多。鄂爾泰作為改土歸流的主帥,也得到了學術界較大的關注,對他與西南改土歸流關系的研究相當全面,從他對改土歸流建議的提出,開展改土歸流的措施與實施方案,到西南改土歸流后如何促進西南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各個環節都有深入的研究。本文選取鄂爾泰改土歸流策略這一環節進行研究,主要基于這個環節的研究目前還稍顯薄弱,相關研究結論還有進一步推進之處。關于鄂爾泰改土歸流的策略,有關研究多少都有所涉及,但直接研究論文目前主要有劉本軍《論鄂爾泰改土歸流的原則和策略——兼對“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說質疑》一文,該文對鄂爾泰在云南、貴州、廣西等地改流中的原則和策略進行了分析,并對“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一說提出質疑,認為鄂爾泰在其改土歸流中并未實踐過[1]131-133。本人不揣淺陋,試就鄂爾泰改土歸流的策略進行再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鄂爾泰對西南局勢和土司問題的看法
關于清初西南地區局勢,鄂爾泰在上奏清廷的《改土歸流疏》開篇就談道:“云、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2]9444。他分析了云貴地區社會混亂的主要原因在于少數民族問題,其兩大隱憂:一是土司,一是苗患。
鄂爾泰直指土司作亂,影響范圍廣,波及西南數省,嚴重危害國家安定。前明在苗疆地區進行改土歸流時因“煙瘴新疆,未習風土”[2]9445,苗疆地區風土習慣與內地有較大差異,故在改流地區因地制宜,以夷制夷。然苗疆地區土司世襲數百載,“苗、猓無追贓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2]9446,司法不明,吏治廢弛,行賄風行。土司對治下土民進行殘酷剝削和壓迫,“彼雖依例輸糧,其實占據私享者不止十數倍,而且毒派夷人,恣肆頑梗”[3]55。土司對土民任意征派,土民生活水深火熱,苦不堪言。此外,由于土司兇悍,專事劫掠,致使地廣人稀的邊疆地區長期得不到開發。如地土肥饒、資源豐厚的烏蒙山區,川境民眾不肯赴遠力耕,滇境民眾亦不敢就近播墾,歷經多年,使得該地成為荒蕪不治之區。另東川等地雖已改流,但是土目已久盤據,“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2]9444。土司治下,社會秩序混亂,沃土荒廢、無人墾殖,極不利于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和封建國家賦稅的征收。
此外,貴州地區苗寨廣布,因其山川地形的阻隔,區內群苗“蟠據梗隔,遂成化外”[2]9445,且貴州地區土司無鉗制群苗的責任,故鄂爾泰認為威脅西南地區社會穩定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貴州的“苗患”,且“甚於土司”[2]9444。
針對西南地區貧窮、落后、野蠻的社會現狀,鄂爾泰指出要改變西南局勢,安定西南邊疆,其癥結歸根到底在于終結土司統治,務必開展改土歸流,“鏟蔓塞源”[2]9446,治其根本。鄂爾泰思想明確,在改土歸流及善后過程中從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綜合整治:政治方面,明確鏟除土司勢力的總方針,化解民族糾紛,加強中央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統治;軍事方面,提出綱領性建議,即“計擒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2]9446為改土歸流的順利開展提供指導;經濟方面,大力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加強中原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交流與融合,以安民制夷,以增賦稅,以靖地方。
鄂爾泰對西南局勢分析和對土司問題的看法客觀深入、有理有據,得到了雍正帝的贊賞和認同,隨后被任命為云南總督,開始大規模的改土歸流。
二、鄂爾泰對改土歸流的主張與策略
在改土歸流過程中,鄂爾泰針對西南各省不同的社會狀況,及不同土司、苗蠻對改流的態度和表現,因其輕重緩急,在政治、軍事方面采取不同的主張與策略,區別對待。
(一)政治主張與策略
政治方面,鄂爾泰根據西南地區的社會狀況,明確指出了急待治理的土司地區:如自明以來歸屬四川行省,但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黔西和滇東北的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與滇東南、黔西南交界的粵西泗城府;以及滇西南地區瀾滄江中下游以東的鎮沅、威遠等府。并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主張重新劃分行政區,對府治等進行調整或重設,并新設“流官”進行治理。
由于苗蠻所處多在行省交界地區,距所屬行省治所較遠,這些地區便成為封建統治的薄弱環節,一旦發生爭斗,如雍正三年(1725)冬,烏蒙攻掠東川,便出現“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2]9444的現象,以至于管理上出現四川總督因遠統治不力,而云貴督撫又因職權不屬難以管理的情況。故此鄂爾泰提出改隸行政區劃,將東川、烏蒙、鎮雄三府改隸云南,相機改流,設三府、一鎮的策略。
黔、粵兩省以牂牁江(今盤江)為界,雖有一江相隔,但邊界土司相互爭奪,操戈不休,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常常逾江互相爭斗,挑起暴亂。且該地區由于苗寨寥闊,管轄的將吏互相推諉,致使該地區長期以來民族關系緊張,民族矛盾尖銳,嚴重影響著地區間的交往。針對黔、粵邊界特殊的地理環境,鄂爾泰則以山川地形為行政區域劃分的依據,主張對黔、粵邊界進行劃分,“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2]9445,并“增州設營,形格勢禁”[2]9445進行管理。另,瀾滄江中下游地區與緬甸、老撾相鄰,地域遼闊、遠通國外,土司、蠻夷眾多,鄂爾泰對前人針對該地區提出的“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2]9445的治理策略表示贊同。
(二)軍事主張與策略
軍事方面,鄂爾泰結合其“計擒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2]9446的總綱領,在改流過程中主要采取計擒、兵剿、招降、自請改流四種軍事策略,并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的實際情況,靈活應用。
1.計擒
針對苗蠻兇詐、苗疆地域復雜的情況,鄂爾泰在改土歸流中多采用計擒的策略,運籌帷幄,力求知己知彼,一戰而勝。如鄂爾泰在平定貴州仲家苗過程中,計擒鎮遠土知府刁澣、霑益土知州安於藩,盡法懲治。雍正六年(1728)五月,鄂爾泰在平定江外蠻夷中,由于六茶山苗寨眾多,有巢穴四千余寨,“窮日力不能遍搜一箐,及搜至,賊又他遁”[4]288,于是選用當地被降服的苗蠻為向導,深入六茶山腹地以賊攻賊,無險不搜。
計擒,顧名思義,以計法擒之,減少用兵,是改流中的上上之策,不僅能有效達到統治者對西南地區改土歸流的目的,同時能最大程度上減輕改流對這一地區的社會破壞,有利于民族地區的社會恢復與發展。
2.兵剿
對于長久作亂群苗和“數往不就撫”[2]9447的土司,鄂爾泰則采取強硬的軍事圍剿措施,“不以擒賊之少與并無首級為慮,而以逃竄頑苗定應搜刮急需,籌一勞永逸之為要機也”[3]104。云南東部之東川、烏蒙和鎮雄,西部的鎮沅、威遠、恩樂、車里、茶山與孟養等地兇夷盤踞,素為民害,鄂爾泰指出想要規劃全省邊疆,務使此數處永遠寧謐方為長策,于是雍正五年至九年(1727-1731)鄂爾泰大舉用兵。如:云南鎮沅倮刁如珍等戕官焚掠,鄂爾泰遣兵討平之,獲如珍;五年(1727),威遠倮札鐵匠等、新平倮李百疊等響應如珍作亂,九月,鄂爾泰檄臨元總兵孫宏本率師討之,“冒瘴突入,禽斬千計”[4]288,獲札鐵匠,降李百疊,使瀾滄江內地區全部改流。六年(1728)春,鄂爾泰遣兵破擒法戛,又遣副將郭壽域捕米貼賊,此后,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螂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馀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2]15285。八年(1730)六月,烏蒙、東川諸苗夷聚為亂,殺塘兵,劫糧運,堵要隘,毀橋樑,嚴重影響地方安定和社會發展,對此,鄂爾泰集官兵萬數千人,土兵半之,以魏翥國、韓勛、哈元生分三路進攻,破其寨,攻其眾。經此一役,祿鼎坤、祿萬福父子兄弟均“伏誅”。除云南外,針對貴州、廣西等省的頑固土司勢力,鄂爾泰也采取了強硬的軍事行動,如:雍正二年(1724),貴州定番、廣順仲苗作亂,抗拒前總督高其悼在此設立衙署營房。鄂爾泰下決心清理苗寨,指出“如欲開江路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2]9445。五年(1727)三月,廣西泗城土府岑映宸縱其民眾外出擄掠,鄂爾泰發兵屯者相,并設立七營管之;七月,鄂爾泰發兵與湖北師會,討定湘西、黔東南交界的謬沖花苗,獲其渠首,降其余眾,“殺一警百,使群苗畏法”[3]80。除對影響力較大、態度惡劣的土司勢力采取強硬的軍事圍剿策略外,對作亂的土目,鄂爾泰也采取強硬態度,“窮搜屠殺,刳腸截脰”[2]9451,如:四年(1726)冬,鄂爾泰在四川總督岳鐘琪的配合下,拿獲土目祿萬鐘等,殺掉敢于頑抗的土官土目上百名;對作亂的米貼土目祿永孝直接“論斬”。
兵剿,則是用于土目盤踞、頑固抵制清廷改土歸流的地區,過程中雖會對當地的社會生產和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長遠來看,兵剿策略對周圍地區具有較大的威懾作用,且及時有效的扼制住了當地土司土府統治者野蠻的反動的統治,結束了西南地區山高路遠,“土皇帝”各自為政的局面,將整個地區置于中央王朝的統治下,有利于地區社會的發展和長治久安。
3.招降或勒令自請改流
基于鄂爾泰在改流中強硬的軍事圍剿措施,群苗顫栗,眾多苗蠻或被招降,或自請改流。雍正四年(1726)冬,長期橫行于烏蒙、東川的土目祿鼎坤迫于改流形勢,“愿求內附”。五年(1727)十一月,招降長寨后路苗百八十四寨。六年(1728),撫貴州拜克猛、長寨、古羊等生苗百四十五寨。七年(1729)七月,招安順、高耀等寨生苗及儂、仲諸種人內附。八年(1730)五月,招黎平、都勻等寨生苗內附。對于湖廣、四川地區土目,鄂爾泰乘威詔扶,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后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兵。除因招降而改流的土司外,不少土司自請改流,如:“樂甸土司刁聯斗乞免死,改土歸流”[2]9446。泗城土府岑映宸繳印獻土,“乞免死存祀,改土歸流”[2]9447。“五年,萬鍾詣鍾琪降,慶侯亦詣鍾琪請改土歸流”[2]9447。對于自請改流,高度配合改土歸流工作的土司土府,清政府更是給予優待,授以誥命,減其歲貢或犒以豐厚的物資,如: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隴慶侯庶母二祿氏、四川沙馬土婦沙氏因未響應作亂,給誥命,賜予銀幣。八年(1730),“永昌邊外孟連土司請歲納廠課六百,鶴慶邊外皦子請歲貢土物”[2]9451,鄂爾泰上報,上“命減孟連廠課之半。皦子入貢,犒以鹽三百斤”[2]9451。旨在安撫歸順土司,防其因不滿而再次作亂,同時借助此等懷柔政策,影響周邊苗蠻勢力,避免因過多使用武力破壞當地社會生產與發展。
招降和勒令自請改流,不僅將用兵降到最低,節約了政府資源,且在最大程度上取得當地民眾的支持,提升認同感,便于維護改流地區的社會穩定,及后期中央政府在該地區統治的深入。
三、鄂爾泰的改土歸流善后策略
在西南完成改土歸流的地區,鄂爾泰為維護西南邊疆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及中華民族的大一統,采取了一系列的善后策略,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兩個方面。
(一) 維護西南地區政局穩定
在完成改流的地區,土司的安置和處理對于維護西南地區政局的穩定意義重大,鄂爾泰僅對個別罪惡昭著而又反抗朝廷的土司量以重刑,對大多數土司仍采取“懷柔”安置的策略,主要是遷徙安置,盡徙已革土司土目于他省守置,如,鄂爾泰“請映宸送浙江原籍”[2]9447。至于所遷處所則是“各有定地、不限千里”[2]6551,湖廣土司保靖宣慰使彭御彬“安置遼陽”[2]15230,桑植宣慰使向國棟“安置河南”[2]15230,云南土司阿迷州土知州李純“安置江西”[2]15293,姚安府土同知李厚德“安置江南”[2]15296。《清史稿·刑法志》載:“惟條例于土蠻、瑤、僮、苗人仇殺劫擄及改土為流之土司有犯,將家口實行遷徙”[2]6551。對土司進行遷徙安置,一方面是自明以來,土司世代承襲,在其轄區內建立了相對獨立的政治、經濟、軍事統治,其根深葉茂,絕不是一次軍事行動就能徹底實現改流目的,惟有對土司、“土目”進行改土重遷,妥善安置,酌量撥給莊田,以資養贍,徹底斷其歸鄉之念,使已歸者無舊主之思,未歸者生欣羨之意,進一步促使邊區和內地一體化;另一方面,改流完成后必然會對該地區進行一系列的政治、軍事、經濟改革,很大程度上會觸犯改流土司原有利益,若改流土司仍留本省,對其管束太嚴,則伊等不得其所。若令疎放,又恐其復生事犯法。由此看來,將改流土司異地安置,有利于緩和改流地區社會矛盾,促進區域和諧發展。
此外,為鎮壓反抗苗民,進一步控制苗民,維護西南地區的穩定,加強中央王朝對改流地區的管轄和控制,鄂爾泰對改流地的行政區進行重新劃分,對府治等進行調節或重設,新設“流官”進行治理,并規定“流官”需由中央選任,加深了中央與西南地方的直接聯系,清明了地方吏治,改變了地方司法不明、“土目”一言定生死的局面。在完成改流的地區戍兵,設置營汛、參將營、協營,如在黔邊諸夷設“建參將營,奮扼險要”[4]288,于“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為古州外衛”[4]290。在云南思茅、橄欖壩各地設官戍兵,用以扼制蒙、緬、老撾門戶。在苗疆“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2]15311。九年(1731),疏請“重定烏蒙、鎮遠、東川、威寧營汛”[2]9451。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螂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2]15285。
魏源《圣武記·雍正西南夷改流記》言:“人即不革之,苗亦必自大變動,以大更革之”[4]296。前代有以夷制夷,然則復返。針對改流地區的各種舊制陋規、地方流弊,鄂爾泰采取徹底禁革的策略,斷其念,易其俗,令勿返。風俗上,令歸流之民“易服薙(剃)發”[4]288,“席其椎髻裹氈之舊、巫蠱械斗之常”[4]295。文化上,在“苗疆”地區廣設義學,以漸化導。雖然“義學”旨在培養苗家上層子弟,宣揚封建教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隨著封建思想文化在這一地區的廣泛傳播,民眾思想意識得以提升,有利于緩和地方社會矛盾。
(二)發展西南地區社會經濟
經濟方面,鄂爾泰在改流地區采取的是“與民休息”的策略,租稅從輕,編戶口,定額賦,“立保甲,稽田戶”[4]288,在有的地方甚至“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官胥之擾”[2]15311。并采取了一系列經濟開發措施,興修水利工程、鼓勵墾殖、疏浚河道、開通江路。
鄂爾泰鼓勵西南地區民眾大力開墾荒地,在云南地區開墾楊林海周圍草塘,耕東川城北漫海。在云貴交界之處,墾辟汙萊,焚烈山林,使得“久荒之土,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五六歧(尺),豆大如栗”[4]291。隨著大量荒地的恢復生產,西南地區的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滿足了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需求。此外,鄂爾泰令人在云、貴邊界筑橋,命名為“庚戌橋”[2]9451,便利了云貴間的交通。九年(1731),鄂爾泰疏請興修云南水利,浚嵩明州楊林海,疏通宜良、尋甸諸水,筑浪穹羽河諸堤,修臨安諸處工,開通粵河道。在苗疆地區,鄂爾泰“遍勘上下江,濬灘險,置斥堠,通餉運”[4]290,并于清水江、丹江設重營,以控制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馀,赴湖南市鹽布糧貨”[4]289。此外,由于都江和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間有五十余里陸路隔斷,若打通陸路間隔,則都江和清水江合二為一,于是“突搗梗頑,奪地避險”[4]290,使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并疏浚柳州至桂林之河,一水直達。江路的開通,促成了商船往返倡道,“民、夷大忭,估客云集”[4]289的繁榮局面。河道的疏浚, 江路的開通,長期以來因陸路不暢而導致的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交通障礙也隨之消失,極大便利了改流地區人民同中原人民的交流和往來。而剩余的農副產品也由江路運轉至中原地區,成為特色的少數民族地區產品,不僅發展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也促進了苗疆地區同中原地區經濟的交流和往來,進一步促使了改流地區同中原內地的一體化。
參考文獻:
[1] 劉本軍.論鄂爾泰改土歸流的原則和策略——兼對“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說質疑[J].思想戰線,2001(2).
[2] (清)趙爾巽.清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清)胤禛.朱批諭旨[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5.
[4] (清)魏源.圣武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