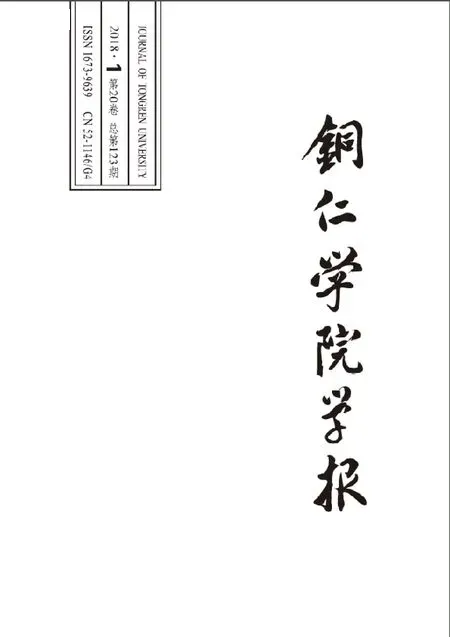關于陶淵明的“三線研究”
范子燁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
由于侯長林教授主編的《梵凈國學研究集刊》的創刊,從本期開始,“梵凈國學”欄目正式更名為“梵凈古典學”;之所以如此,我們是想更好地實現集刊與學報的分工,集刊的覆蓋面最大,傳統的經史子集研究無所不涉,而學報的古典學欄目,則以古典文學研究為主,重在以多元的角度和多元的思維闡發古典作品的特殊價值。而所謂古典學(Classics),實際是取義于西方的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和傳統,它發源于古希臘和羅馬時代,偏重于經典文學作品及其語言的研究。因此,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無疑是古典學研究的重點。
陶淵明其人其詩當然屬經典之列。其實,關于陶淵明的研究,早已成為古典文學界的顯學,這種顯學具有明顯的世界性。姑且不談有關陶詩的多種西文譯本,即以英譯陶詩而言,目前也已經形成一門專學,我們可以稱之為陶詩英譯學,相關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陶淵明具有永恒的魅力,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就中國詩人而言,當推第一,如果有人對此持有質疑,那么,只能說明質疑者對相關的情況不夠了解。就我國學術界的陶淵明研究而言,目前已經呈現出“三線布局”的態勢:一線研究,是關于直接研究陶淵明及其作品的研究,吳國富教授所撰《陶淵明早年北方仕宦考》一文是也;二線研究,是關于陶淵明的影響研究,陳際斌教授所撰《論唐傳奇集盛期文人之桃源情結》一文是也;三線研究,是研究的研究,即關于陶淵明研究史的研究,高建新教授所撰《一心塑造自我心目中的陶淵明形象——評清人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一文和李劍鋒教授所撰《論方東樹從古文義法對學習陶詩途徑的揭示》一文是也。這是本期“梵凈古典學”推出的四篇論文。
國富兄的論文,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陶淵明還到北方做過官!他的驚人的觀點,讓我一時無法招架。他的基本看法是:凡是陶詩中提到的北方地名,如張掖、幽州、東海(他理解為山東濱海地區)之類的,陶淵明都是去過的,并推斷出陶淵明青年時曾在朱序手下為參軍,在北方奔走十年,二十八歲始返回南方,旋即召為江州祭酒。但是,如此重要的事情,《宋書》《南史》和蕭統《陶淵明傳》居然都沒有記載,而《宋書》“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的表述,本來是陶淵明曾經仕于桓玄幕下的隱語,因為劉裕當了皇帝,而桓玄是被劉裕消滅的政敵,所以陶淵明的那段仕宦經歷就成了“歷史問題”,為尊者諱,史家不得不如此書寫。劉裕(363-422)于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十月,率晉軍攻克洛陽,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但是陶淵明的朋友羊松齡出使秦川,陶淵明高興地寫了一首贈別詩:“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政賴古人書。賢圣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乘運見踈。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從這首詩來看,陶淵明明顯沒有到過黃河以北地區,所以他拜托松齡代為觀賞沿途的名勝古跡,特別是與“商山四皓”有關的歷史遺跡。國富說:“假如陶淵明從洛陽出發,每天騎馬100里,半個多月也就到了張掖。”姑且不說陶淵明能否每天騎馬走100里(事實是即使人能夠做到,馬也做不到),從洛陽去張掖也必然經過商山(在今陜西省商洛市,黃河北岸),那里正是上引陶淵明《贈羊長史》詩提到的地方。我料定國富兄既不會騎馬,也沒去過商山。至于文中局部征引的《天魏故彭澤令陶公(潛)墓志》和《大魏故銀青光祿大夫、司徒并錄尚書事、都督荊湘等州諸軍事陶公(浚)墓志》,完全是當代人的漏洞百出的偽作,當代史學工作者已有考辨文章發表,在此情況再用來做文章的論據,也是非常不妥的。國富的觀點雖然可商,但是,此文從北方地域著眼,畢竟喚起了我們對陶淵明與北方文化的關系的關注,同時,文章中不無精彩之處。如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時來茍冥會”一句,國富解釋說:
詩中的“冥會”,指自然吻合、暗自巧合,但頗有“碰上好運氣”、而且是不平常的運氣的意思,指的是人生大機遇。如郭璞《磁石》:“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藝文類聚》卷六)后秦僧肇《肇論·責異》:“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梁書·陶弘景傳》說:“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這些“冥會”,都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意思,用來形容人生際遇,自然就不是一般的機會了。
這是非常明晰、精確的解說。國富教授對陶淵明的貢獻是很大的,先后四部陶淵明研究專著出版,他對江西地域文化的熟悉,使他對陶淵明往往有獨到的理解。譬如,他從潯陽文化的角度論證《后搜神記》確為陶淵明所作,言之鑿鑿,論證嚴密,是其對學術界的重要貢獻之一。我對此至今記憶猶新。
陳際斌教授論文主要討論《桃花源記》對唐傳奇的影響,他認為處在繁盛時期的唐傳奇關于神仙勝境的描繪“折射著文人的桃源情結”,“對壺中天地的追尋即是為了尋求另一理想天地,對桃源勝境之向往即是對無奈現實之否定。桃源仙境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二次尋找時總是無路而返,亦可看作是文人希望的破滅。”這實際上涉及古人對《桃花源記》的另一個解讀方向,那就是視桃源中人為仙人。有人質疑說:“記曰設酒,殺雞,作食。仙者,豈能殺乎?”這也是很有趣的現象。文學的接受和解讀,有時是非理論性在起作用,由此對陶淵明這樣的經典作家,闡釋的空間便越來越大了。
高建新教授的論文全面評述了清人邱嘉穗的《東山草堂陶詩箋》,重點揭示其研究陶詩辭章、義理、版本、考據兼顧的特點。他一方面肯定:“邱嘉穗由衷熱愛欽佩陶淵明,悉心揣摩陶詩,在評注中多有創獲,主要體現在對陶淵明高尚人格的贊美推重、對陶詩藝術深入的體味和獨具匠心的闡發。”并指出:“邱嘉穗一心想塑造自己心目中的陶淵明形象。在邱嘉穗看來,陶淵明甘愿回到鄉村,躬耕自食,飲酒賦詩,是身處鼎革之時不得已而為之,自然不是縱酒佯狂、‘放達風流’的晉人可比的。”同時,對邱嘉穗關于陶詩的極為過度的政治學闡釋又持堅決的批判態度。建新是平視甚至俯視邱氏的。建新是我國當代學林中最熟悉陶詩文本和陶集版本的學者之一,故發言遣詞皆有依據,而文辭簡古,語言典雅,顯示了深厚的文章功力。多年來,建新為陶淵明在北方草原上的傳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事實上,陶淵明早已經進入了他個人的信仰世界,至于陶公的酒早已進入其生活世界,則學界同仁所共知的。
如果說邱嘉穗的《東山草堂陶詩箋》偏重于對陶詩的考據的話,那么,方東樹的《昭昧詹言》則側重于對陶淵明及陶詩的理論闡發。李劍鋒教授的這篇論文全面研究了方東樹關于陶淵明的理論闡釋。他重點揭示了方東樹的主要貢獻在于“以古文義法論陶詩,凸顯了陶詩的跌宕變化之妙,指示了學習陶詩的有效途徑”,同時,他指出:“方東樹認為陶淵明的‘識抱’不如杜甫‘篤實正大’,‘陶公所以不得與于傳道之統者,墮莊、老也’”。即認為陶淵明由于受老莊的影響,其作品的風格氣象比杜甫遜色一籌。從劍峰征引的方氏論陶文字來看,大致上包含著“無心為詩論”和“寄托深婉論”兩個方面,前者如:
如阮公、陶公,曷嘗有意于為詩;內性既充,率其胸臆而發為德音耳。
惟陶公則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學人而自成,無意為詩而已至。
后者如:
陶公胸中別有大業,匪淺儒所知。
古人變革之際,其立言皆可覘其志性……陶公淡而忘之,猶有《荊軻》等作。
兩相比較,前者更占上風。其實,這兩種看法是存在矛盾的。完整的解決方案,方氏并沒有給出。其理論思維水準,比劉勰、劉知幾和章學誠遜色遠矣。劍鋒能夠彰顯其理論的內在矛盾,足見眼光之敏銳。近十年來,劍鋒于陶淵明之研究用力頗勤,就其未來能夠取得的成就而言,他出版的三部研究陶淵明的著作,都屬于奠基性的起點。以陶淵明研究為核心,學術的輝煌無疑會屬于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