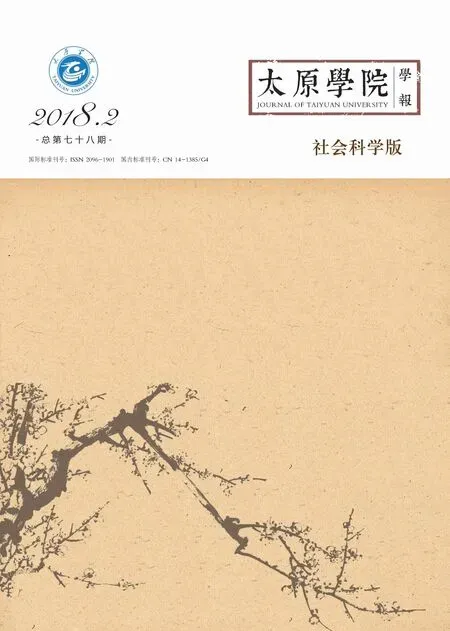質(zhì)疑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的三個通說
(蘇州大學(xué) 王健法學(xué)院,江蘇 蘇州 215006)
自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我國革新經(jīng)濟體制以來,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日新月異,金融交易運作漸趨頻繁。出于對信用授受的擔(dān)憂、風(fēng)險規(guī)避的考慮,實踐中萌生出大量以設(shè)定擔(dān)保為基礎(chǔ)的交易,除典型擔(dān)保外,尤以讓與擔(dān)保為甚。然而,法律具有滯后性,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的以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為基礎(chǔ)的信用交易,儼然成為物權(quán)法定主義統(tǒng)攝下的“法外空間”,與現(xiàn)行的定限擔(dān)保物權(quán)體系“格格不入”。與此同時,司法實踐對于“無法可依”的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之認(rèn)定亦莫衷一是,“同案不同判”現(xiàn)象催促著物權(quán)法學(xué)界對此的回應(yīng)。毋庸諱言,此背景下建立健全科學(xué)合理的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已成當(dāng)務(wù)之急。
作為非典型擔(dān)保的代表,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是指債務(wù)人或第三人為擔(dān)保債之履行,與債權(quán)人約定將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先移轉(zhuǎn)于債權(quán)人,如嗣后債務(wù)人不能履行到期債務(wù)則債權(quán)人可就該動產(chǎn)優(yōu)先受償之擔(dān)保方式。從歷史沿革角度看,讓與擔(dān)保制度可追溯至古羅馬時期,其雛形為信托質(zhì),端緒由此萌生。信托之適用并不限于擔(dān)保,其亦廣泛應(yīng)用于諸如親權(quán)等涉及人身的民事活動。信托質(zhì)系信托于債的關(guān)系中的擔(dān)保化應(yīng)用,其運作表現(xiàn)為以擔(dān)保為目的的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具體而言:債權(quán)人先于形式上取得標(biāo)的物所有權(quán),若債務(wù)人逾期未履行債務(wù),則債權(quán)人可處置該動產(chǎn)或主張以物抵債,但應(yīng)返還超出債權(quán)額部分之價款;反之,若債務(wù)人如約履行,則債權(quán)人被課予返還標(biāo)的物所有權(quán)之義務(wù)。值得注意的是,信托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債權(quán)人以占有改定之形式對標(biāo)的物施以管領(lǐng)控制,債務(wù)人仍直接占有該動產(chǎn)并對其使用、受益[1]。由于此制度能很好地平衡雙方利益,故信托質(zhì)一度風(fēng)靡,成為早期擔(dān)保的主要形式之一。近代以來,大陸法系國家普遍繼受讓與擔(dān)保制度,然其并非明定于成文法,而系于判例中表彰。德國法院于1906年以判決的形式肯認(rèn)了讓與擔(dān)保之債的合法性,后又于《租稅調(diào)整法》中對此予以細化明確[2]。受前述德國判例影響,日本法院于明治45年對讓與擔(dān)保的態(tài)度出現(xiàn)更迭,由原先的“因其系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轉(zhuǎn)變?yōu)椤盎趦?nèi)外效力有別而對內(nèi)有效”,據(jù)此承認(rèn)了讓與擔(dān)保制度。隨后,我國臺灣地區(qū)引進了德日學(xué)說,對于讓與擔(dān)保制度的抵觸逐漸松動,僅以禁止流押作為對其的限制。至此,不論是理論抑或?qū)嵺`,讓與擔(dān)保制度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制中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反窺我國立法,物權(quán)法定主義下讓與擔(dān)保制度的生存空間極為逼仄。因其于制定法中無跡可尋,故迄今為止讓與擔(dān)保并未取得擔(dān)保物權(quán)之名分,司法實踐中法院對其的立場亦顯騎墻。然而,學(xué)理上的論爭無法阻遏信貸實踐的飛速發(fā)展,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日益凸顯。時至今日,學(xué)界對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已作較為充分的研究,但筆者認(rèn)為,其中的三個通說觀點值得商榷。
一、質(zhì)疑“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不可成文化”之通說
通說觀點認(rèn)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不可成文化”。首先,讓與擔(dān)保本質(zhì)系通謀的虛偽表示。縱觀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設(shè)立始末,債務(wù)人并無轉(zhuǎn)移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于債權(quán)人的意思;易言之,所有權(quán)移轉(zhuǎn)僅為形式外觀,而以此為對價擔(dān)保債的履行卻是實質(zhì)內(nèi)涵,故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系雙方基于通謀而為之虛偽表示。其次,讓與擔(dān)保明顯有違現(xiàn)行法中“禁止流押”之規(guī)定。禁止流押的設(shè)立初衷系遏制債權(quán)人乘人之危之行徑,保護立約時處于窘迫境地的債務(wù)人,避免其因“城下之盟”蒙受巨額損失。而不論從形式抑或?qū)嵸|(zhì)上看,讓與擔(dān)保與流押契約幾無二致。再次,讓與擔(dān)保與現(xiàn)行擔(dān)保體系相沖突。物權(quán)法定主義下,擔(dān)保物權(quán)的定位系定限物權(quán),即其僅享有部分所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其由所有權(quán)派生并起限制效果。而讓與擔(dān)保具備“完全所有權(quán)”屬性,故如若將其成文化,無疑將構(gòu)成對現(xiàn)行擔(dān)保體系完整性的破壞,邏輯上亦難以自洽[3]。最后,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成文化既無比較法上的先例,亦無迫切的實務(wù)需求。一方面,比較法上承認(rèn)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國家大多未設(shè)置動產(chǎn)抵押制度,某種程度上,前者是后者缺位時用以彌補漏洞之法的續(xù)造;另一方面,實踐中可通過對動產(chǎn)抵押進行解釋以處理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糾紛,故無立法之必要[4]。
筆者認(rèn)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不可成文化”這一通說觀點值得懷疑,理由如下:
(一)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讓與”并非虛偽表示
民事主體憑借表意參與民事活動,內(nèi)心意思與外化表示相結(jié)合即形成意思表示,此為法律行為成立之核心。意思表示系表意人表達內(nèi)心意愿之產(chǎn)物,屬法律概念。表示行為與內(nèi)心真意不一致時即引發(fā)真意保留與虛偽表示兩種樣態(tài)。虛偽表示適用于雙方通謀之情形。所謂通謀,其成立須同時滿足以下三要件:其一,雙方的意思表示均欠缺效果意思;其二,表意人效果意思缺位之情況為對方所知曉;其三,雙方串通,故意作出非真意之合意[5]。
需澄清,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中“讓與”并非虛偽表示,而是基于真意所欲發(fā)生之權(quán)利移轉(zhuǎn)行為。如前所述,虛偽表示之“偽”以效果意思欠缺為前提。就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而言,雙方移轉(zhuǎn)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之際即確切地達成以此作為擔(dān)保之合意,該合意系真正的效果意思,并無構(gòu)成虛偽表示之嫌隙[6]。退一步講,即便“讓與”構(gòu)成虛偽表示,由于“以供擔(dān)保”為隱藏其中之意思,根據(jù)《民法總則》第146條之規(guī)定,虛偽表示無效并不牽連于包裹其中之隱藏行為之效力,故當(dāng)事人可主張適用隱藏行為之規(guī)定,排除虛假意思適用之余地。比較法上德國判例即借助羅馬法的信托理論對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之“讓與”作出有效性解釋,從而顛覆了先前因“讓與”被誤讀為虛偽表示而無效的觀點。
(二)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并不違反“禁止流押”之規(guī)定
前述已及,立法之所以對流押條款持否定態(tài)度,緣其保護經(jīng)濟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債務(wù)人,以阻遏債權(quán)人利用債務(wù)人窮困之窘境逼迫其簽訂流押條款進而巧取豪奪。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讓與擔(dān)保“披擔(dān)保之衣行流押之實”,本質(zhì)仍是變相的流押。筆者對此不敢茍同,一方面,就法律性質(zhì)而言,流押系債之履行的實現(xiàn)方式,而非擔(dān)保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流押與讓與擔(dān)保分屬不同范疇,并無交集。與流押即直接以物抵債不同,讓與擔(dān)保之設(shè)立著眼于標(biāo)的物的交換價值,擔(dān)保之債到期不能清償時,債權(quán)人負(fù)有強制清算義務(wù),僅就擔(dān)保物清算所得價款優(yōu)先受償,故從實質(zhì)上看,讓與擔(dān)保能很好地平衡雙方利益,避免流押可能引發(fā)的恃強凌弱之不平。另一方面,就當(dāng)事人享有之權(quán)利義務(wù)而言,由于流押發(fā)生于抵押擔(dān)保中,故物權(quán)法定主義下雙方享有之權(quán)利義務(wù)已為實定法所明確。相形之下,讓與擔(dān)保中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多源于習(xí)慣或法理,譬如擔(dān)保物變價后,債務(wù)人有權(quán)請求債權(quán)人返還超額價金。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司法實務(wù)不斷深入,“禁止流押”規(guī)定的弊端也逐步昭顯。首先,“債務(wù)人處于弱勢”這一預(yù)設(shè)即存在疑問。當(dāng)下大多數(shù)借貸關(guān)系并非以債權(quán)人為主導(dǎo),而系互利共贏之合作:債務(wù)人舉債融資,通過抬高財務(wù)杠桿激進式經(jīng)營,增加每股收益,以博得報表使用者青睞;債權(quán)人收取本息,通過將閑置資金投出獲取收益,從而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利潤。由是觀之,“債務(wù)人處于弱勢”之預(yù)設(shè)在當(dāng)下顯得以偏概全、不合時宜。其次,“禁止流押”規(guī)定有悖于民法意思自治原則。禁止流押是手段而非目的,其設(shè)立旨在遏強扶弱,匡扶公平。借貸雙方實力均衡背景下,“禁止流押”規(guī)定之適用應(yīng)逐步限縮,讓位于意思自治。最后,實踐中抵押權(quán)的實現(xiàn)多為經(jīng)雙方協(xié)商后將抵押物折價,故從法律效果看,其與“以物抵債”的流押并無二致,故規(guī)定“禁止流押”之必要性亦不如前。
(三)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并不與現(xiàn)行擔(dān)保體系相沖突
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多采潘德克吞體系,遵循體系的內(nèi)在邏輯一致性系維護法典形式理性的應(yīng)有之義。現(xiàn)行擔(dān)保制度下?lián)N餀?quán)均為定限物權(quán),而讓與擔(dān)保所讓與之權(quán)利并非“完全所有權(quán)”,其行使以擔(dān)保目的為限,實質(zhì)上仍屬定限物權(quán),故對其作創(chuàng)設(shè)并不悖于擔(dān)保體系的內(nèi)在邏輯。有學(xué)者指出,承認(rèn)讓與擔(dān)保即突破物權(quán)法定主義,有違所有權(quán)內(nèi)容法定和擔(dān)保物權(quán)種類法定。筆者認(rèn)為此觀點值得商榷。作為所有權(quán)擔(dān)保的他種形式,所有權(quán)保留與融資租賃均以成文化,列示于合同法分則中,此二種擔(dān)保均對所有權(quán)內(nèi)容作限縮,皆有僭越物權(quán)法定主義之嫌,故將同為所有權(quán)擔(dān)保的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成文化亦無可厚非。至于“承認(rèn)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存在違背擔(dān)保物權(quán)種類法定之嫌的觀點,筆者認(rèn)為,此恰恰印證了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成文化的必要性,宜將其法典化示于典型擔(dān)保之列。毋庸諱言,前述沖突之化解端賴于立法始竟其功[7]。
(四)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于比較法上有跡可循且有迫切的實務(wù)需求
研究一項制度是否應(yīng)予立法,其肯綮在于其是否與我國國情相匹配。域外立法例僅具參考價值,以他國未創(chuàng)設(shè)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得出我國亦不應(yīng)對此成文化之推論,顯然難以令人信服,遑論比較法上確有將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成文化之先例。譬如日本通過《假登記擔(dān)保法》之頒布,以立法形式承認(rèn)了賣渡擔(dān)保的合法性;韓國亦頒布專門法調(diào)整讓與擔(dān)保當(dāng)事人間法律關(guān)系。放眼更廣闊的視域,不論是《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抑或《聯(lián)合國動產(chǎn)擔(dān)保交易立法指南》,其中均存在針對讓與擔(dān)保立法所作之論述。
此外,就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與動產(chǎn)抵押之取舍而言,有觀點認(rèn)為,二者功能相當(dāng),取其一即可。筆者對此不敢茍同。一方面,前者具有后者所不具備之突出優(yōu)勢,集中體現(xiàn)于實現(xiàn)方式的靈活便捷。現(xiàn)行物權(quán)法下,動產(chǎn)抵押權(quán)之實現(xiàn)主要通過民事訴訟法的特別程序完成,且須以當(dāng)事人間無異議為前提。實踐中抵押人動輒以實體權(quán)利義務(wù)尚存爭議為由延宕抵押權(quán)實現(xiàn)之進程,此無疑將增加抵押權(quán)的實行成本,于債權(quán)人不利。相較之下,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的實行無需司法公權(quán)力介入,不論采處分清算抑或歸屬清算,債權(quán)人均可依約定及時獲得債之清償,而不必勞神費力,周旋于曠日彌久的司法程序。另一方面,“逕以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取代動產(chǎn)抵押”之觀點亦不可取。動產(chǎn)抵押權(quán)變動無需公示,此有違我國物權(quán)變動長期以來所恪守的債權(quán)形式主義,實屬異類。而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雖能解決上述問題,但仍具有體系異質(zhì)性,以此代彼的方案并不適妥[8]。筆者認(rèn)為,應(yīng)同時規(guī)定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與動產(chǎn)抵押,二者并無非此即彼之對立關(guān)系,兩項制度可以同時存在。隨著金融交易數(shù)量逐年攀升,金融擔(dān)保前景廣闊,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實務(wù)需求愈發(fā)迫切。不斷催生的金融交易手段如融資融券、信托收據(jù)的廣泛應(yīng)用足以證成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應(yīng)用前景之廣闊,立法理應(yīng)對此作出回應(yīng)。綜上所述,由于動產(chǎn)抵押與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實行機制有別,適用領(lǐng)域各有側(cè)重,故我國即將編纂的物權(quán)法編中宜將兩項制度同時規(guī)定,使二者各司其職,服務(wù)于相應(yīng)的經(jīng)濟活動。
二、質(zhì)疑“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采所有權(quán)構(gòu)造”之通說
通說觀點認(rèn)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采所有權(quán)構(gòu)造”。首先,讓與擔(dān)保權(quán)無價值權(quán)性。讓與擔(dān)保雖形為擔(dān)保物權(quán),然其以權(quán)利轉(zhuǎn)移為先決條件,并無變價可言。所有權(quán)權(quán)能不可隨意拆分,債權(quán)人受領(lǐng)“讓與”即取得完全所有權(quán),對外效力上物權(quán)變動已成,對內(nèi)效力上債權(quán)人僅受內(nèi)部信托關(guān)系約束。其次,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以占有改定為其公示手段。作為交付形式之一,占有改定能夠充分發(fā)揮讓與擔(dān)保“保守商業(yè)秘密”之功用。當(dāng)下,隨著社會分工精細化程度不斷提高,占有與本權(quán)相分離之現(xiàn)象顯得稀松平常。明確占有改定的公示效力系大勢所趨[9]。最后,采所有權(quán)構(gòu)造有利于保障債權(quán)人利益。債權(quán)人取得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后,可在不超過擔(dān)保目的范圍內(nèi)對擔(dān)保物施以處分,從而大大提升債權(quán)實現(xiàn)之可能。
筆者認(rèn)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采所有權(quán)構(gòu)造”這一通說觀點值得懷疑,理由如下:
(一)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具有價值權(quán)性
擔(dān)保物權(quán)的設(shè)置以服務(wù)于保障債務(wù)清償為目標(biāo),以支配擔(dān)保物交換價值為手段,價值權(quán)性是其根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亦是如此。根據(jù)定義,債權(quán)人受讓擔(dān)保物所有權(quán)時,雖于表面上形成“權(quán)利外觀”,但基于雙方真實意思可知,此“讓與”僅供保障債務(wù)清償,債權(quán)人不得對該動產(chǎn)作出超過擔(dān)保意旨范疇之處分。就實質(zhì)而言,債權(quán)人所受讓之所有權(quán)并不圓滿,得受擔(dān)保目的之限,如若嗣后擔(dān)保權(quán)實現(xiàn)程序啟動,債權(quán)人將僅從該標(biāo)的物清算價值中優(yōu)先受償。由此可見,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中債權(quán)人仍是對標(biāo)的物交換價值作支配,其價值權(quán)性不言而喻。至于“所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無拆分之依據(jù)”的提法,筆者對此不敢茍同。權(quán)能系權(quán)利所分解之能力,特定場合所有權(quán)項下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分離,恰恰是“權(quán)盡其用”的表彰。某種程度上,擔(dān)保物權(quán)即是所有權(quán)交換價值凝結(jié)成的獨立權(quán)利,讓與擔(dān)保權(quán)亦是如此[10]。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所有權(quán)構(gòu)造”動搖了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系擔(dān)保權(quán)屬性之根,而惟有對其采“擔(dān)保權(quán)構(gòu)造”方能體現(xiàn)其實質(zhì)。
此外,亦有學(xué)者指出,“擔(dān)保權(quán)構(gòu)造說”將讓與之所有權(quán)定性為非完全屬性,系對“所有權(quán)讓與”要件之忽視,這種企圖通過模糊所有權(quán)與定限物權(quán)之邊界進行解釋的做法,實乃牽強附會之舉,不足為訓(xùn)。筆者認(rèn)為此觀點欠缺說服力。一方面,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中“債權(quán)人于形式上取得標(biāo)的物所有權(quán)”、“擔(dān)保權(quán)實現(xiàn)時允許歸屬清算”等足以證成該制度并未忽視“所有權(quán)讓與”;另一方面,定限物權(quán)本就是由所有權(quán)派生,將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理解為僅具備交換價值之所有權(quán)亦應(yīng)無可非議。
(二)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不應(yīng)以占有改定為其公示手段
權(quán)利的靜之擁有和動之行使須以外化形式得以呈現(xiàn),物權(quán)概莫能外。物權(quán)的直接支配性、普遍對世性要求其變動須以特定機制顯現(xiàn),由此,公示制度應(yīng)運而生。
“所有權(quán)構(gòu)造”理論下,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公示手段系占有改定,此為德國判例所采納并沿用多年。然該做法飽受學(xué)界詬病,理由是:占有改定雖為交付形式之一,但因其過于隱蔽,對善意第三人保護不周,故其公示價值微乎其微,所有權(quán)變動之形式要件亦名存實亡。筆者對此深表贊成,我國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之公示如若采占有改定,則物權(quán)變動構(gòu)造無疑會向意思主義傾斜,其結(jié)果是將從實質(zhì)上撼動債權(quán)形式主義之根基,此應(yīng)避免。
既然公示手段不應(yīng)采占有改定,那么還有哪些其他的可供選擇之公示方法呢?一種觀點認(rèn)為,可借鑒日本,以明認(rèn)作為公示手段。明認(rèn)源于習(xí)慣法,日本判例在林木、溫泉等自然資源物權(quán)變動場合對其予以承認(rèn),效力等同于登記。簡單易行是明認(rèn)之優(yōu)點,然其內(nèi)容過于粗略,難堪記載復(fù)雜物權(quán)變動之重任,故不宜采納。第二種觀點認(rèn)為,應(yīng)效法動產(chǎn)抵押制度,以登記作為公示對抗要件。有學(xué)者對此提出反對意見:一方面,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受追捧的原因之一系其隱蔽性特征,不論是所有權(quán)讓與時的內(nèi)部約定抑或擔(dān)保權(quán)實現(xiàn)時的清算方式選擇,當(dāng)事人均可自行協(xié)商,外人無從知曉,此無疑增加對舉債經(jīng)營的債務(wù)人商業(yè)秘密保護之力度。而如若采登記,則上述優(yōu)勢將蕩然無存,針對債務(wù)人的商業(yè)秘密之保護亦被摧毀。另一方面,動產(chǎn)種類層出不窮,紛繁蕪雜。加之其價值量通常較小,移動頻繁,故以登記對其公示將招致不堪重負(fù)的工作量,巨額成本的耗費亦是必然,從制度設(shè)計的成本收益權(quán)衡角度分析,此做法無疑得不償失[11]。筆者認(rèn)為上述觀點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一方面,評判某項制度的優(yōu)劣,關(guān)鍵著眼于其運行是否能平衡好各方利益,減少偏頗之虞。“陌生人社會”模式運作下,貿(mào)易往來以信用為其基石,以緩和人際隔閡帶來的信任危機。作為信用評判的關(guān)鍵依據(jù)之一,交易參與者的財務(wù)狀況應(yīng)以合理方式予以外現(xiàn),其真實性務(wù)必依仗健全披露機制之運作。誠然,商業(yè)秘密系企業(yè)之隱私,債務(wù)人設(shè)法對其施以保護無可厚非,然而制度設(shè)計應(yīng)作通盤考慮,以實現(xiàn)各方利益之衡平為宗旨。除債務(wù)人外,債權(quán)人、第三人利益以及維護交易秩序之穩(wěn)定理應(yīng)予以觀照,不可顧此誤彼、失之偏頗。如是思忖,借助登記公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之變動恰是考慮周延的中肯之舉。公示對抗模式下,借貸雙方讓與擔(dān)保權(quán)之設(shè)立依約定而成就,經(jīng)登記可對抗善意第三方。此制度的優(yōu)點有二:其一,有利于衡平債務(wù)人與債權(quán)人之利益。債務(wù)人可出于隱蔽商業(yè)秘密之慮選擇不予登記,此情形下?lián)?quán)自合同生效時設(shè)立,雙方即受擔(dān)保關(guān)系約束。若讓與擔(dān)保人無權(quán)處分,使擔(dān)保物所承載之交換價值減損,債權(quán)人可對其主張違約責(zé)任。其二,有利于保護不知情第三人利益,從而實現(xiàn)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并重。在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未登記場合,債務(wù)人在繼續(xù)占有擔(dān)保物之際,可能為無權(quán)處分之行徑。通常,占有系權(quán)利人享有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的表征,不知情的交易相對人基于債務(wù)人占有動產(chǎn)之事實,合理信賴其乃真正權(quán)利人,而后基于此信賴與讓與擔(dān)保人訂立買賣合同并支付相應(yīng)對價。登記對抗下,善意第三人原始取得動產(chǎn)所有權(quán)。準(zhǔn)此,交易安全得以保障,個益與公益亦達致衡平。
另一方面,登記并非一概采書面形式,文件登記已不再是唯一選擇。于比較法視角觀瞻,美國法上除傳統(tǒng)書面登記外,亦施行聲明登記制。與前者有別,后者不以文件為載體,且內(nèi)容上無需記載合同詳情。筆者認(rèn)為,聲明登記制可資借鑒,理由有三:其一,隱去債務(wù)人部分隱蔽性信息,緩和因采登記導(dǎo)致的對債務(wù)人商業(yè)秘密保護之不周。聲明登記下,對外公示的內(nèi)容僅為最基本信息,有關(guān)所擔(dān)保合同的詳細情況均會被過濾,債務(wù)人資力狀況亦僅是簡單陳述,其細枝末節(jié)處無登載之需。此方式能于使外界周知的同時盡可能地保障債務(wù)人秘密信息,實為衡平之舉。其二,減少成本,消解動產(chǎn)登記耗資繁重之不足。動產(chǎn)易移動,地點的更迭將會導(dǎo)致登記內(nèi)容的頻繁變更,此誠大幅增加交易成本,存在本利懸殊之虞。文件登記下,該不對等之境況還將被進一步放大,當(dāng)事人基于對本利的權(quán)衡選擇對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不予登記,其結(jié)果是該登記制度名存實亡。相形之下,若采新型登記,由于聲明內(nèi)容不涉及擔(dān)保細節(jié),僅顯示最基本信息如主體身份、標(biāo)的物價值等,故“登記內(nèi)容因動產(chǎn)移動而頻繁變更”之疑慮可予消弭。此外,隨著資本市場的變遷,金融擔(dān)保異軍突起,作為擔(dān)保物的動產(chǎn),其價值亦不可同日而語,“動產(chǎn)價值量小”這一成見應(yīng)當(dāng)摒棄。其三,與時俱進,聲明登記的電子化更契合時局。隨著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迅猛發(fā)展,其應(yīng)用已廣泛普及,進入尋常百姓家。紙質(zhì)化的文件登記有賴于人工對信息的逐字填寫和比對,文件歸檔與整理即嗣后保管需要大量人力、財力的投入,此自不待言;對比之下,電子化登記不以紙為載體,無紙化操作在簡化流程的同時,節(jié)約了資源,也為第三人查詢擔(dān)保信息提供了更為便捷的途徑。鑒于交易成本的減少,擔(dān)保權(quán)人更愿意辦理登記以保障其清償時的順位,債務(wù)人亦可于不過度披露其自身秘密的同時從擔(dān)保權(quán)人處取得融資,電子登記下雙方利益皆被考量,均衡局勢始現(xiàn)。另外,比較法上法國、韓國、澳門地區(qū)等均對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采登記對抗模式,運作優(yōu)良。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登記機制的建立無需另起爐灶,擴大現(xiàn)行動產(chǎn)抵押登記系統(tǒng)的適用范圍,使之涵蓋包括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在內(nèi)的動產(chǎn)擔(dān)保登記,不失為上策之舉。
(三)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制度設(shè)計應(yīng)兼顧好各方利益
前述已及,實現(xiàn)各方利益的均衡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運行之歸宿。“所有權(quán)構(gòu)造”理論下,擔(dān)保權(quán)人基于信托法律關(guān)系所享有的擔(dān)保目的范圍內(nèi)的所有權(quán),其在對外效力上和完全所有權(quán)無異,對于擔(dān)保目的所對應(yīng)的交換價值部分,其可自行處分,此無疑對擔(dān)保權(quán)人有利。然而,“所有權(quán)構(gòu)造”保護債權(quán)人過度,而對他方保護不足。該理論下,擔(dān)保人于動產(chǎn)上設(shè)定擔(dān)保后將“惶惶不可終日”,唯恐債權(quán)人無權(quán)處分。債權(quán)人僅受合同內(nèi)容拘束,效力不及于外部第三方。故若債權(quán)人果真無權(quán)處分,符合善意取得要件時第三人將無負(fù)擔(dān)地取得標(biāo)的物所有權(quán),而擔(dān)保人只得主張違約責(zé)任以獲救濟,其地位之薄弱可見一斑。相反,“擔(dān)保權(quán)構(gòu)造”理論下,所有權(quán)于實質(zhì)層面并未從設(shè)定人處移轉(zhuǎn),此大大削減債權(quán)人無權(quán)處分該動產(chǎn)之可能。債權(quán)人可于條件成就時通過清算程序優(yōu)先受償,利益得以保障;設(shè)定人仍支配著擔(dān)保物,無需惴惴而栗,寢食難安。由此可見,較之于“所有權(quán)構(gòu)造”,“擔(dān)保權(quán)構(gòu)造”更能照顧好各方利益,契合衡平法理。
三、質(zhì)疑“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實現(xiàn)采處分清算”之通說
通說觀點認(rèn)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實現(xiàn)采處分清算”。一方面,采處分清算可回避被認(rèn)定為流押條款之嫌。擔(dān)保權(quán)的實行以債之不履行為其啟動前提。就實行方式而言,存在公私之分。“公的實行”借助公權(quán)力,通過民事訴訟法的相關(guān)程序予以實現(xiàn),司法干預(yù)性是其特征;“私的實行”依當(dāng)事人約定展開,不必歷經(jīng)繁瑣的強制執(zhí)行程序,靈活便捷是其優(yōu)勢。就擔(dān)保權(quán)實行而言,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顯屬后者。前述已及,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最鮮明的優(yōu)勢系清算環(huán)節(jié)的簡單便捷,無訟累之煩擾。就“私的實行”而言,其清算方式存在處分清算與歸屬清算兩種備選方案。處分清算指擔(dān)保權(quán)人從將標(biāo)的物變賣所得價款中優(yōu)先受償,而歸屬清算指擔(dān)保權(quán)人確定地取得標(biāo)的物所有權(quán),并將超額價金返還于擔(dān)保人。從表征看,歸屬清算與流押實現(xiàn)幾無差異。另一方面,基于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的價值權(quán)性,采處分清算更契合擔(dān)保權(quán)普遍特征,也有利于厘清當(dāng)事人間的實體權(quán)利義務(wù)[12]。
筆者認(rèn)為,“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實現(xiàn)采處分清算”這一通說觀點值得懷疑,理由如下:
(一)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處于優(yōu)位
作為民法基本原則之一,意思自治鮮明地體現(xiàn)著民法本質(zhì)以及私法自治理念。在無禁止性規(guī)定且不違背公序良俗場合,當(dāng)事人間的意思自治應(yīng)優(yōu)先被尊重,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權(quán)的清算方式選擇亦應(yīng)遵循此理。通說觀點將處分清算視為唯一方式,排除當(dāng)事人約定的做法誠不可取。貫徹意思自治原則下正確的做法應(yīng)首先考慮當(dāng)事人針對清算方式的選擇是否有約定,惟有無約定情形下,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方有適用之余地。
(二)采歸屬清算無流押條款之嫌
如前所述,規(guī)定流押條款之禁止在抑強扶弱方面有其功用,但應(yīng)有所緩和。歸屬清算下,擔(dān)保權(quán)實現(xiàn)時雖有所有權(quán)確定性的移轉(zhuǎn),此與流押相似,但債權(quán)人應(yīng)返還超額部分價金,其結(jié)果是擔(dān)保權(quán)人僅就債權(quán)額部分變價受償,并無偏頗受償之可能。故“歸屬清算與流押實現(xiàn)幾無差異”的觀點過于片面,不應(yīng)采之。
(三)采歸屬清算更能凸顯制度優(yōu)勢
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制度優(yōu)越性顯于其高效便捷。該優(yōu)勢借助歸屬清算可彰顯得淋漓盡致,此處分清算所不能比。有觀點認(rèn)為,處分清算系變價清算,而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采“擔(dān)保權(quán)構(gòu)造”,變價受償乃其清算之核心,因而處分清算與其更為匹配。筆者對此不敢茍同。處分清算固然圍繞變價展開,緊扣擔(dān)保權(quán)構(gòu)造邏輯,然其并非唯一之選。歸屬清算下,債權(quán)人對超額價款負(fù)返還義務(wù),從其受領(lǐng)的絕對金額看,并未超出其應(yīng)得額,準(zhǔn)此,債權(quán)人受償結(jié)果與變價清算下無異,并不存在“處分清算與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更為匹配”一說。在承認(rèn)了歸屬清算與變價清算在與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匹配程度無高下之分后,對于清算方式的取舍理應(yīng)回歸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機制本身之營運。事實上,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法律關(guān)系中,擔(dān)保人于設(shè)定時已有以物抵債的心理預(yù)期,擔(dān)保權(quán)人亦有到期取得擔(dān)保物完全所有權(quán)之期待。由是,某種程度上采歸屬清算更吻合當(dāng)事人設(shè)立該擔(dān)保權(quán)之初衷,同時也能最為迅捷地達致債權(quán)實現(xiàn)之目的。比較法上,法國即規(guī)定了當(dāng)事人間無約定時歸屬清算優(yōu)先適用,制度優(yōu)勢由此凸顯[13]。
四、結(jié)論
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之“讓與”系真實意思,該制度不抵牾流押禁止之規(guī)定,能很好地融入現(xiàn)行擔(dān)保體系之中,且存在大量實務(wù)需求,因而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制度成文化誠有必要。鑒于價值權(quán)性之特征,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采“擔(dān)保權(quán)構(gòu)造”,并以聲明登記為公示手段,如是,方能兼顧好各方利益。就清算方式而言,應(yīng)首先尊重當(dāng)事人意愿,以約定為先;無約定時,應(yīng)采歸屬清算方式以突顯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制度優(yōu)勢。
參考文獻:
[1]周枏.羅馬法原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4:391.
[2]王闖.讓與擔(dān)保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5.
[3]胡緒雨.讓與擔(dān)保制度的存在與發(fā)展——兼譯我國物權(quán)法是否應(yīng)當(dāng)確認(rèn)讓與擔(dān)保制度[J].法學(xué)雜志,2006(04):126-128.
[4]王衛(wèi)國,王坤.讓與擔(dān)保在我國物權(quán)法中的地位[J].現(xiàn)代法學(xué),2004(05):03-08.
[5]施啟揚.民法總則[M].臺北:三民書局,2001:246.
[6]謝在全.民法物權(quán)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1:1105.
[7]王澤鑒.民法學(xué)說與判例研究(重排合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1497.
[8]高圣平.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的立法論[J].中外法學(xué),2017(05):1193-1213.
[9]向逢春.動產(chǎn)讓與擔(dān)保公示問題研究[J].求索,2013(05):165-168.
[10]高圣平.金融擔(dān)保創(chuàng)新的法律規(guī)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42.
[11]向逢春.讓與擔(dān)保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72.
[12]謝在全.民法物權(quán)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1:921.
[13]葉朋.法國信托法近年來的修改及對我國的啟示[J].安徽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4(01): 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