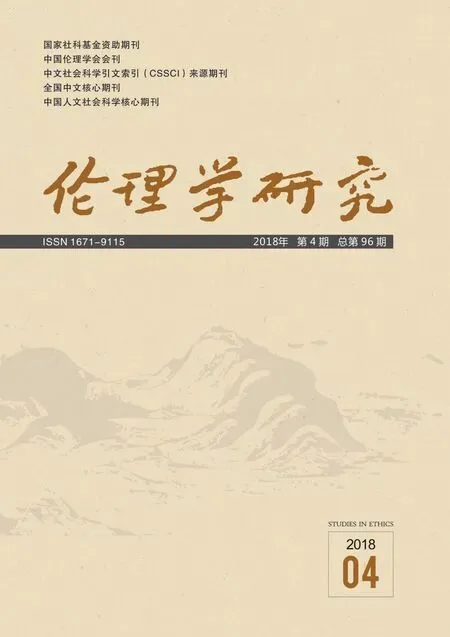中國天下觀與西方國際觀的倫理視差
靳鳳林
自五四運動以來,有不少學者認為,要改變當代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須徹底放棄我國古代王道政治的落后觀念,全面學習近現代西方國際政治的先進思想。然而,伴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快速發展和迅猛崛起,其民族自信心可謂“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對此情此景,今天又有不少學者主張,必需重新檢審中國傳統王道政治的歷史地位和價值意義,并從中尋覓理論資源,以便有效求解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倫理困境,是也非也?抑或何去何從?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筆者在本文中采用國際寬視域的比較研究方法,對中國傳統王道政治的天下觀與西方近代生成的霸道政治的國際觀進行了比照對勘,并對其倫理視差進行了深入揭橥。以便激發我們去思考,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由跟跑、并跑走向領跑時,能否用本民族傳統的國際政治倫理智慧,在重塑當今世界秩序和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承擔起應有的歷史責任。
一、重農抑商的封閉求穩與商貿經濟的開放求變
要對中國天下觀和西方國際觀的倫理視差予以深入剖析,首先要從雙方在不同自然地理環境下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入手,進而對各自心理觀念的差異性予以仔細詮釋。中國地處亞歐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這片廣闊的溫帶大陸上,四周被高山、沙漠、草原、大海隔離開來,在這一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分布著雄渾的黃土高原、眾多的大江大河、廣闊的平原地帶和復雜的山脈溝壑。特別是黃河流域疏松細膩的黃土,為古代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的出現奠定了天然根基,這就使得中華民族中原地區的農業文明在世界范圍內長期處于領先地位。而歷史上西北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不斷侵擾,一方面使得大量南遷的中原民眾,將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方式推展至長江以南地形復雜的廣大地區,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游牧民族被同化到農耕文明中來。悠久的農業文明在造就華夏民族勤勞節儉、篤實寬厚、謙和好禮、重義輕利等優良品質的同時,也使得其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呈現出保守內斂型特質。諸如:長期的農耕生活使得人們對土地產生高度的依賴感,養成了“金窩銀窩不如家中的土窩”“落葉歸根”“狐死首丘”等安土重遷、不愿流動、依戀家鄉的心理,在潛意識中對流動遷徙的經商活動以及漂泊在外的陌生人,抱有一種天然性鄙薄和憐憫態度。由于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使得人們自我陶醉于“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家田園生活之中,缺乏積極向外拓展的心理動力。在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中,人們長期聚族而居,形成了以宗族血緣為核心的家庭孝道倫理,它注重追求人的身心之間和人際之間的安寧和諧,漠視對個體權利的爭取。傳統農業生產高度重視五行相生相克、四季周而復始的自然觀,并嚴格遵守春耕、夏長、秋收、冬藏的生產生活規律,這種經驗的不斷積累,極易產生墨守成規、保守懷古的封閉心態,難以打破常規和開拓創新。
與中華民族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構成西方文明底色的兩希文化,深受波瀾壯闊的大海的影響。地中海東岸耶路撒冷附近,一方面,這里到處是綿延起伏的山脈和一望無際的沙漠,極不適宜大規模的農業耕種,在這一“新月形”地帶上造就了古希伯萊人的游牧生活,另一方面,它又是地處亞非歐三大洲的咽喉要道,古埃及、古巴比倫、古羅馬帝國都在這里爭雄逐鹿,各種貿易商隊川流不息,使之成為貿易集散之地。而身居地中海的希臘文明,生成于狹長的半島之上,同散布在其周圍的諸多孤島一樣,土地貧瘠,難以形成完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體系,不斷地殖民遷徙和海上貿易活動,成為其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由此,奠定了歐洲民族獨特的社會心理特質。例如:希伯萊民族多次喪失主權并流離失所,維系其民族生而不滅的奧秘,既不是血緣性宗族紐帶,也不是地域性鄉土情懷,而是對創世之神耶和華的堅定信仰與期待,經歷中世紀漫長的傳播與型塑過程,轉化為近現代歐美各民族對上帝的皈依與信靠。而居住在地中海各島嶼上城邦或城鎮中的希臘羅馬人,由于主要依靠商業貿易維持生存,形成了追求金錢與利潤、注重律法與契約、張揚個性與平等的精神特質,經過近代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洗禮,演變為基督新教的經濟理性觀、神圣天職觀、新型禁欲觀等,并成為當今資本主義制度的精神支柱。黑格爾曾經指出:“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們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為的有限的圈子。”[1](P134)應該說,盡管黑格爾對中國建基于大河之上的黃色土地文明存在偏見,但他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不同自然地理環境對東西方民族心理差異的深刻影響。
二、天人一體的共生共在與神人二分的主客對立
在特定自然地理環境中形成的中國文化,在思維方式上通常以“統觀”或“會通”的方式觀察宇宙、社會和人生,著眼于天、地、人、神的相互依存和密切聯系,認為不僅人體小宇宙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天地大宇宙也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宋代力倡王道政治的朱熹,把“天理”視作人間秩序的終極道德依據,人類只有體認到天理的重要性,才能形成對宇宙秩序的認識,對人類和萬事萬物的敏感。張載發揮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的義理,在《正蒙·大心篇》中主張:“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人只要獲得了這種認知,就能夠達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境界。王陽明在其《大學問》中更進一步指出:“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不難看出,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將宇宙自然、人類社會統攝為“天下一家”“天涯若比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情懷,由之,形成了崇奉“以和為貴”的國家政治哲學以及民族國家間“和而不同”的道德寬容精神。
與中國古代在天人一體基礎上形成的民族國家間共生共在的和平倫理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在古希伯來的信仰精神和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亦即兩希文化)基礎上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張神人二分和主客對立,并以此為出發點,強調民族國家間的利益沖突以及由此而生的隸屬關系。如《圣經·舊約》中的上帝是一個發布命令和提出要求的神,它主動地創造世界,并賦予每個人以靈魂。“我們要按照我們的形象,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舊約·創世紀》1:26)。古希臘的柏拉圖則將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靈魂與肉體區分開來,這一觀念通過中世紀“實在論”與“唯名論”之爭,逐步運演到近代哲學中,特別是伴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命題的提出,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日漸彰顯。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中更是以主客對立為基礎,提出了著名的“主奴關系”理論,認為自我意識的獨立性依賴于他者的承認,每一自我意識都有被承認的欲望,欲望之間的沖突和斗爭直接導致主奴關系的產生,結果是主人贏得了奴隸的承認,而奴隸在恐懼戰栗和按主人要求勞動的過程中,又會產生被主人依賴進而獲得承認的獨立意識,這就是主奴關系的辯證法,但這種承認是在不對等的關系中形成的,要真正實現平等主體之間的相互承認就必須超越主奴關系。上述哲學主張最終演化為近現代西方以國家主權和資本擴張理論為依托的販賣黑奴、種族歧視、廣泛殖民等活動,尤其是為了爭奪主人地位而掠奪他國資源和財產的殖民行為,最為集中地體現了西方哲學的主奴關系理論。其典型標示當屬大英帝國創制的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隸屬關系,而當代美國借助各種軟硬實力贏者通吃和支配世界的霸權行徑,則更為深刻地彰顯出主奴關系理論的本質內涵。二戰之后,世界各地廣泛興起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其所表明的恰恰是重建本民族主體性、實現平等主體的相互承認和重塑非西方世界歷史的過程。
三、隆禮重儀的差序格局與法律至上的城邦共治
“差序格局”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因其強大的概括力和解釋力被學界廣泛采用。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不像西洋社會是由獨立個體構成的界限分明的團體,而是由各種圈子構成的復雜網絡或同心圓,他說:“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發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2](P23)面對這種“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中國歷代統治階級高度重視以“禮儀”為核心的治國方略,或通過改造、轉化古代的禮儀,或設計、創造新型的禮儀,以適應和維護各種新的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最終形成了由禮制、禮儀、禮器、禮樂、禮教、禮學等內容構成的完備性禮儀體系。后人依據不同的研究需要對中國古代禮儀進行過形式多樣的類型劃分,如《尚書·堯典》中有“天事、地事、人事”三禮說;《禮記·祭統》中有“吉、兇、賓、軍、嘉”五禮說;《禮記·王制》中有“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說。盡管禮儀在形式上呈現出儀態萬千的特征,但歷朝歷代制定各種禮儀的目的十分明確,即明身份、定親疏、別內外、序尊卑,并以此整頓君臣秩序、規范國人行為、統治天下諸國。當然,筆者并不否認中國古代也存在復雜的法律體系,但主要以刑律為主,并被儒家的德治思想所統帥,通常被視為道德之器械,且受到前述各種禮制禮儀的嚴格約束,它無法與現代西方國家的法治體系同日而語。
如果說以差序格局為核心的禮儀體系是一個奇跡,那么,以城邦共治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則是另一個奇跡。在古希臘眾多島嶼上形成的城邦,其典型特征是以一個城市或城堡為中心,包括附近數公里以內的若干個村落組成,與其他城邦之間往往有山河海洋為自然邊界。這種小規模的政治實體就是一個國家,它對外獨立,對內形成由城邦公民、自由人和奴隸構成的政治共同體,其治理方式呈現出三大特征:(1)全民參政。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公民們的主要生存方式是從事政治活動,人人皆政治家地生活著,因此,亞里士多德才說:“城邦顯然是自然的產物,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3](P4)公民們不僅議政,而且直接參政,城邦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由公民大會集體討論決定。(2)法律至上。城邦公民對法律予以高度重視,認為只有絕對服從已有法律的人才能對其同胞取得勝利,法律一旦被濫用或廢除,共同體的毀滅也就不遠了。蘇格拉底之死充分彰顯出雅典公民對法律至上性的全力維護,當蘇格拉底被以“謾神和蠱惑青年罪”判處死刑后,他本可以通過繳納贖金或逃跑的方式免于一死,但他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寧肯依法飲鳩而死,也不違法茍且偷生。(3)制度治國。即高度重視制度設計的作用,無論是在柏拉圖的各種對話中,還是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對城邦政體的討論都占據重要篇幅。如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對各種城邦體制進行了深入區分:由一人統治的君主制和僭主制;由少數人統治的貴族制和寡頭制;由多數人統治的共和制和平民制。其中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皆是以共同利益為目標的好的政體,而僭主制、寡頭制、平民制皆是以私人利益為目標的壞的政體。雖然希臘城邦最終被龐大的羅馬帝國所取代,但尚法重制的政治基因遺傳至今天,依然決定著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四、德性濡化的仁政倫理與公平正義的契約意識
中國王道政治在處理帝國中心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上,強調以仁政倫理和自身文化道德上的優越感來濡化周邊地區,在不同朝代的擴張過程中,不以掠奪土地和殺戮人口為目的,看中的是自身文明的擴散與傳播。如《禮記·中庸》就特別強調“懷柔四夷”原則的極端重要性,“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這里的“遠人”就是指周邊諸國,在儒家看來,真正的仁君不僅是人類社會的保護者,也是文化價值的監護者,要承擔起為天下謀太平的責任,包括恢復斷代的諸侯世家、復興亡廢的諸候國家、幫助治理混亂危難的周邊世界等等。質言之,要從優秀文化的傳播、生活方式的重塑、深層價值觀的改造入手,用華夏文明中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理念來化育天下,成為中國建構世界秩序的理想模式。與之相反,試圖通過弒君篡位或密謀政變來推翻其他國家政權,使其歸順自己的做法,為歷代中央王朝所不齒。與此同時,周邊國家也通常會“誠心向化”,并尊中國為“上國”,盡量從中華文明中汲取養分,且以“華化”程度最高為榮耀。質言之,中央帝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是大樹樹干和纏繞樹干的藤蔓之間的關系,二者之間寄生共存但并不完全同質,彼此之間各取所需、互利共榮,中央帝國從朝貢國那里獲得“天下共主”的榮譽,朝貢國從中央帝國獲得政權合法性標簽和各種援助與保護。
與中國王道政治力圖通過“仁義禮智信”的德政方式來處理國際關系不同,西方國家更加看重使用“公平正義的契約原則”來處理國際間的利益沖突。在西方語境中,公平正義主要指社會價值(權力、財富、身份、地位、名譽等)的分配原則,以及這些社會價值實際分配狀態的主觀判斷。《圣經·舊約》中的上帝和以色列民族多次立約,立約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公平正義,他不僅把公平正義當作對人間掌權者的優先要求,也將其視作以色列民族的根本品質;亞里士多德更是把“公平正義”當作為政的準繩,它是處理城邦內外關系的基本原則。上述思想貫穿西方政治文化幾千年,直到上世紀末,羅爾斯在其一鳴驚人的《正義論》中,再次把這一原則運用到當代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其正義原則在《萬民法》中的運用,再次彰顯出西方國家以“契約”“條約”思想為核心的國際正義理念。在筆者看來,西方政治中公平正義的契約原則是在其工商經濟背景下,市場交往主體之間意志自律的產物,正是借助這一原則來規范自己的交往行為,以實現工商經營活動的公平和理性,正是源于契約當事人對公平利益的期待、對合理條款的認可、對合同義務的履行、對有效合同的信守,才使契約精神得以升華,超越經濟領域,上升為法律制度和社會政治秩序建構的普遍準則,并反過來成為推動近現代資本主義全面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有效工具,如:今天國際經濟貿易組織(WTO)制定的各種規則,就是維護世界各國多邊貿易秩序的重要制度保障。
五、貴中尚和的處世理念與崇力尚爭的價值取向
民族國家間在各種交往中產生利益沖突在所難免,然而,究竟以何種方式正確處理沖突,中西政治文化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深受王道政治天下觀影響的中國文化,特別強調“貴中尚和”的極端重要性,《中庸》就認為,“中和”是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大道,并將“中和”解釋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這里,“中”被看作人類生存的終極依據——“天下之大本”,“和”被視為人類追求的理想境界——“天下之達道”。當然,儒家所持守的中和,不是機械教條地堅持不偏不倚的原則,而是根據天時、地利、人和的具體要求,因地、因時、因人而異采取恰到好處的方法去靈活運用中和原則。可以說經過數千年的傳承和積淀,“中和”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如:中華民族在處理不同國家間的文化沖突時,主張以廣闊博大的胸襟、海納百川的氣魄,去促進民族國家間文化的多元交流,因為中國文化歷來都是儒道互補、儒法結合、儒佛相融、佛道互滲、儒佛道相通,即使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外來宗教文化也都采取容忍和吸收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二字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更是指善用“中和”思想做人行事和處理國際關系的中華之國,可以說“貴中尚和”思想已經深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已成為中國之為中國的重要標示物和文化形態集成。如:中國的鄭和下西洋,其目的是為了“弘揚天威”,吸引更多的國家到大明帝國來朝貢,通過交流、合作與融合,達至不同國家之間彼此共生共在、和諧相處的天下一體狀態。
與中華民族“貴中尚和”的處世理念不同,建基于兩希(希伯來和希臘)文明基礎上的西方文化,具有明顯性“崇力尚爭”的精神特質。《舊約》中的上帝充滿了對異教徒的征伐與毀滅,希臘神話中的諸神更是你爭我奪,折射出地中海東部各城邦之間戰事紛擾的現實,從希伯來和希臘文化中衍生出的基督教,不僅自身內部出現過無數次教派沖突,而且同伊斯蘭教的征戰綿延不絕,二百余年的十字軍東征便是明證,標志近代民族國家誕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新教諸侯和天主教諸侯之間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在這種文化根基上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及其國際關系理論更是充滿了競爭、斗爭、戰爭的“三爭”氣息,如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將政治的本質理解為君主及其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效地治理臣民和社會;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則用“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說明國家是求解這種矛盾的契約性產物;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中,更是強調民族國家間的戰爭,既是人類本性使然,也是國家和國際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美國現實主義政治大師愛德華·卡爾在《20年危機》中認為,任何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都要謹慎對待“國際共同體”“整體國際利益先于個別國家利益”的空幻性道德主張;與其志同道合的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提出了“權力政治”的概念,認為建立在國家實力基礎上的權力制衡才是國際政治的真實面相,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人類兩次世界大戰何以誕生在歐洲大陸。當然,我們并不否認西方也存在著康德、威爾遜等人所主張的永久和平論和國際道德論,但在此只是強調,相較于中國古代的王道政治,西方近代的霸道政治在解決民族國家間利益沖突的過程中,更加看重如何實現彼此之間的相互宰制或利益平衡。
綜合上述五個方面的深入剖析,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王道政治的天下觀與西方霸道政治的國際觀,由于生成初期自然地理環境的天壤之別,致使其在本體論上呈現出共生共在與主客對立的差別;在國家治理層面凸現出隆禮重儀與法律至上的異質性;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上彰顯出德性濡化與契約正義的區別;在處理利益沖突的方式上顯現為貴中尚和與崇力尚爭的特質。正是上述諸方面的顯著不同,構成了中國天下觀與西方國際觀的重大倫理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