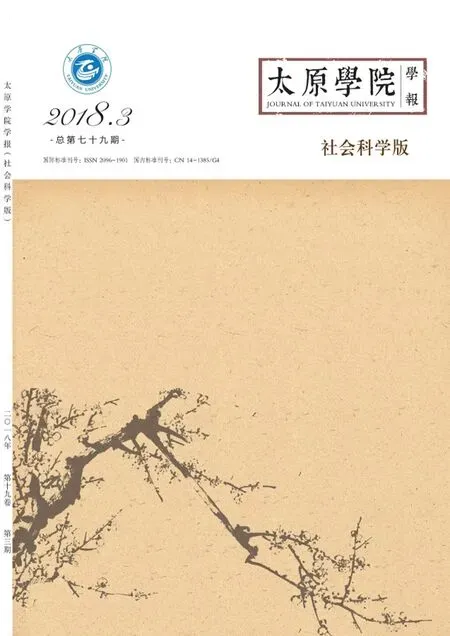張愛玲小說對民初社會言情小說的繼承與突破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廣州 510420)
“通俗, 是小說的藝術生命, 具有必然性, 這是中國小說最根本的一種傳統”。[1]這里的“通俗”, 是指通曉世俗人生, 對所描繪的社會現實及人生的了解和把握。從小說發展的歷史來看,言情是通俗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古典小說中就有言情的傳統。“言情小說”顧名思義,即以描寫男女愛情為主要題材的小說,情調浪漫,情節曲折。從唐傳奇開始,就出現了與愛情相關的描寫。元稹的《會真記》首創了“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戀愛模式。《李娃傳》則首開了“士子與青樓名妓”的戀愛模式。在宋話本和擬話本小說中,出現了更為平民化的言情故事,如《碾玉觀音》《賣油郎獨占花魁》等。明清之際更是出現了專門的言情作品,以《玉嬌梨》《好逑傳》《平山冷燕》等為代表,它們都是描寫官宦之家的小姐與青年才俊之間純潔高雅的言情故事。《紅樓夢》則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才子佳人言情小說,成為難以超越的藝術高峰,于是言情傳統便 “另辟情場于北里”[2], 產生了《青樓夢》《花月痕》《海上花列傳》等大批狹邪小說,其中也有不少杰作對現代言情小說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本文所涉及的社會言情小說的概念指民初開始到抗戰之前,稱為“民國舊派小說”的通俗言情小說。民初社會言情的大量流行,一方面是因為晚清出現了像《恨海》這樣的“以社會變革為經,以兒女之情為緯”的“寫情小說”。另一方面,是清末民初出現了大量的“禮拜六派”的言情小說。范伯群先生提出了社會言情小說這一概念 ,他認為:“言情者是在社會之中談情說愛,所以大多言情小說都涉及若干社會的側面。而在通俗文學領域中,寫社會小說者,也難免不包涵若干言情片段。論家將他們硬分成‘社會’與‘言情’等不同品種,只不過指出他們的側重點而己。凡此類小說,統稱之為‘社會言情小說’”[3]。民初的言情小說以鴛鴦蝴蝶——禮拜六派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專門描寫男女愛情的言情小說曾風行一時。
范伯群先生認為:“將民初寫言情小說稱為鴛鴦蝴蝶派是順理成章的,但這一名稱無法負載社會、黑幕、偵探武俠等眾多題材,而‘禮拜六派’倒似乎是可以包羅萬象的,取其消遣、娛樂功能,‘一攬子’塞進了這個大筐子。但是,在現代文學史中卻不用‘禮拜六派’,而是通用‘鴛鴦蝴蝶派’,約定俗成地用‘鴛鴦蝴蝶派’來涵蓋一切?這不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一種習慣性的約定俗成,有時就不再講究科學性了,似乎就狹義而言,是指言情類的通俗文學作品;而就廣義而言,也可用來指謂一切娛樂消遣類的作品。”[4]范先生認為采用“鴛鴦蝴蝶——禮拜六派”最為妥帖。這說明這個流派是以言情起家,逐步去繼承中國傳統的眾多題材,同時也借鑒外國的新樣式,形成了新的分支。同時,又參照約定俗成的歷史因素,又注意其涵蓋面,使流派的名稱與內涵相一致,并經得起推敲。
一、民初言情小說的發展特點
民初通俗言情小說的概念是梁啟超提出,并冠名為“寫情小說”的。 1903 年,《新小說》第七號就開辟了“寫情小說”欄目,在廣告中寫到:“人類有公性情二: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情之為物,固天地間一要素矣。本報竊附《國風》之義氣,不廢《關雎》之亂,但意必蘊籍,言必雅馴。”[5]寫情小說的情節雖然描寫的是男女之情,但其主旨并不是愛情,而是借“兒女”主題表達家國之感。1906 年,吳趼人的《恨海》掀起了清末民初言情小說的潮流,體現了晚清言情小說藉兒女之事言家國之情的主題,又點明兒女“小情”終將服從于社會“大情”。這給了言情以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審美上的崇高性。但與晚清相比,民初言情注重感情的發展,不以婚姻為結果的才子佳人故事,結局又多為悲劇,這產生了哀情小說。
徐枕亞認為:“凡屬言情之作,總不能脫離佳人才子之范圍。”[6]可見民初言情小說家基本上都有“才子佳人”的觀念, 民初的言情小說往往描寫青年男女一見鐘情,纏綿相戀,結局或喜或悲,都可歸結為“才子佳人”模式。作為故事模式,才子佳人的男女雙方必須德、才、貌兼備,缺一不可。“佳人”暗含了品性美好的含義,如果佳人僅有貌而無法在文學審美與價值觀上與男主人公產生共鳴,便不成其為佳人。在人物塑造上又存在理想化的特點,通常男女主人公都很年輕且沒有戀愛經驗。基于中國的婚俗文化,其戀愛必須以婚姻為最終結果。從審美上看,青年男女形貌上的美又增加了戀愛性質的純潔性。古典言情小說中,才子佳人的戀愛最終指向婚姻,其故事模式往往是一見鐘情后就私定終身,但又必須經歷磨難,最后迎來大團圓結局。但在古典言情小說中,談情說愛和戀愛心理并非小說的重點。言情可以成為小說的情節,但單靠言情本身難以支撐起一個完整豐富的故事,直到民初的社會言情小說中,才子佳人的模式才進一步發展。
從閱讀背景上看,張愛玲是熟讀小報,也熟讀《海上花》《歇浦潮》等作品,她更說《金瓶梅》《紅樓夢》這兩部作品是她一切寫作的來源。她的小說繼承了細節描寫的華美和小說主題的虛無這一特點。她對日常生活的刻畫,對兩性的悲歡離合、心理描寫都深受其影響。她第一本小說集直接稱為《傳奇》,是以現代都市人的“奇情”—— “畸情”吸引讀者。她的“奇”不是一般意義上由情節的巧合構成的“奇”,而是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和都市人的各種遭遇構成的,“奇”的不一定是故事情節,而是人在怎樣“奇異”的心理狀態下做了選擇從而推動故事發展。可見,張愛玲的小說不僅超過了通俗言情小說,與新文藝作品相比,在描寫人性,刻畫人物上也有所超越。
二、張愛玲小說對舊派言情小說的突破
(一)反通俗小說的道德評判
通俗小說除了吸引人的故事情節,勸誡目的是明顯的,作品的道德觀就等于作家的道德觀,描寫人性的墮落是通俗小說的主題之一。從1920年代開始,寫金錢、家庭解體、人格墮落的故事成為重要的主題,從結局來看,大多數的墮落結果是走向沉淪。舊派言情作家多為男性,他們不太可能去批判男性控制家庭、社會,所以只能去譴責那些欲望太多的女性。
張愛玲的故事主要通過冷靜的呈現,讓我們看到人性的罪惡。《色戒》中的王佳芝作為間諜的任務是去接近易先生,使同伴有機會完成暗殺的任務。作為舞臺演員,她習慣被關注,在與易先生在一起時,她體會到了來自權貴的寵愛和物質享受,在易先生看來,為女人購買珠寶不過是他換取風流韻事的手段,但王佳芝卻誤認為“這個男人是真愛我”,虛榮使其失去了判斷能力,缺乏革命經驗又使其輕易地放走了易先生,導致全軍覆滅。在此控制人物行為的,恰是無法理喻的情欲與非理性的虛榮心。
《半生緣》主人公的悲劇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于外界的破壞,如世鈞的母親因為曼楨長得像丈夫年輕時在上海捧的舞女而不喜歡他,曼楨的姐姐讓丈夫強暴了妹妹,并囚禁她生子,這樣的情節不管在通俗小說或新文學作品中都值得大書特書,但張愛玲卻沒有把它作為最重要的沖突,僅展現為一個場面,當世鈞找到了曼璐,曼璐沉默地把那個紅寶石粉戒指交回給他時,他就自己編織了一個“曼楨嫁給了張豫瑾”的故事,可見最終分開他們的固然有來自外界的破壞,但世鈞作為世家子弟的優柔寡斷與容易被蒙蔽,使他輕易放棄了對曼楨的尋找。但當我們讀到此處,對他產生的不是道德批判,而是感受到他的選擇是完全符合角色特點和身份的。
在言情小說中,道德因素非常重要。民初小說多以悲劇收尾,這往往來自于小說人物的道德選擇,為了道德的圓滿而選擇了愛情的缺憾,這種悲劇性結局的力量是來自外部的禮教因素,屬于偶然性的悲劇。而張愛玲小說的悲劇性卻往往來自于人物個體的非道德性選擇,正因為這一看似有可能實際上卻毫無選擇可能的境況,讓現代人警覺當自己也處于同樣情形之下,其選擇也未必比小說人物要強,從而突出了現代人悲劇的普遍性。
傳統小說中寫女性的墮落,多數來自外部力量的誘惑或威逼。但張愛玲的小說寫女性的墮落卻來自于自身清醒的選擇。《第一爐香》中葛薇龍從一開始就知道姑母是把她當“清倌人”來吸引男性,卻抵御不了浮華的物質生活和情欲的撩撥,自愿選擇了墮落,她不是沒有預見未來的可怕命運,但卻無法從這樣的生活中掙脫出來,她愈清醒其墮落就愈可怕。如果說《金鎖記》中曹七巧嫁給金錢與門第來自于兄嫂的安排,那在后來改寫的《怨女》中,可以看到銀娣是可以選擇命運的,但她卻毅然選擇了物質生活的富足。《半生緣》中,曼璐為了留住丈夫,想到用妹妹來籠絡他。她的理智知道這是一個瘋狂的念頭,但她無意識的妒忌卻使她最終設下圈套,毀了妹妹的人生。
正因為個人清醒的自我選擇,她無法違抗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的內心無意識狀態下的決定,這才突出了悲劇的普遍性意義——人性的選擇往往是趨利避害的,卻也常常是違背道德的,在此,讀到了作者對人物的憐憫與同情,使小說凸顯出現代主義精神。
通俗小說的道德批判,易停留于表面呈現,而通過人的內心世界的無意識的展現而非道德評判,才能從更豐富的角度去挖掘人性、展現立體的角色,這也是張愛玲小說具有現代性意義之處。
(二)小說的寫作模式上的超越
通俗言情小說以完整的故事為基礎,講究結構上的完整與敘事的清晰。從故事背景、人物由來都要介紹得清清楚楚。言情小說從古到今,其內涵不斷豐富,定義也在不斷地改變,從單純的言情發展到將言情、愛情包裹在一個更大的敘事中。古代的言情小說不關注婚姻的日常生活,重點在于男女愛情的整個發展過程,這一模式決定了小說的人物類型、故事走向以及結局。到了現代,言情小說從人物到內容上都有所拓寬。另一方面,寫民初兩性婚姻的不自由,除了禮教和家長的原因外,還有經濟原因,男主角大多經濟條件一般。這就逐漸出現了描寫金錢、情欲上對愛情的破壞的作品,純潔的愛情則成為神圣的存在。
民初通俗小說中影響愛情的力量來自外部社會,愛情本身是神圣美好的,為了成全愛情,男女主角甚至會以殉情或一方死亡(離開)的方式來使愛情得到升華。這就出現了“哀情”小說的流行。小說的主角無法用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愛情,又不愿意屈服于物欲和情欲,尋找愛情的代替品,所以產生了一份哀情,這保持了愛情的純潔性。
與通俗言情展現一個完整的世界不同,張愛玲的小說重點在于從生活中選擇一個短片或人生的橫截面,重點展現現代人的精神狀態,人們往往被無意識的力量所支配,無法獲得生活與精神的自由。《封鎖》以城市封鎖中的電車為背景,在這樣一個被外力支配下的真空中,人得以脫離平時的角色,一場意想不到的調情就發生了,然而張愛玲卻沒有讓它變成通俗言情,而是讓這一還沒開始就結束了的愛情故事終止于封鎖的解除。她冷靜地指出,只有在城市文明的真空之外,人才能獲得一點放縱,在猶如機器般精確運轉的都市生活中,是不會有純粹的愛情存在的,假使有真情流露的瞬間,也會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行為而被無情地扼殺。
在這樣的都市中,如果有愛情的存在,那也是雙方利弊權衡之下的最優選擇。但即使在這樣的男女之間,也不乏溫情,《傾城之戀》中范柳原的真情坦露在日軍轟炸后的頹垣斷壁下。《留情》中敦鳳一邊埋怨米先生年紀大了,一邊又貼心地照顧他,恰好表現出“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信念,這就是生活的真實狀態。張愛玲告訴我們,在都市人那里,愛是奢侈的,勢均力敵的智力與少量的互相理解便能使他們在一起。
(三)人物形象的塑造
通俗小說常常宣稱主角才貌雙全,讓人感到正因為主角各方面都超越常人,從而成就了其不平凡的經歷。民初通俗小說又慣于塑造完美的兩性形象,從而形成一系列“至情男性”的形象。張愛玲則開拓了女性形象描寫,深度描寫了都市文化熏染下的“謀生亦謀愛”的都市女性形象。一方面,她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與傳統言情不同,她們大多不是少女,而是對生活有相當閱歷,洗去人生幻想的年齡。另一方面,張愛玲的小說中,主角不是英雄,角色也各有自身的缺點。小說中的敘述者和主角以女性為主,敘述視角的不同,造成小說語言、人物心理的不同。張愛玲的小說中有兩類人物寫出了自己的特點:一類就是小說中的姨太太形象,另一類則是浪漫的女性形象。
比起新文學作品常常不遺余力地贊美女性的犧牲與奉獻,通俗言情小說則會濃墨重彩地去描寫那些“壞女人”以及“浪漫的女性形象”。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新文學主流作家對新女性是贊賞的,對舊女性則飽含同情。 新文學作品中描寫到母親、青年知識女性、社會底層的弱小者等形象常從正面角度進行描寫,從其觀點來看,女性在封建社會中處于被壓迫的地位,是值得同情、需要啟蒙甚至要被重新創造的,另一方面,新文學深受西方文學影響,加上思想上要打倒父權,又在成長過程中深受母親的教誨之恩,贊美女性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母題。再加上新文學作家大多厭惡封建社會風氣,對普遍世情與社會的深入程度未必有通俗作家理解得透徹,這一切都決定了其很難寫好“壞女人”形象。[7]
像姨太太、妓女這樣的角色在一般作品中總是被妖魔化為蛇蝎女子,但在張愛玲的筆下,她們的形象卻往往是家常而乏味的。《花凋》里的鄭先生的姨太太,也許曾經有過魅力,但現在卻整天在閣樓里,用縫紉機縫衣服、被套,成為半仆半妾的角色。《小艾》中的憶妃老九,雖有屬于妓女神秘的一面,也有屬于妻子的家常化的一面。在她掉光頭發后,吸引丈夫的是共同生活培養起來的默契。張愛玲認為美色只是獲取生活資源的手段,當獲得安穩生活時,大部分女性便放棄了打扮。這一結論恰與男作家相反,壞女人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生活的必須手段,當不再需要這種手段時,她們也能以家常化的方式存在。狹邪小說中不乏描寫妓女家常生活的一面,如《海上花列傳》,但那只是相對于妓女迎來送往生涯的一個對比性描寫,而不是生活常態。張愛玲則寫出了這些女性在進入日常生活后無異于常人的一面,顯示出家常生活庸常停滯,無意義的一面。
對浪漫的女性形象,舊文人通常是批判其新潮只是趕時髦。新文藝作家則容易將其理想化為左翼的、激情的代表人物。張愛玲的處理方式是將其日常化,讓我們看到浪漫的女性與一般女性并沒有什么不同,甚至更難獲得世俗的理解。
張愛玲在描寫這些女性形象時,是處于通俗言情與新文學之間的,她從女性的角度指出,這些“浪漫”的女性形象,本質上并不壞,甚至比普通的女性要天真一些,她們的浪漫既與富裕的生長環境相關,也與她們本身魅力相關,這兩者共同構成了其浪漫的特點,并使其做出一些不合世情與常規的行為,這成了世俗批判她們的緣由。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振保在國外的華僑女友玫瑰與情人紅玫瑰王嬌蕊、《殷寶滟送花樓會》中的富家小姐寶滟、《半生緣》中的石翠芝,她們無需為“謀生”而傷神,遂將“謀愛”作為人生的頭等大事。張愛玲超越通俗言情之處就是點出了女性想追求的“愛”,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一方面世俗社會不允許她們以超越道德的方式來追求愛情,如殷寶滟與老師同居,或紅玫瑰作為有夫之婦卻與振保戀愛,都不被世俗道德所接受,另一方面是所愛的男性,也依然以世俗的眼光看待她們,浪漫的女性因與普通的女性不同而獲得男性的青睞,但從實用的角度出發,小說中的男性絕不會以浪漫為出發點來選擇婚姻伴侶。不僅是振保這樣保守的男性,即使是《半生緣》中代表進步青年的叔惠,也因不敢“高攀”富家小姐石翠芝而選擇了遠走逃避。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形象代表了普遍意義上的世俗眼光,而浪漫的女性在張愛玲的筆下反而褪去光環,還原成普通人。她們的浪漫,反倒在現實世界中陷于尷尬處境。張愛玲告訴我們,現實世界是冷酷的,并不像通俗小說那般富有傳奇色彩,也不像新文學作品所宣告的那樣,精神的力量能戰勝庸俗,一個天真的浪漫主義者在現實世界中注定是進退維谷的。
三、結語
張愛玲的小說從傳統小說中汲取了養分,她非常重視讀者的需要與作品的閱讀效果,其作品并不故意塑造超人的形象,在敘述故事和安排情節時也遵循人性的發展和世俗的選擇。但張愛玲不拘泥于傳統通俗小說的道德觀和審美標準,在看似通俗的故事框架下給予讀者深思與反思的空間,在小說筆法上也超越了通俗小說的技法,達到了現代性與通俗性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