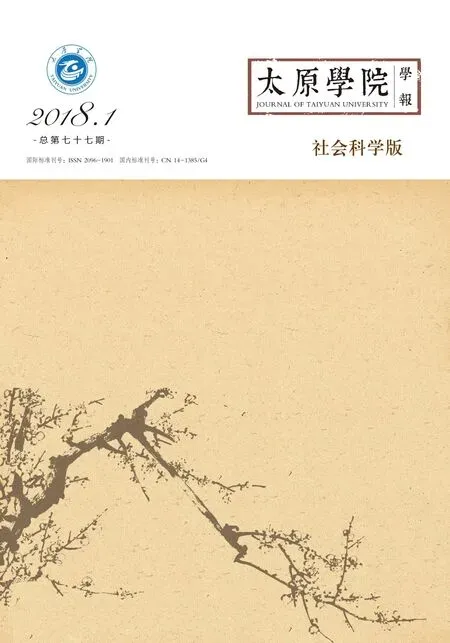《有感》:李金發是如何成為“詩怪”的?
(泰山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山東 泰安 271000)
李金發《有感》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篇詩歌名作。李怡教授質疑其有句無篇,第二節是“精彩而極有現代主義感受的,但可惜在那首《有感》中也只有這么一個孤零零的句子,而且很難想象它是怎么鉆進去的”[1]199。文貴良教授則認為,第二節不是孤零零的,因為第一節是它的一個比喻,“殘葉何以能濺血?殘葉不是枯葉,濺血不過是一種意象,正是生命消失的癥候,濺血肯定是不可停留的事件,對于一個濺血的生命體來說,生命的持續只在彈指之間。死神唇邊的‘笑’恰好迎合了這一特征,那笑短暫,不穩定,頃刻間會消失。這就是生命的脆弱,脆弱是生命走向死神的最后一步,短暫而沒有力量”[2]。本文同意文貴良教授的觀點,第二節是本詩的有機構成,但它和其他詩節是如何關聯的呢?這是需要以文本為基礎進行仔細考慮的問題,迄今已有的解釋并未能很好地回答。由于在表述我的看法時有機會與它們展開充分的對話,這里暫不評述之,而是直接進入我的解釋。
一
詩題曰“有感”。感者,感想或感悟也。因何而起感想感悟?一般地,遇事而感,對境興感。何事何境?本詩有感的現實契機是什么?好像既沒有直接說明,也沒有什么暗示。如果堅持這種看法,那就意味著我們沒有讀懂第一節。試想一種情境:秋色正濃,北風蕭瑟,詩人于林中小徑漫步沉思,在他眼前,不斷有紅葉從枝頭墜落,偶爾落在他的鞋面上。于是,詩人頭腦中閃過一個句子:殘葉像血一樣濺在腳上。但這個表達太普通了,詩人遂做了重要的改動與深化:舍棄那個自然的、容易理解的明喻表達,不是“殘葉濺在腳上,像血一樣”,而是“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把一個自然現象予以陌生化地傳達,令人怵目驚心,因為它使我們的視覺焦點與語義中心放在了“濺血”上。
更妙的是,詩人前置了一個“如”字,自然現象殘葉飄落(殘葉濺血)僅僅作為一個喻體,什么“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呢?未有任何說明或暗示,顯得十分突兀,更能激起讀者的追問與思考。
第二節給出了答案:是生命“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濺血”由殘葉的顏色聯想而來,但它的豐富的語義并不局限于此:一方面,血是寶貴的,是生命的象征;另一方面,血在飛濺,意味著生命在萎縮在消失,而這是任何一個生命都不可避免的自然過程與自然現象。于是,便有了韶華易老、生命短暫之感慨。那么,第二節——“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僅僅是明確了第一節暗含的意思嗎?
孫玉石先生似乎就是這么認為的,他說:“生命與死神中間的距離這么的近,生命是多么短暫啊!這個比喻和前一個‘殘葉濺血’的意象,如電影的兩個重疊性的鏡頭,推到人們眼前,詩人的情調就在這意象的疊加中呈現出一種可觸可視的強烈印象來”[3]202,楊劍龍教授也認為:“詩人以明喻‘殘葉濺血’比喻生命的凋零,以隱喻‘死神唇邊的笑’比喻生命的短促,詩人因此感悟到人生的短暫”[4]。亦有別樣的解釋:“人不能承受生命之輕,一旦生命被死神垂青,在死神的微微一笑中,生命將被死神所奪取”[5],但這個解釋顯然破壞了詩句的語法結構:它縮寫為“生命是笑”,如何能解釋成“在死神的微微一笑中,生命將被死神所奪取”?
本文認為,第二節應作如是字面理解:在生命與死神二者之中,死神是存在之根本,生命僅是死神之附屬物,只是它轉瞬即逝的一笑,盡管笑是溫暖的、動人的。事情大概就是這樣:愈是寶貴的,愈是短暫;或者,愈是短暫的,愈是寶貴——但終究要歸于死亡與虛無。進一步的理解可以參考弗洛伊德“兩種本能”的理論。弗洛伊德認為,存在著兩種基本的本能,一種是愛欲本能(或翻譯為生的本能),一種是破壞本能:“愛欲本能的目標在于不斷地建立更大的統一體,并極力地維護它們——簡而言之,是親和。相反,破壞本能的目標是取消聯結,故而帶來毀滅。由于這個原因,我們也可以稱它為死的本能”[6]286。死的本能更原始,更基本,生的本能是為死的本能服務的。我們可以把生命本身視為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之間的斗爭,結果是后者(死)必然戰勝個體。然而,通過個體和集體對死的本能的不斷斗爭,文明的連續性和力量得以增長。就《有感》所表達的人生感悟來說,生命雖是短暫的一笑,但這一笑就是愛的力量對死的本能(死神)的勝利。
雖然謙虛是美德,但本文仍然自信自己的解釋是目前對本詩前兩節最圓滿的解釋。第二節并非是孤零零的,它在第一節對境直覺感悟的基礎上做了一個知性的判斷。只有充分理解了第一節,才能深入理解第二節。“殘葉濺血”既非是第二節“笑”的一個比喻,亦非是平行的語義關系——因為,第一節并非是一個完整的句子,而僅是一個完整句子的一半,另一半融入了第二節的知性判斷。
二
那么,第三節是如何出現的呢?解釋者們建立了這樣的因果關系:“當一個人惑于生懼于死,必定渾渾噩噩,心靈自閉,為此郁悶、傷感,必定尋找解脫。于是就出現了月下縱飲狂歌的場景”[5]。亦即,第三節的個體行為是因前面的感悟而來,因感到生命短暫或恐懼死亡而去盡情享樂。可是,細味之下,與其說第三節所表達的是及時行樂的思想,還不如說是在放浪不羈的外表下向著死神的抗爭。拿什么抗爭呢?“半死的月下”氤氳著強烈的死亡的氣息(一反古典的溫柔的月亮);“載飲載歌”表面上無所顧忌、放浪形骸,但聲嘶力竭的喊叫“隨北風飄散”,意味著個人的聲息或意志被無情地抹掉;唯一可行的是“撫慰你所愛的去”,愛欲本能是人生短暫存在的唯一的溫暖力量。正因為生命太短暫,所以要去愛,而不是一個人縱酒狂歡及時行樂。
如何“撫慰你所愛的去”?“開你戶牖”,意即敞開心扉,毫無保留地說出你的情話、坦露你的愛意;“使其羞怯”,使你愛的人為你的大膽和愛意而感到害羞,其實就是讓她感到你愛她的幸福;不要再猶豫等待,“征塵蒙其/可愛之眼了”,歲月的滄桑已經使她容顏不再、人世的奔波勞苦已經使她憔悴了。“此是生命/之羞怯/與憤怒么?”生命羞怯于什么,又憤怒于什么呢?
有人認為:“雖然抒情主人公很渴望得到同情,獲得愛,也有敞開心扉的意愿,畢竟愛是需要心與心的交流的;但同時他又心存疑慮,擔心自己的坦誠被對方漠視,為此而羞怯,不敢邁步走出自己孤獨的天地。對自己的這種萎縮自悲,他又暗暗懊惱,自己不應有的羞怯,讓本應可愛的生命蒙塵。矛盾的感受糾結為這樣的感慨:‘此是生命/之羞怯/與憤怒么?’”[5]這個解釋違背了第四節的本意:“開你戶牖,使其羞怯”指抒情主人公的敞開心扉使所愛的人感到羞怯(這是幸福的表情),不是抒情主人公自己羞怯,非因“擔心自己的坦誠被對方漠視”而羞怯;再者,不是羞怯讓可愛的生命蒙塵,而是“征塵”使可愛的生命黯淡了。
孫玉石先生說:“詩人以酒與愛來消磨人生時光,但他內心又充滿了矛盾。不甘沉淪,也不甘自棄的心理,終于使他發出了這樣痛苦的疑問:‘此是生命/之羞怯/與憤怒么?’‘羞怯’與‘憤怒’,指愛情的沉醉與發泄之痛苦,詩人似乎在問自己,生命就應該在這種‘羞怯’與‘憤怒’中度過嗎?”[3]203這個解釋違背了本詩第三節的本意。第三節前四行表達的意思是:在死亡的根本性威脅面前,個體的“載飲載歌”既無力又無效,遂投向愛人的懷抱,引入人與人之間愛的力量,在愛與被愛中度過生命的時光,這是人類對付死神的唯一的方式而非消極地“消磨人生時光”。孫先生的解釋亦無說服力。
本文認為,“羞怯”在第四節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使其羞怯”,所愛的人因你坦露衷曲而羞怯;第二次是“生命之羞怯”,顯然對應的是第一次羞怯(生命因愛而感到幸福與充實)。與此類似,“憤怒“在第四節其實也出現了兩次:第一次,“征塵蒙其/可愛之眼了”表達了抒情主人公的憤怒,憤怒于像“可愛之眼”這樣美好的事物無法挽留住,即青春與生命不能永駐、歲月不為愛而停留;因此才有后面“生命之憤怒”的質問。
概而言之,“此是生命/之羞怯/與憤怒么?”生命羞怯于愛(幸福與充實),憤怒于死亡之不可抗拒(美好的事物終究要被剝蝕被沉埋)。但詩人為什么要使用一個疑問句,而不是肯定地表達“此是生命/之羞怯/與憤怒!”?因為人類之命運不能通過個體之理性來解決。人只能苦苦反思與追問,而不可能達成一個理智而透明的答案。于是,本詩開篇二節復又響起:《有感》對生命的思考是直覺的、感性的、詩性的。
三
李金發被稱為“詩怪”,“他的不少象征詩乍一看不知所云,語言結構上的跳躍太大,太零碎,句與句、部分與部分之間,幾乎沒有什么過渡的橋梁。在章節安排、詞語搭配上又打破了習慣的次序,中間往往有很大的跳躍,也有很多句子成分的省略,造成了種種‘無序’狀態”[7]271-2,這段話解釋了李金發的不少象征詩為何“乍一看不知所云”,但不知道這“不少象征詩”是否包括代表作《有感》?如果不包括,前引說法的說服力就要打折扣。但不包括也沒關系。我們解釋一首詩,難道僅僅止于“乍一看”嗎?當然要細看,而細讀《有感》,按照本文前面的解釋,句與句、節與節之間是有語義上“過渡的橋梁”的,并沒有“很大的跳躍”,整首詩的表意過程是有序的,所表之意是可以正常理解的。這種看法得到了唐納德·戴維森隱喻理論的支持。戴維森承認隱喻具有暗示的效果,但這種效果是如何產生的?戴維森并不認為隱喻表面上“說的是一回事,其含義又是另一回事”,他論證的是“隱喻僅僅屬于語言使用的范圍。隱喻是通過對語詞和語句的富于想像力的運用而造就出某種東西,隱喻完全依賴于這些語詞的通常意義,從而完全依賴于由這些語詞所組成的語句的通常意義”[8]294。我認為,李金發的詩歌“乍一看不知所云”,那不能怪李金發,只能怪解釋者僅僅是“乍一看”,沒有進行全面、仔細的研究與解讀(這是讀懂一個隱喻、一首詩歌必備的工作),而是選擇性地、掛一漏萬地進行局部的聯想與片面的解釋,讓文本符合自己的意圖。
那么,李金發到底是如何成為“詩怪”的呢?要明白“詩怪”是什么,就要首先弄清楚當時不“怪”的是什么。對比于李金發,不“怪”的是胡適。
胡適是五四新詩革命的首倡者,他的詩歌主張簡言之就是“詩體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9]148。按照本文的理解,胡適的“詩體大解放”就是要建構一種自然的詩學話語。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以歷史進化的眼光認識中國詩歌的變遷,以“自然”的話語方式為白話新詩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最大的、最有力的辯護。胡適把《三百篇》到騷賦文學看作第一次解放,從騷賦體到五七言古詩看作第二次,從詩到詞曲是第三次,從詞曲到白話新詩乃是第四次詩體大解放。這就意味著詩體解放的需求是內在于中國詩歌發展本身的,五四白話新詩是它的一個自然發展的趨勢,無須借助于外邦的詩歌資源[10]125-7;
2.白話新詩本身是最“自然”的,因為它破除了各種形式上與表達上的束縛,就和說話一樣: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所謂“明白如話”。但問題是如何做到“明白如話”,說話如何能明明白白、不模糊沒有歧義呢?胡適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在回答“中國同音異義之字太多”這個問題時,提到了“上下文”這種自然的解決方式:
語言文字不是一個一個的獨立分子,乃是無時無地不帶著一個上下文的。無論怎樣容易混亂的字,連著上下文便不混亂了。譬如一個姓程的南方人,有人問他貴姓,他說姓程是不夠的;人家要問他是禾旁程,還是耳東陳。但是我們說話是,‘開一張路程單’的程字,決不會混作‘陳年大土膏’的陳字。即如有人問先生的貴姓,先生一定須說‘藍顏色’的藍,或是‘青出于藍’的藍。但是我們若說‘一個大姑娘穿著藍布衫子,戴著一朵紅花’,聽的人一定不會誤解了。語言文字全是上下文的。[11]78
因為我們要理解的字詞句段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置于“上下文”的聯系之中,單獨一個字詞的意思是多義不確定的,把它置于某個語境之中,置于與其他字詞的關系之中,它的含義就可以明確下來而變得易于理解,正如周作人所說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把個體的人置于群體(世界)的關系之中來確定他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上下文”就可以自然地化解多義性,留下清楚明白、無人誤解的意思。因此,胡適極力主張“明白如話”。
3.白話新詩的音節是自然的:“一是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10]129,“句里的節奏,也是依著意義的自然區分與文法的自然區分來分析的”[10]131,新詩的聲調有兩個條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韻要自然”[10]132。可以說,在胡適看來,沒有自然,就沒有新詩。
4.“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里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便是詩的具體性”[10]134,因為寫詩如說話,說話空洞抽象不但妨礙理解,而且沒有動人的力量,內容要具體,做法要自然。胡適舉沈尹默的《生機》作為好詩的例子:
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著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
地上的嫩紅芽,更僵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
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摧折;
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
他們暗地里卻一齊換了顏色!
樂觀,本是一個很抽象的題目,本詩卻用最具體的寫法寫出,所以胡適說它是一首好詩。但胡適以為的這首好詩,我們現在并不以為它是好詩——沒有一家現代詩選會選擇這首詩以讓它流傳下去。這就表明,胡適的自然詩學與評價標準是有問題的。那么,問題出在哪兒呢?
四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弄清楚李金發的詩歌主張與其實踐表現:
1.與胡適不同,李金發自稱要調和中西,把東西兩家所有試為溝通,他反而怪異于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人心向外,無人過問中國古代詩人之作品[1]191。就《有感》而言,它的悲秋主題在傳統詩歌中十分常見,然而它的象征主義的表達方式卻是陌生化的,叫讀者乍看之下難以理解。
2.李金發詩歌的做法既不具體——“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能使我們腦子里發生一種“明顯逼人的影像”嗎?——又不自然:“殘葉像血一樣濺在腳上”,這才是自然明白的說法,為什么要用“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來表達呢?李金發有意地反“自然”。
3.有了上下文,胡適認為詩歌表意會更清楚明白;有了上下文,李金發的詩歌卻不知所云了。這正如朱自清所說:“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來卻沒有意思。他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著瞧”[12]235。一個以為靠著上下文而使語言表達明白如話,一個卻因為上下文而讓人看不懂了,因為上下文或語境的存在固然可以使詞語的某些方面或者某些表達的意義確定下來,更多的時候卻是讓詞語的意義漂移起來。因為有了與其他字詞符號的聯系,我們的理解才變得困難,而不是像胡適所認為的更加容易了。前面李怡教授的“很難想象”正是這個情況。
胡適自然詩學的最大問題就是把寫作等同于說話。說話是在即時的溝通交流,當然也是為了即時的溝通交流。胡適認為“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如何才是好和妙呢?“第一要明白清楚”,使人容易懂得,“決不會誤解”;“第二要有力能動人”,使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感動”;“第三要美”,美就是上述兩者(明白和有力)加起來自然發生的結果[13]158-9。看來,胡適的文學主張實質上是心理學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由語言文字得到了明白、正確而有力的表達,而讀者由這些語言文字也即時理解了作者意圖。這樣,寫作如面對面的說話一樣,使主體間達成了相互理解的和諧境界。
李金發的出現則讓我們意識到寫作不是說話,二者是根本不同的話語系統,寫作不是為了即時的理解與交流,而是在創造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文本。文本是由書寫而確定了的話語,按照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的論述,當文本取代了言談(說話)時,至少發生了三場大變動:首先,對話直接把一個人的說話聲與另一個人的接聽溝通了起來,說者與聽者通過對話關系而明確下來;但作者與讀者之間并不存在這種交流,它不是對話關系,相反,文本導致了讀者和作者的雙重消失:讀者遠離了書寫行為,作者遠離了閱讀行為。由此,文本面對的是任何一個可以閱讀的人,因而具有某種被無限閱讀的可能性;其次,言談(說話)情境的共享現實性直接而明確地決定了言說話語的指稱,但在書寫的情況下,這一共享的現實性不存在了,文本從明確指稱的限定中解放了出來,它擁有一個不同指稱維度,需要在解釋的過程中展開;再次,在口頭話語中,說話主體的意向與所說內容的意義之間常常重疊;然而在書寫的情況下,文本的意指與作者的意思再也不會重合,文本意義和心理意義擁有不同的命運[14]107-111。
本文認為,李金發與胡適詩歌觀念的不同就是上述文本與說話的不同。胡適對詩歌的認識是建立在對話交流的基礎上的,我說你聽,可以達成即時而直接的理解。這是一種文學功利主義: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很容易地去影響甚至改造讀者的思想感情,以利于人群進化和世界大同;李金發的反常之處就在于他的詩歌創作不是為了即時性的理解,不是為了讀者而存在,因其存在是自足自為的,是語言符號刻寫而固定下來的世界。這就是說,他的詩就是他的語言,不是他生活的時代背景,不是他的個人經歷,不是他某一時期的思想狀況。知人論世的詩歌解釋傳統到了李金發而行不通。李金發的詩歌對讀者產生影響不是通過他的感情和思想而是通過詞語與句子。朱自清說李金發的詩歌“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表明他仍然沒有真正理解李金發的異質之處;此外,認為是象征、隱喻、“遠取譬”等等造成了李金發詩歌的怪異感,這也僅僅是著眼于詩歌寫作的技術層面而言。
李金發的代表作《有感》并不難懂,只要我們以文本為依據展開全面而細致的解釋;他作為“詩怪”出現其實是把胡適提倡的“白話新詩”真正提升為“現代新詩”。
參考文獻:
[1]李怡.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2]文貴良.李金發:詞的夢想者——新詩白話的詩學實踐[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28-32.
[3]孫玉石.有感[N]//公木.新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4]楊劍龍.“在向著精細的地方發展”——論李金發象征派詩歌的藝術張力[J].新文學史料,2001(2):57-63.
[5]琚靜齋.獨異的人生感喟——李金發《有感》品賞[J].名作欣賞,2012(36):116-7.
[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綱要[G]//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卷8.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7]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8]戴維森.隱喻的含義[G]//戴維森.對真理與解釋的探究.牟博,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9]胡適.《嘗試集》自序[G]//胡適文存(卷一).合肥:黃山書社,1996.
[10]胡適.談新詩[G]//胡適文存:卷一.合肥:黃山書社,1996
[11]胡適.答藍志先書[G]//胡適文存:卷一.合肥:黃山書社,1996
[12]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G]//朱自清全集:四.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
[13]胡適.什么是文學[G]//胡適文存:卷一.合肥:黃山書社,1996
[14]保羅·利科.什么是文本?說明與理解[G]//詮釋學與人文科學——語言、行為、解釋文集.孔明安,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