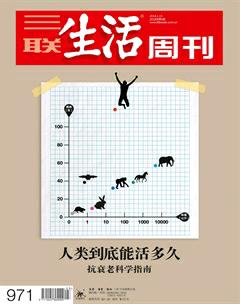在瑞士工坊,修復故宮古董鐘表
楊聃
修復之后的六枚古董機芯不僅煥發生機,還填補了各自幾近空白的歷史。曾經的它們告訴我們時間,如今的它們見證了時間。
聯合修復
經過耗時四個多月、累積近千工時的實際操作,六件鐘表文物機芯重新回到紫禁城,再次被“植入”200多歲的“身體”里,為歷時三載的文物修復國際合作項目畫上了句號。這是故宮博物院鐘表藏品的機芯部件第一次出國“就診”。
“2007到2009年,故宮博物院與荷蘭自動音樂鐘博物館也有過一次合作,不過那次只是校準了自鳴鐘的音調,在音樂方面他們是專業的。”故宮博物院文物鐘表保護修復專家王津對我說。此次,故宮博物院選擇合作的機芯專家是瑞士卡地亞制表工坊。
故宮鐘表館有千余件18至19世紀的機械鐘藏品,在還沒有《我在故宮修文物》系列紀錄片之前,好些人對王津的工作內容不太了解。他開玩笑說,有人會覺得,“在故宮修鐘表,那是給故宮里的表換電池嗎”?事實上,大部分時間王津都在做鐘表的“搶救性修復”,讓疏于養護的機械結構不再被氧化腐蝕,讓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拒絕工作的齒輪重新運作起來。他常感嘆,故宮鐘表館的藏品一輩子也修不完。
雖然鐘和表的原理大致相同,但要修復這六款直徑小到3.5厘米、大到7.5厘米的機芯,勢必需要更多精密的儀器。“分針傳動軸氧化、擺輪夾板螺塞多處被戳穿、擺輪夾板斷裂……”在《故宮博物院點交單》上每一款機芯的問題都被詳實地列了出來,而跟其相關的歷史信息只是簡明地寫著——時代:清。
六款機芯都被定為“二級”。據王津說,這是早期“老賬”上的標注,大部分故宮博物院院藏都屬于這個級別,只有少數大型復雜的孤品被定了一級,還有一部分零散的、沒經過修復的鐘表處于未定級的狀態。
初期考察階段,卡地亞的修復團隊發現六件鐘表文物在機芯內部都標注了“London”字樣,從內部結構到裝飾風格都沿襲了英國制造的特征,比如擺輪夾板只有一個觸點,時針、分針采用的是甲蟲針和火鉗針(Beetle & Poker)風格。通過在《英中鐘表年鑒》和《瑞士鐘表匠以及世界各國鐘表匠大辭典》等文獻上搜索表盤或機芯標注的鐘表匠姓名,他們一點點拼湊起跟這些鐘表文物相關的蛛絲馬跡。最終確認了方案之后,由王津師徒等四人組成的故宮博物院鐘表修復組分為兩撥,先后前往位于瑞士拉夏德芳(La Chaux-de-Fonds)的卡地亞制表工坊,與其共同完成修復工作。2017年2月,王津的徒弟亓昊楠帶隊先行“護送”機芯出發;5月,王津等二人抵達瑞士跟先前隊伍完成交接,留守等待將文物送回。
當看到負責實際修復工作的凱拉(Micaela)時,王津說他當時心里有點打鼓:太年輕了。但他也知道瑞士的情況比較特殊,在瑞士有70%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接受的是職業教育。雖然米凱拉只有25歲,跟機械結構打交道的時間已經不下10年了——她一邊在卡地亞鐘表修復部門工作,一邊在當地的制表學校任教。得益于瑞士成熟的鐘表產業教育體系,他們的技藝是從小在專業學校里經過系統的理論學習,加之畢業后進入工廠實踐操作而習得的。相比之下,國內像亓昊楠這樣的專業人員,大學畢業以后才開始接觸鐘表修復工作,遵從傳統的師承制,跟著師傅從一張白紙開始,一步一步口傳心授,累積經驗。
在瑞士,王津每天早上坐7點21分那班火車,經過五分鐘車程到達拉夏德芳,7點半準時打卡進入工坊,開始修復。除銹、打磨、燒藍等看似寂寞的工作在他看來是跟每一個零件的對話,這也更讓他佩服那些最初的設計者們。文物修復講究修舊如舊,會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零部件,為了讓機芯正常運作,某些無法修復的零部件即便要重制,也會盡可能“做舊”,跟其他部分在外觀上保持一致。“發條斷了就接一下,這樣可能比原來的短了。原發條上滿了可能表演個15回,修完就剩10回了,那也夠用了。”王津解釋道。他希望后人再次拆開機芯時,看到的還是本來面貌。
合作修復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雙面鍍金表編號182994機芯缺失的四根指針,這時離計劃中回國的日期只有一周多的時間了,遠在故宮的亓昊楠已經把古董鐘體修復完畢,期盼著機芯的歸來。電話中,他感受到了師傅王津隱隱的憂慮。
“卡地亞一方希望重新制作指針,而我們因為是文物,希望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修補補配。”亓昊楠解釋說。這一原則被故宮鐘表修復組嚴格恪守著。即便故宮藏鐘并不是每一件都被詳盡地登記造冊,但大多是成對兒的,可以相互參照。對于未能找到史料參考的孤品,只能保持原狀而不可“憑空創作”。所以,若要修復這款零件缺失的機芯,必須要給它“找回身份”。但年代久遠,唯一的線索只有表盤上的“John Ilbery London”字樣。
歷史上伊伯利(Ilbery)這一姓氏在英國、瑞士和中國的鐘表界聲望頗高,僅安帝古倫拍賣會上拍出的標有“Ilbery London”的鐘表就多達129件。2012年,伊伯利的一塊表甚至拍出了50萬歐元的高價。當年伊伯利的產品幾乎所有都出口到了亞洲市場,尤其以“中國表”而聞名。原本伊伯利設計簡潔的機芯只拋光而不加修飾,為了迎合中國市場的偏好,工匠開始對部分機芯進行裝飾,從那以后雕刻裝飾之風日漸興盛。這些裝飾工作通常在日內瓦完成,不只是機芯,表殼也鍍金或飾以琺瑯,并仿照神圣羅馬帝國時代的風格用珍珠鑲邊。此次修復的故宮雙面鍍金懷表就屬于這類經典之作。
修復團隊翻查了數千件古董鐘表文獻,終于在蘇富比的拍賣記錄中發現這款雙面懷表是成對兒的,并從其姊妹款的拍賣信息中確認了制作年代約為1790年,最后根據資料上指針的形狀和材質,復刻了缺失的四根指針。
時間的見證者
銅鍍金獅馱規矩表,銅鍍金嵌鯊魚皮透花表,銅鍍金嵌瑪瑙規矩音樂表……這些記載在故宮文物檔案里的名字取得有些拗口,看實物就覺得生動、有趣多了。以眼前這對兒剛剛經過“芯”臟復蘇的銅鍍金嵌瑪瑙規矩音樂表為例,木質基座上三層結構的造型,看似強調裝飾性,實則暗藏功能。endprint
底部八面雕花的箱體是個音樂盒,旁邊的小機關一碰,就能聽到舒緩清脆的旋律。伴隨著韻律,正面處于第二層的人偶開始“調皮”地左右擺頭。圍繞在他身旁的四頭大象寓意“太平有象”,共同頂起了一個瑪瑙箱,外部包裹著鏤空的鍍金花紋。用料這般豪氣,萬萬沒想到它居然是個“修顏箱”。打開一看,工具還挺齊全:小剪刀、鑷子、耳挖勺等整齊有序地卡在各自的位置上,其中對稱放置的兩個小小玻璃瓶,推測是裝香粉之類的容器,還搭配了取粉用的袖珍小勺。修顏箱的開蓋上頂著一只小表,簡潔的白色表盤上,羅馬數字小時刻度外圈疊加著阿拉伯數字分鐘標識。
在故宮的鐘表藏品中,像這樣輕巧的座鐘只是少數,大部分是體積更大、機械結構更復雜、表演功能更多的機械鐘。
相傳最早給紫禁城帶來這類舶來品的人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601年,他給萬歷皇帝進奉的禮物中除了世界地圖、鐵絲琴外,還有自鳴鐘。大小兩座自鳴鐘深得皇帝的喜愛,因為宮內無人會調試,利瑪竇則以養護皇帝的鐘為契機,實現了留居京城的目的。清代初期,西方傳教士經由澳門或廣東把早期鐘表帶入國內再運送進宮,成了討好中國皇帝的重要手段。1707年,第一位瑞士鐘表匠來到宮廷,隨后法國也開始以印度公司的名義與中國進行鐘表貿易。這樣的“鐘表外交”在清朝中期達到鼎盛。
繼法國鐘表之后,18世紀可以說是英國鐘表獨占鰲頭的時代。清朝的廣州官員不惜重金購買新穎華麗、做工精細的鐘表進貢。據《乾隆朝貢檔》的不完全統計,乾隆收到的進貢鐘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國鐘為佳。內務府還專門設立了“做鐘處”,仿制西方的鐘表。
自乾隆時期開始,鐘表貿易有了迅猛發展。那段時期的歐洲座鐘融合了法國路易十五與路易十六時代的鐘表風格。有數據顯示,1770年還只有一家歐洲鐘表企業與中國做生意,到了19世紀增加到了十幾家,甚至有歐洲鐘表企業在廣州、上海、香港和天津設立辦事處,直至太平天國運動爆發,這種貿易勢頭才被中斷。
如今留在故宮博物院的機械鐘藏品也是世界少有了。王津記得2006年故宮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館的人員互訪時,訪客對故宮博物院的院藏鐘表之多驚訝不已。雖然他們對史密斯的英文著作《故宮鐘表圖書目錄》早有印象,其中記載了來自18世紀的英國鐘表約有70件,出自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等30多位鐘表匠師之手,但實際的數字,比那還要多。即便是大英博物館的專業人員也不能準確判斷某些機械鐘表的由來。
相應地,當王津看到大英博物館的鐘表收藏時也詫異了一下。“在沒去之前,我還在想他們幾千件館藏得占多大地兒啊?”去了之后才發現,與大部分歐洲博物館相似,大英博物館的鐘表藏品即便時間軸更長,但都以懷表和手表居多,座鐘和重型機械鐘很少,更別說像故宮里的種類這么豐富了。他還記得一拉開大英博物館保管柜的抽屜,就能看到百十來個標著編號、包裹仔細的機芯靜靜地躺在里面,有的已經被氧化得黑成一團。當時他們負責保管和修復的師傅只有一人。算算時間,現在那位老先生也該退休了。
看著眼前重新煥發生機的鐘表文物,王津感慨無論是設計還是修復,匠人只是文物漫長歲月中的一個過客。生命終將歸于塵土,時間永恒于世。作為文物保護修復人員,他們有一種使命,和時間賽跑,讓這些文化和技藝的載體,盡可能長久地留存于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