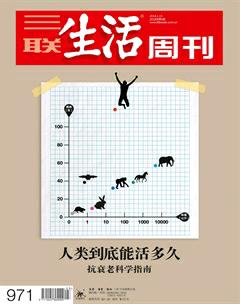格非:文學的邀約(1)
朱偉
格非真名叫劉勇,江蘇丹徒人。有關家鄉、家庭,好像很少聽格非談起過。我記憶中,經常混在一起的日子,他只說過,家鄉的河豚是真好,“等春天,到我家吃河豚去”。這一說,30年就都無下落。
他的履歷很簡單:從鄉下到上海,進華東師大讀書,讀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后留校當講師,隨后是副教授、教授。華東師大文學系當時集結了一幫文學評論精英:許子東、王曉明、李劼、吳洪森……討論小說技藝的風氣很濃。格非在《中國》雜志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追憶烏攸先生》時,署名就是劉勇。《中國》的主編是丁玲,1985年創刊,原是提供給革命作家發表作品的一塊園地。但當過“右派”的著名詩人牛漢與馮雪峰的兒子馮夏熊當上副主編主持工作后,團聚了幾位躊躇滿志的青年編輯,王中忱、林謙、吳濱之流,1985年底改刊,1986年第二期起變成一個專發新銳小說的陣地。《追憶烏攸先生》就是在改刊的第一期,與楊爭光的《老家人》一起登場的,責任編輯就是王中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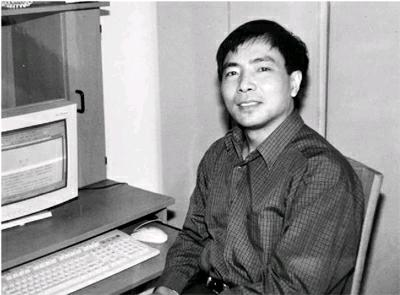
格非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迷舟》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時,吳洪森在序中寫道,劉勇是因為發現小說作者中有重名者才起的筆名。“這兩個字組合在一起,有一種朦朧說不清或說不出意思的魅力。”“我覺得,格非在構思筆名的過程中,就已經作為一個優秀小說家誕生了。”這是吳洪森的說法,他是格非的近友,格非曾帶他到過我家。吳洪森的意思,筆名其實是格非對自己創作道路的尋找。格是至,是感通、匡正,格物致知,撥迷惘而知事理。我估計,“格非”出自《尚書·冏命》中的“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愆是過失,以準繩糾過失,匡正是非。向格非求證,他說:“古有所謂‘格君心之非說,陽明多言及之。”“取筆名時,與王方紅翻字典隨意挑出二字,覺得不俗而已。當時還沒讀《答顧東橋書》,也未顧及沖撞了李清照之父的名諱。”王陽明的《答顧東橋書》,其中的顧璘(1476~1545)是金陵才俊,號“東橋居士”,小王陽明(1472~1529)四歲。
格非在新時期,是難得一位以其學術背景創作的作家。這學術氣在讀者認知度上,其實幫了他很多倒忙——他的書卷氣敘述往往會阻礙急于窺知故事因果的讀者,他們沒有耐心體會語境氛圍背后,格非煞費苦心的結構。這其實正是他小說的魅力所在。
我以為,起碼,在創作剛起步時,格是格非小說構思中的途徑,是非構成意味。他以一個意象開始尋找邏輯——《追憶烏攸先生》的“烏攸”就是司馬相如《子虛賦》中的“烏有”——“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這是一個倒裝結構的小說,故事其實很簡單:烏攸先生因奸殺杏子而被槍斃了。烏攸先生死后,警察才來村里調查,調查的結果是,杏子其實與烏攸先生相愛,奸殺杏子的是村里的“頭領”。烏攸是個有文化的醫生,頭領先燒了烏攸的書,烏攸拿刀要與他拼命時,頭領輕易就擊倒了他。然后,頭領奸殺杏子后又誣陷了烏攸,因為他早就放話說,要殺死杏子與烏攸先生。謀殺,是因烏攸搶了他風頭,挑戰了他的權威。格非不像其他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說,就形成深思熟慮,他自己獨特的結構與娓娓道來的敘述風格。小說從警察進村開始倒敘,因警察進村,“人們才不情愿地想起烏攸先生”,“人們的記憶通過這三個外鄉人的介入而被喚醒”,說明這是個封閉、沉睡的村莊。因警察進村,“我”才想起烏攸先生被槍斃那天的情景,時間已相隔遙遠。情節通過“我”帶警察去烏攸先生故居,背烏攸先生回家的守林人保留的血跡回溯后,回到“我”追憶與弟弟去看烏攸先生被槍斃時,遇到了一個小腳女人,這個女人目擊了頭領強奸杏子,但烏攸先生被槍斃后一個多月,“我們才從她嘴里知道了那件人命案的真相”。上世紀80年代,每個作家的脫穎而出,應該說,背后都有某一類型外國小說的影響。格非剛開始寫作的結構,我以為是受法國小說家羅布·格里耶與阿根廷小說家博爾赫斯的影響。《追憶烏攸先生》的故事,需要你通過分辨它的敘述,來理出因果。有趣的是時間差,它構成懸念與意味。小說的最后一段是,我與弟弟遇到小腳女人,“她決定揭露事情真相,發瘋似的朝槍斃地點飛跑”。但她“滿身是泥趕到槍斃現場,烏攸先生已經被埋掉了”。這就是時間差。
1987年在《收獲》發表的《迷舟》,才是格非的成名作。這篇小說的意象,就是迷霧中的渡河之舟,格非還專畫了一幅曲曲彎彎,從棋山要塞到榆關,由漣水進蘭江的草圖。駐守棋山要塞的是孫傳芳部,蕭旅長率部準備駐守棋山對岸的小河村前,接到了父親的死訊。小河村正是蕭旅長故鄉,蕭于是回鄉奔喪。而攻占榆關的,正是蕭旅長哥哥率領的北伐軍。小說一共寫了七天:第一天,蕭回村,見過母親。村里有算卦的道人,他讓道人卜生死,道人說:“當心你的酒盅。”第二天,父親下葬,站在母親身邊的杏(格非剛開始的兩篇小說中,都用了紅杏出墻的杏),使蕭憶起他從軍前在榆關跟表舅的學醫生涯。杏是表舅的女兒,夏末一個下午,杏熟睡在躺椅上,他曾搭過她的脈。現在,杏已經嫁給了獸醫三順。第三天,杏去茶林采茶,媒婆馬三嬸告訴蕭,三順去上游捕魚,兩天后才回來。蕭在茶園將杏扳倒,但格非描寫:“他越是用力抱緊她,她就仿佛離他越遠,他覺得自己深陷在一個巨大的泥潭里,他的掙扎只會耗盡他的生命。”第四天,格非只寫了兩行字:蕭到杏的屋里去,三順還沒回來,河上起了大風。第五天,一夜雷電風雨后,蕭帶著警衛員在激流邊釣魚,馬三嬸來告訴他,他與杏的事發,昨夜回家的三順吊打杏,杏供認了他,三順閹割了杏,她被送回了娘家,三順揚言要殺死他。第六天,蕭在父親書房里,看到父親未寄出的給他哥哥的信。信上說,預計他的部隊不久就要覆滅,孫傳芳軍已近崩潰邊緣。他在決定趕回部隊時想到了杏,于是,決定晚上去杏的娘家。在河邊,他遇到追殺他的三順與同伙,他出門卻忘了帶手槍,槍里有六發子彈,警衛員又喝醉了沒跟他。三順在該殺他時卻放了他,把刀扔進了河里。最后,第七天早晨,他從榆關回村,走進家門,警衛員就用他的手槍對準了他。警衛員告訴他:“離開棋山來小河的前夕,我接到了師長的秘密指令:如果你去榆關,我就必須把你打死。”結尾是——
警衛員站在離蕭只有三步遠的地方,認真打完了六發子彈。
這故事其實也簡單,格非的敘述,始終營造一種神秘的、如霧迷蒙的感覺。道人說:“當心你的酒盅。”那晚他就把酒杯推到警衛員面前,“警衛員偷覷了他的長官一眼,遲疑地端起了酒杯。蕭又從警衛員的眼睛里看到了道人雙目詭譎的光芒”。這是埋伏的細節。格非一開始的寫作敘述都沒有對話,他將讀者注意力調度到一個方向,指鹿為馬,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讓你玩味那個出其不意中的前因后果。我因此而喜歡他的布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