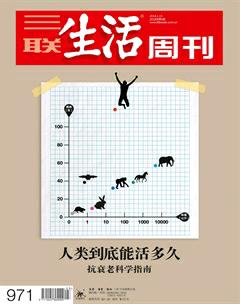周作人長孫周吉宜:為爺爺著作權打官司
劉周巖
在人生的前17年,周吉宜與祖父周作人朝夕相處,只是“我在那個年代受到的革命教育,讓我很難對我的爺爺產生親密的感情”。人生的后半段,他主動選擇回到周作人,用打官司、研究和整理資料的方式,維護周作人家族的權益,也重新理解自己的祖父。
身為周作人之孫
68歲的周吉宜是周作人的長孫,已從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的位置退休8年。他現在每日的事情是處理和周作人著作、遺物相關的各類官司,整理和出版周作人資料,自己也搞周作人研究。公眾面前,他相當程度上扮演了周作人家族代言人的角色。
他還清楚記得小時候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和別人不太一樣。“1959年我上小學的時候,人民大會堂有一個慶祝活動叫‘祖國十年我十歲,我們那一個年級的孩子基本都是1949年出生的。”平常一貫表現很好而且是班長的周吉宜理所當然地成為參加慶祝活動的學生之一,被分配了一個名額。有一天上課,周吉宜忽然被叫了出去,“教室外站了一圈人,有老師、大隊輔導員、副校長和一個沒見過的人。他們問我,你父親叫什么,我說叫周豐一,又問你爺爺叫什么,我說叫周作人。他們就說沒事了,你回去上課吧。然后我的名額就被取消了。”
周吉宜第一次覺得自己的父親、祖父好像不太平常,而且這種不平常會對自己產生影響。在周吉宜的印象里,和自己朝夕相處的爺爺只是一個溫和好脾氣的老頭。“我從沒聽他大聲喊過別人。有時候我在院子里玩,他大概有事喊我,我裝聽不見,他最多喊我兩次,我還不答應他就不再叫我了。”
和哥哥魯迅(周樹人)一樣,周作人同樣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二人一起在紹興長大,一起在日本留學,“五四”時期一起在北大任教,共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直到1923年因為至今沒有公論的原因兄弟失和,思想發展也愈發走上不同的道路。日本占領北平之后,周作人出任偽職,被稱作“文化漢奸”,歷史評價毀譽參半。
“我們院里有一棵棗樹,院里各家平分。有一次聽見兩個阿姨談論我們,‘他們家也想吃棗,也不看看他們家什么成分。”年幼的周吉宜回家問母親自己是什么“成分”,母親沒有回答,只是叫他以后不要再參與院里小孩敲棗分棗的事情,家里從外面給他買棗吃。“可是小孩都要在院子里一起吃,大家你吃一個我吃一個,我拿著外面買來的棗,和其他人的形狀都不一樣。我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周吉宜終于知道自己的“成分”,是一次放學時和同學一起回家。大家談起各自家里的情況,一個女生忽然說:“周吉宜我知道你們家干嗎的,我爸爸告訴我了,你爺爺是大漢奸!”
家里人對過往的歷史從來不談,一些事情上也會有所回避。奶奶周信子是日本人,家中有大量日文藏書,周吉宜很自然地想學習日語,但畢業于北京大學日語系的父親周豐一始終是非常冷漠的態度。“我后來看父親學生寫的文章,說他如何深入仔細地教他們日文。但是我找他輔導日語,他沒有給我講過什么。”
隨著年齡的增長,周吉宜自己通過閱讀對家里的歷史有了了解。1963年,周吉宜入學北京四中,這所聚集了全國眾多重要家庭子弟的中學處在即將到來的暴風雨的中心。“從1964年開始氣氛越來越緊張,我也看了很多書,心里有了認識。‘文革真正來的時候我并沒有特別震驚,覺得這是事情必然的發展。而且我也知道,因為我的出身,我將來也不會有什么前途!”
1966年“文革”開始后,周作人和周豐一受到批斗。周作人曾兩度寫“呈文”:“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請求公安機關準許他安樂死,未受理睬。1967年5月6日,82歲的周作人被鄰居發現于家中去世。1968年中學生“上山下鄉”風潮中,周吉宜抓住機會,借著送站混上開往東北的火車,和幾位同學一起去了北大荒,由此離開了北京,但始終離不開“周作人孫子”這一身份。
今天的周吉宜已經頭發花白,和妻子住在北京市海淀區一個普通的小區里。在他家里,一半是關于文史方面的書,一半是電子學、工程、物理書籍。“文革”將結束時,他請父親周豐一給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中仍在世的周建人寫信,問能否幫助他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工作。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周建人只是簡短回復說自己雖官至高位,但有名無實,無力相助。周吉宜隨“知青返城”風潮回到了北京,從北京鉛筆廠鍋爐工干起,靠著在四中時的理科底子和后續的自學,實現了不少技術創新,考上了大學,由工人變為工程師,后來做了中關村一家高科技公司的總工程師兼副總經理。
直到1988年,“文革”后落實政策將抄家抄去的周作人物品返還,其中有大量文獻資料,包括兩萬余封來信和周作人1936年以后的日記,這批歸還的材料讓他產生了探索祖父歷史的興趣。“歸還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這批文獻長期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他們不愿歸還,說已經申報了文物等級,屬于國家文物。后來層層上報,當時的文化部部長王蒙說,別管幾級文物,只要是人家的東西,就按政策還給人家。”周吉宜回憶。
1997年,周吉宜的父親周豐一去世,成為他將精力轉向周作人研究的轉折點。“有朋友跟我說,你別再‘不務正業了,你家里的老人一個一個去世,你再不開始整理周作人的資料,遇到問題都沒人問,而且這不是你一家的事。”周吉宜覺得有道理。他辭去了科技公司的職務,加入了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是由巴金倡議建立的集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于一身的中國現代文學資料中心。周吉宜在發揮專長為博物館建立計算機系統的同時,利用工作之便研究現代文學,整理和祖父相關的資料。
“這種興趣更多是一種好奇,我想知道真實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尤其是對我產生這么大影響的祖父的歷史。倒未必是出于血緣的情感原因,我和祖父之間的感情紐帶似乎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過。”周吉宜說,盡管祖父去世時已經和自己生活了17年,但他始終和祖父之間有著情感上的距離,“我在那個年代受到的革命教育,讓我很難對我的爺爺產生親密的感情。”
“我到現代文學館以后,很多人又開始以周作人孫子的身份看待我了。”以后的20年里,那個“非常和藹、說話從來不大聲”的老頭,以另一種方式重新成為周吉宜生活里每日打交道的人。
附逆問題的爭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北平的學界人士紛紛南下,周作人任教的北京大學也宣布和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并南遷。但隨著時間推移,南下隊伍中始終未見周作人。
到8月30日,郭沫若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知堂即周作人),以一種急切的語氣說:“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換掉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沫若還談到,因為“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較多”,所以周作人是否南下對于打擊日寇氣焰和給民眾信心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1938年2月,周作人出現在日本軍方背景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上。消息一出,舉國嘩然。茅盾、郁達夫、老舍、胡風、丁玲等18人聯名發表《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做最后的警告與挽回:“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希望幡然悔悟,急速離平……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胡適等人亦去信,勸其趁尚未“落水”之前盡快南下,保全清白。
談及周作人滯留北平,周吉宜說:“周作人不離開北平,大家最熟知的原因是他家累很重,其實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很多原因。李大釗的子女委托周作人保管李大釗手稿、稿費等一系列事情,我父親在北大的同學去參加革命,走前也把東西寄存在我家。很多這樣的事情,他負有的責任很重。”周吉宜說自己也是在整理家中留存的從未發表的信件后才逐漸有所了解。
李大釗犧牲后周作人保護他的遺子李葆華并送其到日本留學的事廣為人知,不過周吉宜認為外界的了解并不徹底。“根據我家里留存的周作人收到的來信,有據可查的李大釗的親屬向他求助的至少有11人。時間跨度從1927年李大釗去世到1945年周作人入獄持續了18年,事情各種各樣,借錢、開路條去解放區、病了住院、孩子沒學上,甚至于誰家沒錢交房租欠債跑了還給他來信說,‘我行李還在原來房東家,請周先生去幫忙打包寄到我們老家。周作人為什么要管這些事呢?是為了他自己的什么利益嗎?還真的不是。他有錢的時候幫,沒錢的時候窮困潦倒了賣東西還幫人家。”
然而無論什么原因,在北平長期滯留后周作人還是“下水”了。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被人試圖暗殺,左腹中槍而被衣扣所擋保住性命。這是繼與魯迅失和之外,周作人一生經歷中另一件眾所周知的重大轉折性事件。周作人自己的說法是這是日方為逼他下水而實施的,但還有若干其他解釋,此事在學界尚未有定論。
暗殺事件11天后,周作人接受了任命他為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這一事件通常被視為周作人正式“落水”、成為漢奸的開端。周作人這一天的日記自然成為研究中的重要材料。錢理群等學者均曾引用1985年版張菊香主編《周作人年譜》所載該日日記,其中有“事實上不能不去,函復之”字句。“不能不去”由此成為討論周作人落水心態的常用詞。
“實際上日記根本不是‘不能不去,是‘不能去!”提及此事,周吉宜的情緒相當激動。周吉宜說,根據其手中的日記原件,完整語句為“下午收北大聘書仍是關于圖書館事而事實上不能去當函復之”(原文無標點)。其中“事實上不能去,當函復之”不知為什么被誤引為“事實上不能不去,函復之”。周吉宜已將此問題發表,“不過國內學界對此沒什么反應。好像只有北大高遠東曾寫文章談及此事,但也是輕描淡寫的態度”。
周作人研究者止庵向本刊證實,這一處日記確實被學界廣泛錯誤引用為“不能不去”,原文當為“不能去”。不過周作人確實出任了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不能去”又如何解釋呢?止庵告訴本刊:“‘不能去不是說周作人不接受這個職務,而是他接受職務但不去上班,只領干薪,事務由其他人代管。這是‘事實上不能去的意思。”
無論如何,偽北大圖書館館長的職務成為周作人落水的開端,有此開頭繼而“順流而下”,周作人又擔任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并在湯爾和去世后根據汪精衛簽署的偽南京政府委任狀出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成為華北敵偽政權中的重要官員。
當被問及這些字句上的誤差是否影響對周作人事件結果與性質的判斷時,周吉宜表示:“這是兩回事。這件事反映的是國內學術界部分人對史料的態度,我拿著日記原件問過很多人,他們都說很清楚,很難是誤認。如果不是誤認,就只能是篡改了,可能篡改了之后對某些人的利益有好處。這種對史料的態度是不配稱為學者的。篡改周作人日記,不是對于史料的闡釋。對史料的闡釋和觀點有關系,觀點每個人可以不一樣,但對史料本身不能作假。”
官司與史料
周吉宜現在的許多精力放在了處理和周作人相關的官司上。在他家里放著若干個文件夾,其中放滿了20多年來十幾場官司的各類文件。周作人給后代留下的,不全是負面的遺產,也有有益的遺產,但它們在今天有時模糊了,周家決心要用法律明確它們屬于自己。“訴訟河南大學出版社的案子中法院最終判決的賠償金額少于對方提出調解的金額,但對方不認錯所以我們還是堅持打官司。我們要的是一個是非,要的是明明白白知道這是祖父和我們的權利。”
1995年的第一場著作權官司具有特別的意義。1992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未與周家協商出版了《周作人散文集》等六本書。此時距周作人去世還不到50年,其作品尚未進入公版期。周吉宜嘗試與出版社交涉,盡管做好了在賠償金額上談不攏的心理準備,得到的卻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答復:“周作人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其出版自由已被剝奪。”
抗戰勝利后,因周作人出任偽職,中華民國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對其做出終審判決: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民權十年”。因時局動蕩,監獄疏散,周作人僅服刑至1949年1月。新中國成立后,經胡喬木、周揚、沈鈞儒等研究提議及毛澤東親自批準,新中國政府對周作人的問題做了“寬大處理”,沒有再追究周作人未服完的有期徒刑,亦沒有沒收其房產,同時生活上給予一定照顧,讓其在家主要從事古希臘文學翻譯工作,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文革”前。其間1953年北京市法院對周作人出任偽職問題再次做出“剝奪政治權利”的判決,后周作人申請恢復政治權利被駁回。這成為廣電出版社說法的依據。
“聽到這個說法我們也很疑惑,我們認為周作人是有著作權的,但沒有經過法律上的確認”,周吉宜說。律師告訴他,著作權不屬于政治權利,可以發起訴訟。周家認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于是打了第一場關于周作人的官司。1996年,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和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終審均判決廣電出版社敗訴,需對周家進行道歉、賠償并停止侵權出版。“我們通過這場官司確認了周作人享有著作權并受法律保護。”自此算起,周吉宜共打了六場著作權官司,均勝訴。
明確周作人享有著作權后,更多的糾紛沒有進入法律程序,周吉宜委托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權益保障辦公室向侵權方協調解決。權保辦主任呂潔告訴本刊,“20多年里,我們為周家追回了上百萬元的侵權賠償”。被問及周作人歷史上的功過是否在調解過程中有所影響時,呂潔表示:“沒有感受到,處理周作人的侵權糾紛和其他作家是一樣的。”
2017年12月,周吉宜收到的一份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書令他感到十分不滿意。2012年他發現嘉德公司拍賣了一份周作人撰書、魯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手稿,成交價格為184萬元。周吉宜認為這份手稿是祖父的財產,可能是“文革”或其他原因流失,周家人對這份手稿享有所有權。周吉宜第一次起訴嘉德公司,一審、終審均敗訴。費盡周折獲知手稿的拍賣委托人為唐弢后人,周吉宜在被告中加上了唐弢后人,重新起訴。然而西城法院再次給出了“不能認定原告系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作為原告起訴主體不適格,應予裁定駁回起訴”的裁定。“我沒有明確的證據,但我覺得這和周作人的身份有關系。當初錢鍾書的手稿也被拍賣,楊絳很容易就查出了拍賣委托人并且叫停了拍賣。我們上訪、打官司五年,直到今天也不知手稿現在在誰手里。”周吉宜說。
為周吉宜代理此案的律師鄧澤敏告訴本刊,他覺得此次審理中在程序上有不合理之處,以至于拒絕對庭審記錄簽字,并決定不再繼續代理此案。“造成這樣結果的根本原因是拍賣相關的法制建設不完善,和部分法官素質也有關系。我覺得和是不是周作人沒有關系。”鄧澤敏說,他當初接下這個案子的初衷是推動《拍賣法》的立法完善,因為圍繞拍賣出現的法律漏洞并非個例。周吉宜決定繼續上訴,目前已將此案的上訴材料遞送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這些打官司的事不是最重要的,只是事情已經發生了,逼得我們要表明個態度。真正重要的還是整理資料”,周吉宜談他對未來工作的計劃。周吉宜手中的兩萬封周作人書信和周作人日記等材料,大多數從未發表過,但是因為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存放了20多年,所以有不少學者已經在研究中引用。“和魯博關系好的人才能看到,之前曾有日本學者去魯博申請查閱被拒絕。而且那些能看到資料的人在使用資料時有各種有意無意的選擇及錯漏。現在原件在我手里,我就更覺得把這些資料公開出版讓所有人看到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者止庵告訴本刊,他同樣認為關于周作人的基礎史料的整理工作還非常初步。“經我手發現并且第一次發表的周作人作品就有40萬字以上,其他散佚的還有更多。已有的材料也需要甄別,比如很多關于周作人的回憶錄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寫的,真實性十分可疑。周作人研究還處在初級的資料收集、整理、鑒別階段,其實還談不上真的研究。”
周吉宜說,目前學界的周作人研究,已經取得不小的成績,但“學界能依據的只是不充分的史料,基于不充分的史料給出的只能是階段性的成果。一些對周作人人品的評價,比如自私、懦弱、沒有氣節,我覺得真實的情況是恰恰相反。現在評價周作人,還太早”。
周作人長孫周吉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