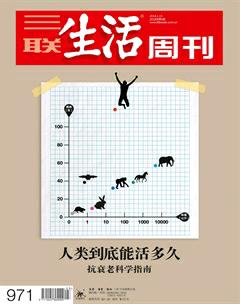狀告波音:MH370空難家屬的漫長訴訟
夕遲
美國時間2017年12月19日,站在被告席上的MH370制造商波音公司駁回了中國家屬的全部訴訟請求。此前,這些家屬的努力填滿三年零九個月的日與夜,但在法律上,從未指向一個足以寬慰人心的結果。這種努力在某種意義上等同于“拓荒”——這架迄今沒有蹤跡的飛機承載了太多疑團,復雜程度早已超越了一般概念的空難。
生離死別催生了執念和傷痛,也放大了家屬之間的分歧,每一個選擇背后,都藏著一個艱難的故事。
把波音送上被告席
從美國法庭回來后,花甲之年的文萬成想要好好學英語,從零開始。
他剛參加完針對MH370制造商波音公司的訴訟——一個當地時間2017年12月19日在哥倫比亞地區法院召開的聽證會。全程英文對答的美國法庭讓文萬成驟感無力。12月22日下午,一身黑衣、神情疲倦的文萬成,在從機場回來的地鐵上,對我表達了自己的困惑。
這是一場復雜且注定漫長的起訴,它尚未進入質證環節,只是圍繞馬航失蹤訴訟戰中的一環。
路很長,希望也微茫。文萬成等家屬的委托律師張起淮向記者介紹,家屬的索賠訴求,關鍵在于“飛機失事的直接和近似結果,是由一個或多個有缺陷和不合理的危險情況,以及波音的侵權行為和不作為造成的”。依據是,迄今沒有找到失事現場,似乎表明——波音飛機的水下定位配備是“無效的”。
這是中國家屬第一次站在原告席上對波音公司進行民事索賠,而波音實質上駁回了家屬的全部訴訟請求。
倘若追循前例,這仍將是一場至今看不到未來的官司——保守估計有七八年的訴訟拉鋸。首例發生在2016年美國家屬針對波音的訴訟,論據相似,卻至今毫無進展。
與波音一起被送上被告席的,還有馬來西亞航空公司、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有限公司、羅爾斯-羅伊斯有限公司和安聯保險集團。針對他們的民事索賠,2017年11月21日,在北京的一次庭前會議上被討論。會上情形,按張起淮的說法——仍在“互相推諉、推卸責任”。“失望”成了原告家屬的一致感受,有人已經患上抑郁癥。
“我們都感覺很憤怒。”49人中首位起訴家屬李秀芝對我說。這一次她因為簽證問題未能赴美,但李秀芝堅決地“要為孩子討公道”,丈夫去世早,上半輩子,她拼盡全力供女兒去英國留學,下半輩子,本該女兒奉養她,可那天剛滿27歲的女兒登上了MH370航班,她至今仍在為女兒充手機話費。
疲憊的起訴,無期徒刑般的等待,組成了239名失蹤乘客家屬三年零九個月的生活。然而,從文萬成這個連手勢都充滿力量的老人身上,似乎沒有一絲斗志被時間磨損。“這件事情必須要有一個說法,我不能告了,孫子來告,孫子的下一代,也要告,我們要一代一代人告下去。”文萬成平靜地說。
從那一刻改變的生活
2014年3月8日,MH370航班載著文萬成的獨生子文永勝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告下去這個決定便如宇宙公理一般,決定了他的世界從此如何運轉。
文萬成幾乎每個月都來北京。從海關出口到地鐵機場線的復雜路線,他已輕車熟路。開始艱難熟悉的,還有飛機構造、地理、法律、計算機等知識。這些努力和以此獲得的掌控感讓他心安。“什么也瞞不過姓文的。”他曾對記者這樣說。
退休前,文萬成是一名特務兵,參與過情報工作。在“找出真相”的畢生使命面前,他重操舊業,孜孜以求。另一位馬航失聯乘客家屬姜輝對我講過一個故事:文大爺有一次和一名家屬聊天,說出一句話仿佛是寬慰:“你的兒子(即使不回來了)也是烈士。”家屬敷衍回答說是,文大爺據此判定這個兒子來自政府某部門,當場對家屬宣布了這一“發現”,依據是——普通人不可能認證成為烈士。這是否經得起推敲?在推動生活一天一天向前的努力面前,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文萬成對我說,前兩年他從一個又一個“可能知道點什么的人”——官員、記者,甚至保安那里套話,一粒又一粒沙子積起來,堅硬的事實和柔軟的希冀,支撐起屬于他自己的強大邏輯:兒子一定還活著。其中,某些“獨家信息”讓文萬成成了部分家屬眼中的“能人”,比如,在所有家屬之前拿到了登機錄像,以及早期和解家屬的名單——一份連律師也拿不到的名單。
把沉甸甸的箱子拽上地鐵安檢傳送帶的時候,文萬成彎下腰,動作有些緩慢,黑白交織的頭發泛出汗水的光亮。似乎只在這一刻,這個像石頭一樣倔強的老人才顯露出一點吃力。這些東西太沉了。
一大箱子幾千頁的訴訟材料,還有電腦里這些年積累下來的超過2000G的資料;在美國心事重重卻必須惦記買禮物“討好”兒媳婦的沉重,以及“生要見人,死要見尸”這條樸素邏輯的壓迫。飛機杳無音訊,沒有一片已發現的殘骸可以被精確“認證”,這意味著希望與絕望在無限漫長的時間里緊緊依附。
實際上,早在2016年3月7日,張起淮和12名家屬就在北京市鐵路運輸法院遞交過庭前會議訴訟材料。他起先覺得“一年半左右才可能有信兒”,但訴訟因為種種困難中止,證據的采擷依舊漫長,現在,一年半過去了,他再度走進這里,這次,他估計要三年才能有結果。
文萬成舒緩的生活時鐘定格在出事那一天清晨:打開電腦看新聞,震驚地讀到頭條,從馬來西亞飛往北京的航班消失,兒子就在那架飛機上,是他開車送兒子出差去機場的。
至今“兒子出差還沒回來”仍是這個家庭談及這件事的固定說法。可是這次出差實在太久了,小孫女在日記里寫想爸爸,還自己對家里擺放的佛像磕頭,盼爸爸平安。
文萬成從不愿和記者談論與悲傷有關的任何東西。
他心里有一種擔憂,馬航的事情過去這么久,“像祥林嫂一樣絮絮叨叨”會透支公眾同情,反而不利于關注度。“踏踏實實、用法律的力量解決,才是正理。”文萬成說,而他所定義的“解決”只有一種:找到飛機,兒子回家。
“實際上,我們索賠,比方說一千萬幾千萬,價開得更高,就是逼著他們找飛機,你要證明自己沒有責任啊,你就得找到飛機才能證明啊。”
張起淮說,本次起訴的49名原告代表14名失聯乘客的家屬,涉及36個家庭,訴請賠償金額少則1000多萬元,多達7700多萬元。
文萬成向我強調,對波音,他沒有明確的恨意。令他寢食難安的是馬航搜索工作的擱淺:必須通過巨額索賠,才能把作為搜索技術顧問的波音倒逼出來,尋找飛機。
而新馬航在庭前會議上認為,責任應歸于老馬航;老馬航則認為飛機沒有墜落在馬來西亞,搜救和他們無關;波音公司給出的觀點是——飛機質量沒有缺陷,不是他們的責任。
不同意見的權利
在所有用力追求“真相”的家屬中,文萬成的努力顯得更激烈,姜輝曾說他很佩服文大爺的勇敢。但2016年3月,姜輝把文萬成踢出了家屬聯絡微信群。
“我當時沒有選擇,必須把他踢出去。”姜輝對我說,很堅決,又糾結地強調他不得不這么做。“他當時已經把一個底線給打破了……”“也沒有做得這么絕,文大娘還在群里,有什么消息文大爺還是能看到的。”姜輝嘆息。
點燃導火索的是那份文萬成一點一點打聽出來的“和解”名單:接受馬航推出的“5萬美元先期賠付”者,名單里有39人,根據后來發布的確切信息,約有60多人。
此前,姜輝和文萬成的矛盾早已浮現。文萬成和張起淮在事發當年就號召大家抱團維權,出于對張起淮代理李天一的反感,姜輝一直不信任張起淮,文大爺覺得這無疑“拖慢了尋找兒子的進程”,這是他最不能釋懷的事。而姜輝支持的律師吳晨,在早期,也因在中國政府派出的代表家屬與馬航談判的律師團中,“沒站在家屬一邊”,遭到文萬成反對。
最初,由于家屬和馬航針對賠償報價差距較大,律師團曾試圖與家屬確認是否接受和解協議,協議的基礎是馬航“全面免責”。
“他們根本不是幫家屬說話的。”文萬成聲音激烈地對我說。
簽了那份協議的家屬,從共同承擔傷痛的親人,變成了“背叛者”。但難以回避的現實考慮是,放棄這筆錢,選擇訴訟,結果便遙遙無期且未必樂觀。張起淮本人在當時接受采訪時也認為:“走訴訟程序最終究竟能拿到多少賠償,誰都說不準。”
據姜輝所說,文萬成把那份名單拋在了群里(談到此事,文萬成搖頭,“沒有,沒有這事”),這份名單在群里攪起軒然大波,那39人瞬間成為辱罵的靶心:“認錢不認人”;“年輕媳婦想再找個主”;“飛機上是你義父”……
飛機消息茫茫,失望煎熬成憤怒。尤其是,馬方的初期事故報告只有5頁紙,是張起淮口中“所有空難報告里最簡單、最敷衍潦草的一個”。對很多家屬來說,不督促馬航好好找飛機,卻為了拿一筆錢承認馬航“免責”,這種選擇看起來無異于“拿錢買命”。
家屬張川(化名)告訴我,在微信群將近一年反復質疑的同時,家里也爆發戰爭。張川的丈夫在飛機上,那筆賠償款對一個頂梁柱倒塌的家庭很緊要——老人要贍養,孩子也要供養,更何況找人本身就是一場看不到花費盡頭的征途。但張川在家庭會議上談及此事時,婆婆聲淚俱下地說她不要丈夫了,先是怒罵,而后哀求,過了一個月,腦溢血犯了,住進了醫院。
一個本就受傷的家庭就此隔閡不斷。張川的母親不滿親家對女兒的態度,兩家裂痕漸深,張川剛上小學的兒子被嚴格的“合同”束縛,只能姥姥家住一個月,奶奶家再住一個月。
“人肯定一定是要找的。”張川對我說,連續用了兩個強調詞。至今,家里有關丈夫的物品一樣都沒動,牙膏放了一年,她覺得過期了不能用了,就再去超市買一管,還是放在那個位置。
“當時大家都是不理性的,其實接受賠償和選擇和解完全是兩個概念,有些拿了錢的家屬,一樣在堅持找人。”姜輝對我解釋。但“找到飛機”的訴求那么龐大而艱難:“本來所有家屬扭成一股勁兒向馬航要人,力量多強。可是有人拿了錢,你拿錢了,大家就感覺你不用心找人了,隊伍里少了一個人,就不強了,可能就是這個心理吧……是的,我自己不會要這個錢,但是我不反對別人各有要的原因,比方說缺錢、家里有人在政府機關工作……他們沒有辦法。”
名單拋在群里那天,姜輝發出一段留言:“我們建立微信群應該是互相取暖,攜手和肇事者共同戰斗的地方,而不應該是家屬之間的屠宰場。”
在姜輝看來,攜手戰斗包括堅持,也包括力氣用盡了停下來——他認為這是他和文萬成的“主要矛盾”。誰也不知道這個已被定義為“空難史最大疑團”的飛機事故能不能等到結果。很多家屬年紀大了,支撐不下去了,選擇離開團隊。姜輝會祝福他們好好生活下去。“甚至真有要錢不要人的家屬,血緣比較淡的那種。”姜輝皺眉,“但這也是他們的選擇。”
姜輝性情溫和,聲音平緩。作為群主,他的性格成為家屬對立情緒的黏合劑,被很多年齡更大的家屬尊稱為“大哥”。他和文萬成至少有一點相似之處:從不自承悲傷,即使MH370航班帶走了他的母親后,很多熟人都覺得姜輝衰老的速度清晰可見。他自認堅強不及文大爺,等待的日子里,姜輝幻聽,失眠,沒有食欲,被醫生診斷為“創傷應激障礙”。他很長時間不敢看母親的照片,有時走路走到父母家,看著那扇窗戶,也不敢上去。他總是混亂地想著很多事,比如母親從窗戶探頭叫他吃飯,母親洗好的衣服應該掛在那空蕩蕩的衣架上。
兒子沒有死,對文萬成是篤定的信條,但對姜輝和更多家屬來說,那是一份忽明忽暗的希望,敵不過一日一夜拉長的時間。
一次,姜輝想幫父親收拾房間,被父親攔住了,說別動,等你媽回來收拾,“你弄得不對她回來又得叨咕”。姜輝無法平靜地接下這句話,甚至不能與父親對視。
面對記者,他十分謹慎地選擇了“沒有消息就不能證明人是生還是死”的表述,但母親是不是還活著,他說自己“不去想這個問題”,就像他從來沒有邁進母親的房間,那一分脆弱,被他藏在心里那個柔軟的角落。
但姜輝的堅持不少半分。MH370失聯事發后,姜輝辭去工作,專職找人,這在馬航家屬中極罕見。辭職前,姜輝是公司的銷售骨干,年輕有為,掙下了當時覺得夠半輩子花的錢。“把人找回來才是這輩子最值得做的。”姜輝說。
三年過去了,金錢上的壓力漸漸浮現,他也沒放棄,一頭扎進了由技術資料和復雜線索組成的生活中。在和馬航的溝通會議上,他拋出專業性極強的問題:國際海事衛星組織給出的衛星握手信息的原始數據在哪兒?飛機上四個ELT一個可以人為關掉,另外三個不能,是這樣的嗎?
報道說,馬達加斯加有飛機殘骸,他親自去找,和毒蛇、鱷魚擦身而過,在大浪中穩住幾乎就要傾覆的小船。但有家屬認為,他的這一努力也意味著“背叛”——去確認“飛機已經不在了,人也不在了”可能是事實。
盡管彼此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犧牲,但在和我的談話中,文萬成和姜輝對雙方的努力成效、價值觀都有質疑,這也是馬航家屬之間大小矛盾的一個縮影。
“就拿請律師來說,家屬都是分成三撥的。”姜輝說,并伴隨哲理地感嘆:生和死是多大的事啊,當你手底下的選擇意味著生和死,它就能放大所有分歧。
但對文萬成來說,三撥律師,誰干得好、誰干得不好,大家都得盯著別人,“這就能督促大家把事干好”——而其中的過程,團結、溫情,抑或爭執,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一個目標:找到兒子,還是開著那輛離別時開的車,把兒子帶回家。
放棄比堅持更難
2017年11月21日,作為馬航MH370引發的首起民事索賠案的原告,李秀芝在下午2點出現在北京鐵路運輸法院的原告席上,隨她呈堂的還有整整14箱辛苦收集來的證據。“她是第一個,往后還長著呢。”文萬成對我說。法律程序逐步啟動,讓這個堅稱“只相信法律”的老人看到了希望。
希望的另一面是等不到希望的無力。很多家屬在三年零九個月的消磨中放棄了。“身體跟不上。”一個網名叫“北方”的中年男子對我說。從小養在他家的外甥和干兒子在MH370航班上。兩年來,馬航家屬每周去外交部重申“找飛機”的訴求,但“北方”一直沒去,他腿里長著骨刺,這使得燕郊到城區兩小時的車程成了無法負擔的重量。
一直以來,對馬航家屬而言,放棄與“背叛”之間有一種難以置辯的邏輯,這讓“北方”沉浸在不見天日的愧疚中。除了工作,他幾乎不出門,甚至不再愿意出房間——之前他常常整日整夜待在兒子的房間不愿出來。北京冬天供暖之前,寒風勒緊他的骨刺,有時疼痛難耐,有時也讓他感到安心。說不定孩子在某個孤島上,也只有冰冷的地面可以睡。
“北方”有他的堅持。見到我那天,他帶著厚厚的筆記本,里面記錄著有關MH370航班的每一條新聞,每一條或真或假的“消息”,甚至每一個在孤獨時刻跳到他腦海里的“可能性”。積累一部分,他就把它們打印出來,寄給他認為可靠的機構,希望能夠“推動一點兒東西”。
“這架飛機(MH370)被一個UFO綁架了,或者掉進了時空隧道里。”我指著這一段給他看,“北方”搖搖頭,認真地看著我:“飛機沒有找到,也就不能排除任何一種可能,如果外星人拿孩子做實驗呢?”
而另一條猜測——為了“不可示人”的目的,飛機被美國和以色列的特工劫持并“技術”墜毀,也讓“北方”琢磨了一陣那“不可示人”的東西究竟是什么,而結論似乎超出了命題本身:“我對美國一直印象就不好。”
“不能排除任何一線可能。”在我采訪的家屬中,這句話眾口一聲。少了一個親人的生活必須繼續,那一絲希望也始終在燃燒。但文萬成和姜輝都知道,竭力作戰的隊伍在變小,時間終究融化了一些東西。
文大爺走后,群里很少再有爭執,“放棄”漸漸被視為一種選擇,而不再斬釘截鐵地“歸入敵營”。群里不多的聊天回歸抱團取暖的樸素初衷。北京家屬會定期發照片到群里:某天又去外交部強調訴求了,外地家屬則回復一句“加油”,一束鮮花。
“千萬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決定不再參與訴訟)是一個特別好的事情,不是說你要多少錢,重要的是你放下了一塊事,這個事情是你們無法承受的。”姜輝的代理律師吳晨曾這樣勸慰愧疚的家屬。
但如何能真正放下呢?一些家屬告訴我,他們用各自的方式用力修復著生活,雖然失去的空洞仍一戳就破。一位大姐對我說,她在離家最近的寺廟里一次又一次進幾千元的香,急迫盼望著“功德”盡快“兌現”為孩子回來的消息,卻在希望和絕望的震蕩中流干了眼淚。另一位大姐經人介紹見了一個“很靈”的算命先生,說女兒肯定能回來,她白天靠這股力氣支撐,卻害怕夜晚,仿佛黑暗會撕裂偽裝。
即使倔強如文萬成,也有藏在戰斗姿態之下的另一面。面對媒體,他斗志激昂,但只有律師張起淮知道,文萬成有時候說了一會兒話就落下淚來,他覺得這就是知道兒子可能回不來了,“哭得嗚嗚的”。
無論如何,回歸是一條注定漫長的路。2017年12月24日,一條新聞發到沉靜已久的馬航家屬微信群里:澳大利亞為MH370事件立紀念碑。消息注明了因為機上乘客狀況未明,碑上沒有名單,乘客們被稱為“失蹤者”而非“逝者”。
但這照樣在群里燒起了一輪怒火:“強烈抗議,想既成事實嗎?”“不要臉的,澳大利亞就是美國的狗,趕緊好好賣你的羊絨!”“我們就要和他斗、斗、斗、打、打、打!”
也只有在夢里那些時刻,平靜屬于他們。在一個家屬的夢里,飛機還沒有起飛,妻子拉住丈夫的手,沒讓他上飛機,一切都停留在那個時刻,直到夢醒。
醒來之后,他們必須面對的,仍然是冗長而無奈的現實。最初接近500人的家屬群,一半人已經默默退出。
因為希望的光芒看起來太微弱了。美國法官并未宣布波音訴訟下一次的審理日期,其他4名被告尚不知何時進入正式的起訴程序。而且,迄今國際上對MH370的全部起訴,都不了了之。“那些新聞越看越絕望。”一位家屬對我說。至于何時能“拿到一個說法”,律師和專家各有解答:3年,8年,10年,甚至如文萬成所說,一代一代人就這樣告下去。
“我的兒子也會相信我。”文萬成平靜地說。在家里,他格外重視孫子孫女的英語學習,爺爺干不動了,他們會把擔子接下去。
(林小陌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