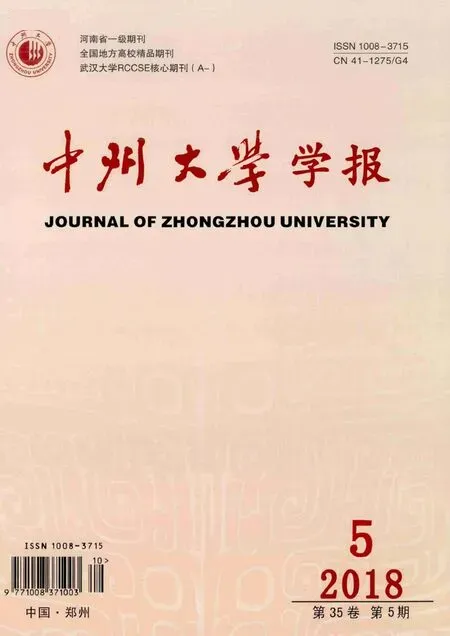王國維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類型初探
孟 勐
(河南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河南 開封 475001)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說過這么一段話:“一時代之學(xué)術(shù),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xué)術(shù)之新潮流。治學(xué)之士得預(yù)于此潮流者,謂之預(yù)流,其未得預(yù)者,謂之未入流。”[1]陳寅恪其實談的是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問題,以我們今天的理解,創(chuàng)新應(yīng)不僅包括研究對象廣度和深度的開拓,也應(yīng)包含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在19—20世紀(jì)之交,西方的研究方法開始傳入中國,中國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zhàn),傳統(tǒng)研究方法中輕歸納、不求實證、缺乏懷疑創(chuàng)造精神的局限暴露出來。近代學(xué)者們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對新思想方法的傳入采取了開放的態(tài)度,對西方科學(xué)的研究理念進(jìn)行介紹和宣傳,并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加以吸收和創(chuàng)造。王國維就是杰出代表之一。他對于中西方思想方法的融合和運用,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可見一斑。本文將試著對其研究方法進(jìn)行歸納梳理并加以探討。
一、二重證據(jù)法
“二重證據(jù)法”自提出以來,在中國史學(xué)界、考古學(xué)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其實在此之前,王國維已經(jīng)通過對甲骨文字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并初步形成了“二重證明法”的概念。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擔(dān)任導(dǎo)師時,在他的《古史新政》課上正式提出了“二重證據(jù)法”的理念,他談到:“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得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2]2-3
王國維所說的“紙上之材料”即文獻(xiàn)資料,“地下之新資料”是考古資料。就王國維那個時期而言,正是甲骨文發(fā)掘的時代。1898年,在河南安陽西北小屯村偶然出土第一批甲骨卜辭,此后專家們開始對此進(jìn)行搜集和研究。隨著甲骨文的大量出土,為我們考證和研究商周時期的社會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幾乎同時,研究者們在敦煌發(fā)現(xiàn)漢簡等古代文物,這些實物的出土對于研究古代歷史提供了更為可靠的資料。王國維的“二重證據(jù)法”就是運用發(fā)掘出來的材料來研究古史古籍的,它實則就是以實證史,以史考實,打破了傳統(tǒng)經(jīng)學(xué)從文獻(xiàn)到文獻(xiàn)的研究模式。如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中,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jù)法”將發(fā)掘出的甲骨卜辭與此時代記錄有關(guān)的論著,如《天問》《山海經(jīng)》等拿來作比較,得出《天問》中的“該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該”和“恒”都是季的兒子。由此,通過王國維的考證,商代先公先王的名號和世系基本得到了確認(rèn),殷商史的體系大致上建立起來。
陳寅恪先生在為《王靜安先生遺書》作序中曾高度總結(jié)了王國維一生的治學(xué)方法,主要分三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3]11“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即是二重證據(jù)法的精髓所在,王國維在文獻(xiàn)、經(jīng)史方面的應(yīng)用最為突出。“二重證據(jù)法”也是對清代考據(jù)學(xué)派的繼承和發(fā)展。乾嘉考據(jù)學(xué)派重視客觀文獻(xiàn)史料,它治學(xué)的根本方法在于“實事求是”“無證不信”。王國維常用的“考之古音以通其誼(義)之假借”的治學(xué)方法,就是從考據(jù)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的研究方法發(fā)展而來。但王國維在考證中,將研究材料的范圍擴大,將野史、文學(xué)作品(如《楚辭》)等考據(jù)學(xué)派不采用的資料都拿來作為參考證據(jù),以研究古史古籍,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就是由此編撰而成。“二重證據(jù)法”不僅拓寬了史料的來源,而且提出了檢驗以往文獻(xiàn)的問題,是對學(xué)術(shù)界研究方法的一大創(chuàng)新。
二、闕疑法
闕疑是指對有疑問的地方要保留,對疑惑不解的東西不妄加評論,這是一種謙虛謹(jǐn)慎的治學(xué)態(tài)度。闕疑法實際上早在春秋時期就開始使用,《論語》中孔子有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這是子張向孔子學(xué)習(xí)求官位得俸祿的方法時孔子所說,即多聽,有疑問的地方先予以保留,對其余無疑問的謹(jǐn)慎地說出,這就能減少過失。這種方法對于古文的研究,尤其是文獻(xiàn)的整理有著重要的意義。后來的學(xué)者們多繼承了孔子的這一治學(xué)方法。許慎將這一方法運用到文字學(xué)當(dāng)中,在《說文解字》中,我們常見“闕”字的出現(xiàn),其實就是表示對此存疑不能妄下定論。
王國維同前輩學(xué)者們一樣,將“闕疑”貫穿于整個學(xué)術(shù)研究中。他曾坦言自己讀《尚書》“不可解”,但同時也認(rèn)為前人的解釋是“強為之詞”,不可通,他不能贊同。這并不是王國維否定前代學(xué)者們的成就,而是認(rèn)為各時期的學(xué)術(shù)成果有其肯定之處,但也需不斷推進(jìn)。這表明了王國維實事求是的學(xué)術(shù)精神,他反對跟在古人后面人云亦云,但也不完全地否定古書,而是獨立客觀地對待古書材料,在新舊材料中相互借鑒,融會貫通,獲得確證。如在《國朝金文著錄表》中,王國維對彝器的年代進(jìn)行了考據(jù),最終只確定了一少部分器物的年代,對于大部分器物的年代和作者沒有確定的證據(jù)來把握,所以,王國維均表示闕疑。同樣,在王國維的其他論著中,對于他不能確定的事,都坦誠表明“不詳”。王國維對“闕疑法”的認(rèn)識體現(xiàn)了他實事求是的學(xué)術(shù)態(tài)度和作為一名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素養(yǎng),這對于我們今后的學(xué)術(shù)研究也是有益的啟迪。
三、系統(tǒng)分析法
朱光潛在談中國人的心理時說:“偏于綜合而不喜分析,長于直覺而短于邏輯。謹(jǐn)嚴(yán)的分析與邏輯的歸納恰是治詩學(xué)者所需要的方法。”[4]3王國維作為中西文化交匯時期的學(xué)者,他的學(xué)術(shù)觀念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他也曾說:“凡學(xué)問之事,其可稱科學(xué)以上者,必不可無系統(tǒng)。”[5]117
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被郭沫若高度評價,認(rèn)為可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并稱為中國文藝史上的雙壁。在談及研究中國戲曲的原因時,王國維在他的《三十自序·二》中說道:“余所以有志于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xué)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又說:“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數(shù)。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jié)構(gòu),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因此,我們從《宋元戲曲考》中可以明顯地看到王國維的系統(tǒng)思想。從宏觀上來看,《宋元戲曲考》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至七章論述了中國戲曲的起源及發(fā)展演變;第八至十三章以元雜劇為中心,論述了它的淵源、時地、存亡、結(jié)構(gòu)和文章;第十四、十五章論述了南戲的淵源、時代、文章;第十六章“余論”為最后一部分,是對我國戲曲的總結(jié)和影響的闡述。整個結(jié)構(gòu)清晰明確,各部分之間緊密聯(lián)系,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
除了《宋元戲曲考》,我們也可以從王國維的另一部著作《人間詞話》中看到系統(tǒng)分析法的應(yīng)用。《人間詞話》一共有64則,以“境界說”為核心展開。64則詞話按照內(nèi)容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九則,主要闡釋了王國維所指“境界”的內(nèi)涵以及與境界相關(guān)的,如“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的概念;第二部分是第十到五十二則,王國維主要通過具體的作家作品來詳細(xì)論述他的境界理論,并以境界為藝術(shù)評判的標(biāo)準(zhǔn),將詞家、詞作進(jìn)行區(qū)分;第三部分是五十三到六十四則,主要闡述了詞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其中滲透了王國維的美學(xué)理念,如對“真”“自然”的重視。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較之中國此前的詞話論著,最大的特點就是結(jié)構(gòu)嚴(yán)密。中國傳統(tǒng)的詩話、詞話重感悟,常用具體例子來說明問題,缺少分析、論證。王國維在吸收西方重邏輯、重實驗的學(xué)術(shù)觀念后,將它與中國感悟式的思維方式融合,使理論的闡發(fā)與作品的引證聯(lián)系起來;《人間詞話》除以境界為中心外,相關(guān)概念之間也組織成一個有聯(lián)系的系列,全文在結(jié)構(gòu)上三個部分之間也相互關(guān)聯(lián),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四、分類歸納法
“抑我國人之特質(zhì),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zhì),思辨的也,科學(xué)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于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6]98這是王國維在比較中西文化時所談,指出中國文化研究缺少分類歸納。分類法為實證主義所長,王國維受斯賓塞等實證主義者的影響,將分類法運用到自己的實踐創(chuàng)作當(dāng)中,推動了學(xué)術(shù)研究的發(fā)展。
在《宋元戲曲考》中,王國維對各時期的戲劇形式進(jìn)行了分類,如將宋代的小說雜劇分為六個類別:小說、傀儡、影戲、三教、訝鼓和舞隊。具體方面又對院本名目進(jìn)行了分類,在院本名目下分十一個子目,詳細(xì)闡述金院本的狀況。在另一部著作《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同樣運用了這種方法,把藝術(shù)境界分為“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兩種。“有我”和“無我”主要是通過主體的情感狀態(tài)表達(dá)的顯隱來區(qū)分的,正如王國維所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則是“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根據(jù)境界審美特征的不同可分為“優(yōu)美”與“宏壯”。在境界的創(chuàng)作中,王國維又區(qū)分為造境和寫境兩種。“造境”多為浪漫主義詩人所運用,“寫境”多為現(xiàn)實主義詩人所運用。而依據(jù)“造境”與“寫境”的特點分為“不隔”與“隔”,即是否達(dá)到物我一體,水乳交融的狀態(tài)。王國維通過對詩詞的分類,使研究對象更加細(xì)化,兩兩對立的分析,使研究更加清晰透徹,因此使得《人間詞話》作為最負(fù)盛名的詞話著作,在中國近代文學(xué)批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五、闡發(fā)研究法
闡發(fā)研究是比較文學(xué)中常用的一種研究類型,它是指將不同民族的文學(xué)理論、文學(xué)觀念和文學(xué)批評中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問題加以相互闡釋,相互發(fā)現(xiàn)。王國維處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交匯點上,他的一些思想觀念、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產(chǎn)物。王國維善于用西方的理論對中國的文論和作品進(jìn)行闡釋,在接受西方的理論中,以叔本華的影響最為深遠(yuǎn)。叔本華融合佛教的哲學(xué)思想和重視藝術(shù)的特點,都使王國維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用西方哲學(xué)和文學(xué)理論對中國古代詞學(xué)理論進(jìn)行闡釋的典型性著作,它與傳統(tǒng)詞學(xué)的不同在于王國維對宇宙、人生問題的探討,使研究進(jìn)入哲學(xué)視界。“境界說”中的“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最富有哲學(xué)意味,王國維對這兩者的劃分受到了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xué)的影響,這里的“我”不僅指審美主體及其情感,而且指人們普遍擁有的意志和欲望。在“有我之境”中,主客體是相互對立的狀態(tài),“我”的意志尚存。如:“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而在“無我之境”里,主客體達(dá)到了和諧,主體意志和情感不再那么強烈,甚至已經(jīng)擺脫個人意志的束縛。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在叔本華看來,人都有生活之欲,并受意志支配。只有意欲滅絕才能得到解脫,而這又并非簡單事,因此王國維認(rèn)為“無我之境”之作更為難得。除此之外,叔本華的審美直觀、天才論等觀點也可在“境界說”中找到痕跡。可見,《人間詞話》既接受了西方哲學(xué)理論的洗禮,又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融貫中西,對中國美學(xué)以后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王國維運用西方的理論對中國的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闡釋的代表作是《紅樓夢評論》。《紅樓夢評論》也是立足于德國哲學(xué)家叔本華的哲學(xué)、美學(xué)和悲劇觀,來闡發(fā)這部小說的意義和價值的,開創(chuàng)了中國傳統(tǒng)小說批評的新風(fēng)氣。
在王國維之前,學(xué)者們對《紅樓夢》的研究主要以索隱和評點為主。索隱即索引,是對古籍的注釋考證。這種方法類似于清代的考據(jù)之風(fēng),為從小說中考證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 。評點是受為經(jīng)書作注影響,對小說也進(jìn)行點評。王國維否定了“賈寶玉即是納蘭性德”的說法,也批評了《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的提法,認(rèn)為以此法讀小說是不懂文學(xué)藝術(shù)的特質(zhì)。王國維在接受西方的理論思想后,運用叔本華的悲劇哲學(xué)和美學(xué)觀來詮釋《紅樓夢》里人物的悲劇命運。
叔本華的哲學(xué)充滿濃厚的悲劇性,他認(rèn)為人都有原罪,將悲劇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惡人造就的悲劇;第二種是盲目的命運的悲劇;第三種是因人們不同的地位和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造成的悲劇。這三種悲劇以第三種最為強烈,是“天下之至慘也”。王國維認(rèn)為《紅樓夢》正是第三種悲劇,是人生的悲劇,而這悲劇的中心就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王國維從新的角度來闡釋《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價值,是采用西方哲學(xué)與美學(xué)觀點來闡釋中國古代小說的最早范例,開啟了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的新范式。
六、結(jié)語
王國維作為中國文學(xué)的奠基人,博通古今,學(xué)貫中西。從實證求實的立場出發(fā),在文學(xué)、史學(xué)、哲學(xué)等領(lǐng)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王國維的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是中西融合與創(chuàng)新的結(jié)果。他立足于實事求是的治學(xué)精神和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既繼承了我國前輩學(xué)者求實闕疑的學(xué)術(shù)之風(fēng),又吸收了西方科學(xué)的邏輯歸納之法,在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上將兩者加以融合,并在此基礎(chǔ)上大膽創(chuàng)新,采用中西文論互釋的方法,使其研究的視野更加開闊。王國維的治學(xué)方法除了使自己的學(xué)術(shù)研究碩果累累之外,在近代學(xué)界也起到了更新觀念、奠定范式的作用。其一生治學(xué)生涯形成的一整套科學(xué)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方法,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nèi)W(xué)習(xí)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