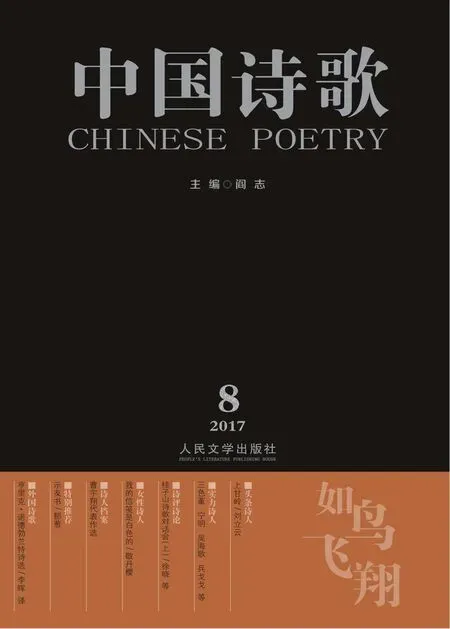語言就是思中之在
◎索耳
語言就是思中之在
◎索耳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一次來華師參加桂子山詩歌對話會,覺得非常榮幸,也有些緊張。因為我對今天對話會的這兩個命題“當下詩壇現狀問題和當代大學生寫作”都不甚了解,因此在這些問題上就不敢貽笑方家了,我就跟各位分享一點個人在詩歌創作上的思考吧。
因為我受語言本體論的影響很深,所以我在語言這個問題上有比較深的聚焦點,語言就是思中之在,就是把思想所思想的存在說出來。在海德格爾看來,語言并不是表達知識的工具,也不是邏輯和語法結構,而是對存在的意義的直接的顯現和解蔽。雖然他承認思想和語言是人的思想和語言,但是他又試圖去排除人的主體性意義,從而把思想看作純粹的思想存在的活動,從而使語言作為存在的直接顯現。排除了人的主體性,將存在本身直接顯現出來。換句話說,就是讓語言自行說話,而不是人說話。在他那里,人退居到了工具性的地位。
我覺得他的觀念有部分的合理性吧,在我看來,當下的詩歌創作應該有一種AI即人工智能的精神。詩人應該破碎舊有的語言體系,從而用一種新型的更接近混沌體的本質的語言去創作。創作應該就是肢解自己,分裂自身,蹂躪語言,而不是被套路化的語言秩序所統率,淪為語言的工具,因此,我們不妨用一種機器人的眼光去重新看待我們的詩歌本態,用一種笨拙,混沌,而又充滿潛質性的觀念去對我們的創作進行重構。所以,我愿意寫完一首詩以后,大家可以這樣認為,這首詩肯定是機器人寫的,那樣就是我感到最高興的事情了。
無論是固化的修辭也好,翻譯腔的語言和能指也好,我都不希望自己的寫作會給別人一種既有的安定感。如果這樣安定感形成了某種固定的審美觀感的話,那我更想走到它的反面去,和它對抗。語言的游戲應該是不安定的炸裂的,哪怕是隨意,就像赫塔·米勒的拼貼詩一樣,那至少也是一種嘗試。不過當然,這不是鼓勵隨意性,任何無道理的隨意的自洽性都是應該摒棄的。寫作應該是挖掘和突破自身的最大可能,而不是輕易的取悅自身。語言游戲應該是像維特根斯坦說的那樣,“……它們是比我們使用我們的高度復雜的日常語言的符號的方式更為簡單的使用符號的方式。語言游戲是一個小孩借以開始使用語詞的那些語言形式”。在他看來,語言游戲就是某種簡單而初級的原生態的使用語言的方式,就是每個人小時候所采用的語言符號形式,通過觀察日常語言的使用來反饋語言的本義和修繕理想語言,而不是用后天習得的語言秩序、用理想語言去統攝世界本質。這樣才能使得詩歌的語言保持著陌異性和永動性。
這就是我對詩歌創作的一點微薄的想法,請各位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