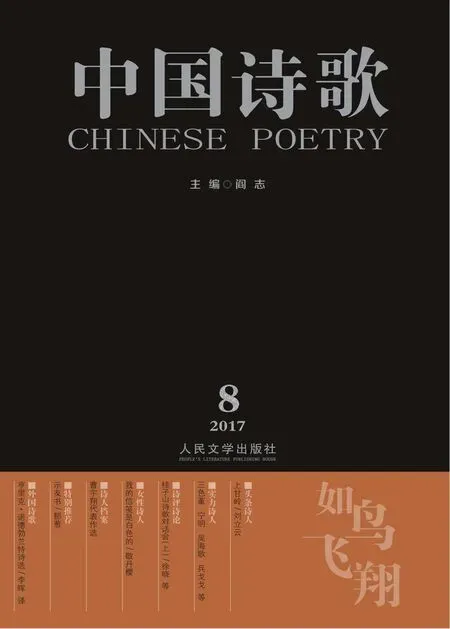結束處往往意味著新的開始
◎蘇宥時
結束處往往意味著新的開始
◎蘇宥時
為新詩正名的時機在過程中潛伏
1918年《新青年》發表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的九首新詩,正式宣告新詩乘著時代潮流的東風應運而生。但因其白話文的體式,從誕生之初便被置于同正統地位的古典詩歌幾乎二元對立的一邊。換言之,新詩的初始面貌是被“拋擲”到了漢語語境中而“橫空出世”,這樣的情形就像一介匹夫試圖跟皇子分庭抗禮,家世顯赫又養尊處優的皇子當然不會成全這樣的野心,于是便造成了此后延續不變的尷尬局面。事實上新詩也確然存在讓人詬病的話柄,比如我最近著手深入研究徐志摩詩歌的前后分期,就發現奉行英美自由主義的徐志摩也難逃這樣的窘境:典型如《再別康橋》這樣的代表作,追根究底也僅有最后一句足以讓人嘆其絕妙;其他不太知名的詩作,可圈可點之處就更為匱乏。更嚴重的懷疑在于,他的詩中有許多從西方詩歌“搬運”過來的意象或寫法,這樣的行為,無異于把西方詩歌中成功的例子以漢語書寫的方式“復制粘貼”了一次。其實這也算不得“不光彩”的事情,因為借鑒是實現提升的一個有效途徑,尤其是在新詩起步的當時。然而新詩要想獨立地存在、健康地發展,面臨的處境便不會那么簡單。
在這百年的進程中,有一個時間點非常有見證意義,那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詩歌與中國詩人曾處于輿論和社會關注的中心。但緊隨其后的,消費轉型與欲望擴張,對國人造成價值選擇上的消解,嚴肅文學受到強烈沖擊,詩歌與詩人的地位,從被眾星捧月般地環繞在舞臺的中央,一下子又為眾星所排擠、拋擲到舞臺的邊緣。柏拉圖要將詩人逐出理想國的預言一語成讖,現實中的詩人們被主流社會“放逐”,日漸與“底層化”、“邊緣化”這樣的詞匯相伴為伍——這樣一個“邊緣化”的進程卻是使動的、被迫的,充滿無奈。然而兩方抗衡,實力懸殊,社會的大多數結成一股強大的異己力量,詩人便淪為孤獨而可憐的少數,在黃昏時、在黑夜里,數著自己的星星,把呼聲肢解為沉默。
談到新詩誕生的原因和使命,概括性的表述便是“對時代新精神的響應”。施蟄存在三十年代就說過,新詩是現代人的新詩,免不了也包含了現代文明的一切在內,但這還不是它的本質上的新。在本質上,新詩之新是其情緒之新。它應該是“道前人之所未道,步前人之所未步”。忙迫、變化、速率、噪音、丑惡、恐怖、不安定、不寧靜,我們生活在現代,我們的經驗不同于前一二個世紀,生活愈加復雜,情緒就愈更微妙。可見新詩的誕生和發展,都是歷史的客觀助產。存在即合理,盡管有著不少懸而未決的疑問,但沒有一種文學體式是絕對完美的,同樣也沒人能夠推翻新詩存在的根基。當代人要有自己的情緒載體,而新詩正是合乎時宜的一個得力工具。
不論新詩詩人如何自信自足,新詩至今仍是副產品般謙卑地存在,或被視為非主流文類。新詩的邊緣化一方面歸根于歷史遺留問題,另一方面自身建設也難逃其咎,這一點在接下來的第二部分中會交叉討論。新詩不遵格律、門檻過低、魚龍混雜,大概也會被視作先天缺陷。而最近北島等詩人在豆瓣上推出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以及“為你讀詩”、“朗讀者”等節目的熱播,借助新媒體的傳播手段,新詩脫下禮帽和襯衫,換上平易近人的T恤,重新走進大眾的視野。這似乎表明:沉默已久的新詩終于肯為自己發聲。新詩曾一度想要爭奪文學殿堂的圣杯,如今又換了種姿態,這一自上而下的路徑也許是好的;在理想貧血的當下,也許是一劑喚醒浪漫意識和人文春風的良藥。
有比照就必須提供參照系。我們之所以能對古典詩歌蓋棺定論,是因為時過境遷,今人再難制造出當時語境、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我們不需要用試圖在古詩詞上超越古人來證明自己的不服輸精神,因為新詩是我們的語言,即使它目前還沒有古詩詞的積淀或所謂成就。作為新詩的寫作者,我當然希望為新詩正名的那天盡早來到,但理性告訴我:為新詩正名,可能永遠是個進行時的過程。
新詩的審美尺度:私人話語的上升空間
憑我自身的寫作經驗,我有個習慣就是經常回頭看自己以前寫的詩,做自己的頭一號讀者,這時就會發現先前的詩歌良莠不齊,有的耐讀,回顧兩三次也覺得還不錯,有些則不然,回顧第一次就覺得爛。那么“好”與“壞”究竟處在怎樣的分野呢?我自問評判高低優劣的標準,卻無果。肇事者通常是用直覺,但這要求讀者的審美修養到達了一定的水準,否則直覺會時常害人犯錯。而培養大多數人的文學嗅覺,是另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
如果說當年新詩發展尚不成熟,重要原因是白話文還沒有“崛起”,我們的新漢語還處于嬰孩期,那么在白話文運動以后的數百年時間里,直至普通話在全國大規模普及的今日,已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要給新詩進行一次籠統的分期,我認為分為早期的“白話詩”和后來的“現代詩”就足以明了。當今的詩人們已然能將現代漢語應用自如。那么,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被悄然置換成新詩審美尺度的選擇。
按照尼采的說法,人是美的尺度,也確然如此。詩歌從筆下分娩之時詩人便已死去,我很贊同巴赫金的觀點。我想以“美”的生產者為本體出發探討新詩審美尺度的問題,其中最明顯的一條線索是:私人話語的膨脹增加了審美的困難。在近幾十年的時間里,新詩寫作的私人化程度明顯增強,被讀懂、被接受的難易程度以及讀者的反饋似乎已不列入詩人的考慮范圍內,這就很容易造成“寫作——傳播——接受”鏈條的斷裂。回顧曾經擁有大量讀者的朦朧詩,經歷了八十年代初期的黃金時代,之后因部分詩文本中意象系統過度密集龐雜,充斥虛假玄思,聯想隨意牽強,導致作品由朦朧走向晦澀,遭到讀者的反感和拒絕。許多過去紅極一時的朦朧詩人開始少寫詩或不再寫詩,朦朧詩寫作群體逐漸走向解體。這或應當成為當代詩人進行選擇之前需要思考的一個前車之鑒。
從去年下半年接觸到余秀華的詩歌,就對她產生了較大的興趣,這主要基于我對她印象的反轉——從未讀其詩先聞其名的些許“反感”,到細讀其詩竟有點陪她一起大哭一起大笑的“沖動”。余秀華從文學的背面出發,用鄉野、酒瓶和殘缺構成一個獨特的敘事空間,在這樣的空間里,她練習著同生活的拉鋸,用手中的筆試探生命的極限。她克制內心蟄伏的愛火噴薄欲出的強烈,又以淡淡的感傷回避著聲淚俱下的低級訴苦。我關注她的時間也不久,讀過兩本詩集,平時有空逛一逛她的公眾號,遺憾發現她近期的詩歌也沒有特別出彩的地方,似乎有點不進則退的傾向……這些且先不論,我覺得從她身上還是得到啟示更多,一是作為一個詩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對詩說話,但現在我們和詩之間隔著太多的阻礙,時代、資本、評獎等等總是企圖蒙蔽我們遠眺的目光。故而不忘初心,是成為真正詩人、寫出優質詩歌的首項必修課。二是一成不變的創作勢必阻礙前進的腳步,新詩寫作最好加入點游戲精神,或及時開始某些探索性的實驗。反復言一種情,尤其以同樣的聲音、語調去表達內核相同的觀點,只會給自己、給讀者造成味同嚼蠟的沒勁。
據一些批評家的看法,當代詩歌的敘事性在直線增強——詩人直面個體真實的生命體驗,以接近口語的語言表達方式,綜合運用各種敘事手法,復現人們的日常現實生活場景、具體生存狀況和個人獨特心理。這樣的詩歌觀念和寫作方法固然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在某種程度上,或許還可優化詩人心理結構。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新生代詩人中已經有一部分人開始把敘事性引入作品,如于堅的《尚義街六號》,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李亞偉的《中文系》、《生活》等等,已經呈現出使用口語、講述生活以及反諷的特點。隨著時間之軸的不停轉動,“真理”之曙光日益明晰,許多詩人加入反思討論后毅然擺脫了過去意識形態幻覺下贊歌式的抒寫,而走向了以敘事手法表現個人經驗的道路。敘事性是一種形式,而個人經驗的輸入、私人話語的生成始終占據核心。私人話語的上升空間究竟有多大?是否存在一個屋頂式的阻礙,來預判私人化寫作的價值?我聯想到北島的《迷途》一詩,直至近年才被人了解其中的真相是紀念妹妹的溺水事件。但假如當年人們知悉了這一事實,這首詩便會因視角的狹隘而輕易被宏大敘事的主流偏好所淘汰。如今的時代更開放、更自由,詩人也逐步從群體性創作中脫離出來,為自己言說,這是否意味著私人話語的上升空間直指無限呢?不然。詩人要有個性,但又不能過分自信。假如一首詩里全是自言自語的叨叨念,無法喚起共鳴,無法引發加斯東詩學理論中所提出的“回響”——這也是不尊重讀者、蔑視他人的表現。更危險的是,在敘事性詩歌的私人話語中也出現了隨意化、過度化的跡象,如惡敘事、身體敘事、簡單敘事、口水敘事等的濫用,無疑偏離了詩歌的本質,以無辜的“新詩”之名為惡俗趣味的滋生提供土壤,進而破壞詩歌生態,對新詩的健康發展帶來的影響絕對是弊大于利的。
在自己的寫作實踐中我也發現:消沉和聲張都是語詞的病態。無人為你的頹廢埋單,也無人因你的跋扈喝彩。語言和文字并不負有將心緒精準傳達的義務。過于簡潔會顯得淺白平庸,過于繁瑣則又陷入奇淫巧技的旋渦,這是一個無定形的尺度,天平的任何一邊傾斜太多無異于矯枉過正,都會引發危險。我想探求一個調和的寫法。新詩的自由是補償個性的缺席,但信馬由韁會摧毀新詩的自塑之路。不論是追求自我抒寫的目的,還是強調現實關照的滲透,都應意識到瞬間的審美愉悅是暫時的,價值訴求所傳遞的信息才是長久的。一旦新詩中沒有注入價值關懷,無異于靈魂缺失的狀態,形式再出眾,也是經不起歷史之海遴選而在岸邊曝光而死的空殼。這也就是,不論一首詩的寫作初衷如何,最好還是有智性的參與。我們要的是詩,不是分行的句子。私人話語本身并無有害的天性,如果詩人能夠做到“以個人生活的點帶出時代的面,寓意式地反映出了一個時代人們心靈的變遷,對現實生活的荒誕進行探尋,對個人生活中折射出的社會歷史現象進行深度追問”,就是成功的。
不斷地否定,不斷地開創,才會產生螺旋上升的連鎖反應。有些人認為,海子的死標志著新詩寫作在農業文明審美意象的終結,而顧城則以更加殘忍的方式結束了中國新詩的自然審美意象,然而這些“結束”并沒有驅使新詩走向早夭的結局,相反,結束處往往意味著新的開始,如今新詩發展的態勢更加多元化。“文學和詩歌永遠不可能單純,它們是文化進程中的一部分。”我認為新詩的發展不需要立法者,只需要探索者。或許詩歌審美的無定態和多重性特質正是新詩趣味之所在,我們不要戴著鐐銬跳舞。這是一項歷史的任務,它的完成最好是交給時間。
加斯東·巴什拉的詩學著作里有一條我很喜歡的形容,他說“詩歌形象是心理形象中突然出現的異常”,盡管這一觀點牽涉到現象學和心理學,但它的意旨是簡明的。我認為詩歌是所有文學體裁中最具創造性的,因為它強調字數的有限性,要求詩人具備水平較高的濃縮和煉字能力。而這一特點又恰好跟當今高速的生活節奏、碎片化的閱讀習慣相契合。同樣的還有意象的新奇性和情感的爆發性。詩歌在短短的篇幅里包藏著水一樣的張力同時孕育著黑洞般的引力。最近在讀張棗的詩,感慨于他的英年早逝無疑使當代詩壇痛失一枚精致而碩大的玉石。在寫作工序上,他獨特的技法令人嘆為觀止——把古典的、唯美主義的詞匯巧妙而精準地降落在深受西洋眼光熏制過的語境中。因此他的詩不論在節奏上,還是彈性上,都極具匠人式高超的表現力。
武漢的空氣很浮躁,在這里生活了二十年,感覺靜下心來寫點深刻的東西,還是有難度的,也可能是自己尚年輕,感知力也有限,但是當我觸碰到詩,詩便主動迎上來,為我打開一扇門,它說:這里有一片未知的世界,你是你自己的引路人。歡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