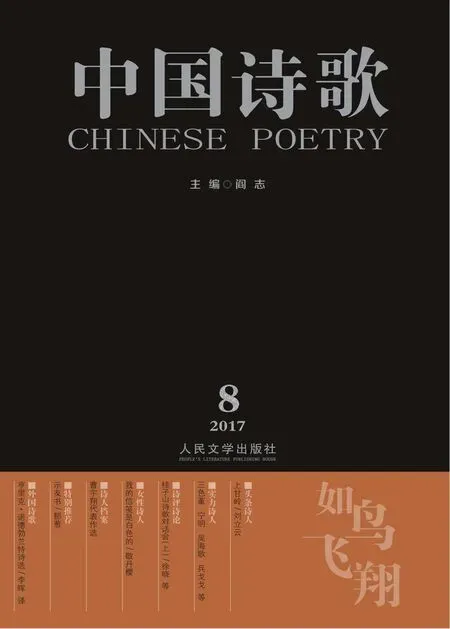關于詩歌的幾個想法
◎莊 河
關于詩歌的幾個想法
◎莊 河
存在的詩人
“科學的飛速發展很快將人類推入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人們掌握知識越深,就變得越盲目,變得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就這樣掉進了胡塞爾的弟子海德格爾的一個漂亮的、幾乎神奇的叫法‘對存在的遺忘’那樣一種狀態之中。”今天,當我們開始努力追尋,奮力為白話詩歌擬一條“再出發”的路徑時,也許越是急迫,越是意味著我們開始慌張了。難以避免的一個問題是,在今天詩歌失落了。海子的時代成為了神圣殿堂遙不可及的夢幻。我們越是精準地了解詩歌,掌握的關于詩歌的知識越多,我們就越盲目。世界、自我與生活,詩歌在這些存在當中退場了,或者說詩歌遺忘了這些存在。詩歌的寫作仍在繼續,但詩人們不再仰望星空,而是閉著眼睛低頭行走。
白話詩歌的寫作自胡適先生開始,此后,關于詩歌的韻律、語言、修辭、形式等的論爭,百年來此起彼伏。但似乎對一個近乎淺薄的問題,我們遺忘了。那就是為什么寫作詩歌?昆德拉曾言:“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理解并同意赫爾曼·布洛赫一直頑固強調的:發現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據此也許對寫作詩歌可以給出這樣一個輪廓:發現惟有詩歌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詩歌惟一的存在理由。
因為有這樣一種東西,是只有詩歌才能發現的,因此詩歌存在,因此我們寫作詩歌。正是詩人,也只有詩人才能夠實現這種發現。同時,正是這種實現確證了詩人作為個體的文學身份,而非社會身份。(個體的存在通過多重身份來完成,其中包含文學身份、倫理身份,法律身份、職業身份等。)
一種身份的確證,是一種可能性的確認,一種合理性的表達。百年前先輩們確證白話詩歌的合理性,是為白話這樣一種語言形式的詩歌發生做一個辯爭。今天我們確證詩人的文學身份,是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中,在不自覺的“對存在的遺忘”狀態下,在詩歌與現實與自我的對抗之中開始的。每一種身份的發生,都是在排他性的限度中建立的,詩歌也不例外。
詩人的文學身份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某種程度上講,我只能就這一問題所延展的邊緣來談。在這種身份延展出的眾多脈絡中,以寫作作為接近詩歌的觸點。并且,最需要注意到的是,詩歌的發生絕不依靠談論,而是具有的無限意義的寫作。寫作才是實現詩歌發現那惟一的,并只能由詩歌來發現的東西的惟一途徑。以詩的方式接觸自我、人生、世界,實現詩歌在各個方面的擴張,是今天的詩人們可能要做的。
變奏的藝術
在描述輕與重時,貢布羅維奇有一個既荒唐又天才的想法。他說,我們每個人自我的重量取決于地球上人口的數量。之所以談到這個問題,是因為輕與重的變化涉及詩歌的一種變奏。它也可以被稱為節奏或者韻律,但變奏這一詞匯不僅包括詩歌的誦讀因素,同時也包含誦讀這一再創造過程。這就好像是戲劇,劇作家的文本創作完成之后,必得有導演、演員、觀眾等的介入,戲劇才具有某種完成意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完成是短暫的、不可復制的、持續更新的。與戲劇藝術相類似,詩歌同樣存在著這樣的狀況。
詩歌這一藝術形式自誕生以來,便與誦讀存在著先天的聯系。每一位誦讀者對詩歌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側重也有所不同,甚至誦讀與誦讀者的學識、修養、經歷、情感、時代等因素都有直接的關系。這同樣是不可復制的、短暫的、持續更新的。在舞臺上或者交流中,誦讀的發生都帶有變奏的性質。變奏,是米蘭·昆德拉在劇作《雅克和他的主人》中提出的。這是昆德拉以戲劇的形式,對狄德羅的小說《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這部小說進行的“變奏”。戲劇在內容、人物、情節等方面繼承了小說,但實現了昆德拉對小說提煉出的“理性”內核的再表達。
就誦讀本身便是一種藝術形式而言,誦讀是誦讀者對詩歌的一種變奏。我曾隱約記得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在輪船上為人們誦讀,他時而激情澎湃,時而悱惻纏綿,感動了在場的聽眾們。事后人們才知他誦讀的不過是一份菜譜,只因他使用的是在場人們不懂的一種語言,這一行為才得以實現。由此也許可以說,語言的陌生化在此完成了誦讀對詩歌的變奏。
誦讀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表演,它是詩歌完成性的體現。詩歌不僅需要文本支撐,同時需要誦讀支撐。或者從更為綜合的角度而言,詩歌不僅需要形式上的視覺效果,同時需要誦讀上的聽覺效果。從這個角度,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淺略的判斷:詩歌,是一種視聽結合的產物。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認同,語言不僅是純思維性的存在,也不僅是視覺觀感或者抒情的存在,它還應是聽覺上的存在。某種程度上講,之于前兩者而言,聽覺于語言似乎更具基本意味。
在整個誦讀發生的過程中,聽眾的藝術修養同樣是不可忽視的。這部分人與讀者部分地重合,但又存在著對抗的性質。視與聽兩種進入藝術的角度,決定了他們對詩歌將會產生的不同認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當誦讀行為在詩歌的接受中發生時,詩歌即轉變成了一種集體行為,集體欣賞,甚至集體表演的形態。
詩人、誦讀者、讀者、聽眾這四個因素都是詩歌發生時不可模糊化的。從接受學的角度而言,文學作品只有在被接受后才真正完成。從這個角度而言,詩歌這種特殊的體裁,決定了它的無限性與永恒性。詩歌具有與時間并駕的包容性。回到本部分最初提到的輕與重的問題,我們發現似乎在詩歌的視聽融合與對抗中,自我的輕與重成為了詩歌的核心。如何把握輕與重以及誦讀這一藝術形式,也可能是今天青年詩人們需要注意的。
風格的味道
具有明晰意義的詩歌,語言晦澀、表達朦朧的詩歌,碎片化意識流動的詩歌等,每一種風格的形成,其實就是一種理解世界方式的被發現。某種程度上說,風格的形成既要產生自我,又要突破自我。比如詩人——我在關于詩歌的想法表述中,不談詩人應該如何,只談他們可能如何,這種可能指向猜測也指向已發生——他們可能創造一個色調濃稠的小世界,也可能將生活引向抽象的表達,還可能關注到孤獨、無聊以及艱澀的生活,但如果他們無法脫離性別的限制,無法在寫作時拒斥自我,無法為自我謀劃一條生路,在被修建好了的公路上,終有一天他們會揮霍掉自我的額度。
當寫作建立了一種自我對世界的體驗后,我們可能要做的不是加固它,而是放棄。如果手仍緊緊握住被占有的路口,路的盡頭則很難是出口。我們不能貪心,但我們可能要有一個對是否完成了自我構建的明確判斷。這一點很難,因為自我這一詞匯指向的存在本身,便是極端矛盾的。換句話說,對一種風格的建立其實是在假設的條件下完成的。我們必須把前提設置好,才能開始探究可能的結論。
一種風格的建立絕不是簡化感覺,而是要釋放感覺。阿奎那在談到靈魂時曾做過這樣的一個論斷,大致是說當把靈魂從肉體當中分離出來,那么剩余的這部分不能被稱為肉體,也不能被稱為靈魂,分離出去的那部分也是。我想,對待感覺這種體驗與想象世界的方式,我們不能切割、不能規訓、也不能簡化,能夠怎么樣,這很難說。或者其實可以這樣說,詩人的風格只能是這樣的一種形態:不是……;而不是這樣一種形態:是……。在寫作詩歌時我們可能要做的是去否認,而不是判斷。這種建立風格的方式是將自我圍困起來,讓詩人猶豫起來,在生與死的兩個端點之間。
我以海子跟顧城的自殺來明確我的想法。自殺這一行為本身極具反抗性——在談論這一點時我避開了倫理的限制,不去考慮自殺的任何不可取性——因為它打破了一種秩序,即生命的產生與死亡被一種異己力量掌控,而非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講,海子跟顧城為自己死亡了,不是為他人活著或者被支配結束活著這一行為。他們做的就是釋放,當然,我不對這種釋放的方式做任何的評論。總之,風格這一問題跟所有問題一樣,都不適合高談闊論。詩人們可能做的是寫作,而不是發表長篇演說。
附件:
一個很機械的,被簡化的方式是:如果是寫作者,讀詩的意義絕不僅僅是閱讀,而應是研讀。或者說,應該把作品通過拆解和組合的方式來讀。關注詩人的切入點、意象、模式等,這種時候尋找問題往往比學習寫法更重要。當然,這種方式似乎破壞了詩歌的整體性,在很多人的心里,詩歌是僅僅需要感悟而非分析的。這是我們的偏見,也許還是讓我們長期無法脫離困境的原因之一。在讀詩的過程中,偏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我們慣于尋找同類,同時消除異類。也許可以做這樣一個判斷,校園詩人在寫作時似乎存在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們讀過詩,但并未研讀,也并未深讀,但是我們卻動筆了。
作為詩人,我們必須寫下去。能寫多久,寫作是否受到重視等問題不是我們要考慮的,這些應該交給學者以及批評家們。多數時候,我們逾越了。以經驗來談,大多數人寫作的時間都極為短暫,似乎熱血澎湃之后,只有干涸在等待。堅持在今天寫作詩歌的人之中,是勝過天賦的。某種程度上而言,我們對待詩歌寫作時把理性關在了門外,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比專制。所謂理性,即是不斷地壓制自己想要完成詩歌的沖動,這一點至關重要。源于抒情,指向想象。
本文所談及的詩人指涉寫作白話詩歌的寫作者,詩歌以現代漢語寫作為范圍。(本文不以新與舊來作為劃分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的準繩,而采用以詩歌語言樣式的轉變作為標準,因稱白話詩歌而非新詩。)題目龐雜,擬就詩歌淺略談談自己的幾個想法,未得展開,還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