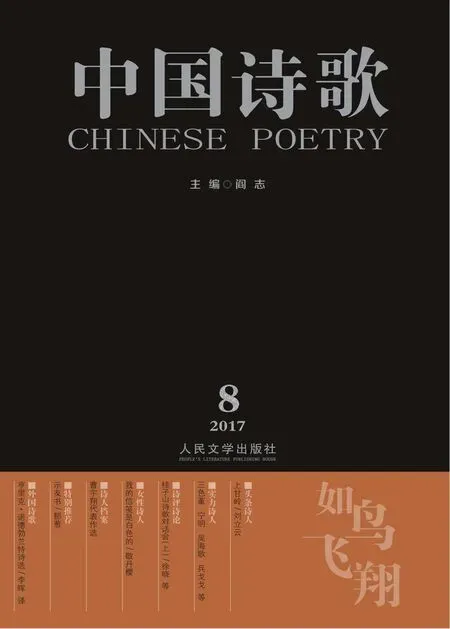回望一場戰爭
□劉立云
回望一場戰爭
□劉立云
忽然想到上甘嶺,想到東北亞的那場遠去的戰役曾是何等的慘烈、吊詭和波瀾壯闊。再有消息說,國外的軍事學院紛紛把它作為經典戰例列入教科書,就想,我們作為戰爭一方,打得那么悲壯,那么驚天動地,怎么可以熟視無睹,等閑視之?又聽說在西方的文獻中,還有上甘嶺戰役的專屬詞組——Battle of Triangle Hill,便鍵入百度進行搜索,果然,關于上甘嶺戰役的信息蜂擁而至。
上甘嶺戰役是二戰以來最典型,最殘酷,規模也最大的一場陣地戰,今天回頭看,已是空前絕后。因為由西方十多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在飛機、大炮的配合下,向上甘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兩座高地,發起一次次瘋狂進攻;中國人民志愿軍也在己方炮火配合下,對聯合國軍發起一次次反進攻。陣地幾十次易手。在相互攻防中,血肉橫飛,日月無光。林彪聽過戰報后,稱上甘嶺為“血磨子”。但上甘嶺戰役之后,精確制導橫空出世,士兵在戰場上冒著炮火沖鋒和反沖鋒的戰爭方式逐漸銷聲匿跡。
中美兩軍在第三國拉開架式,展開正面大搏斗,這是第一次。戰役初期,美國人用武裝到牙齒的重炮、坦克、戰略轟炸機和火焰噴射器,企圖一舉奪取志愿軍的那兩座高地,但遭到沒有空中支援、武器也相對落后的中國人的迎頭痛擊——他們勇往直前,以命奪命,用氣吞山河的獻身精神,在僅有3.7平方公里的戰場上,把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打得難解難分,不相上下。歷經十二天激戰,率先投入戰場的美7師被打癱打殘了,被迫退出戰場。這標志著伴隨新中國誕生而站起來的中國人,不懼怕任何對手,即使強大如美軍,從我們身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而在世界戰爭的舞臺上,以志愿軍出現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此一戰成名。
水無常形,兵無常勢。美國駐韓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司令范弗里特將軍對上甘嶺發起上甘嶺“攤牌行動”時,原定只投入美7師一個營。但戰爭打起來就由不得他了,最終不僅動用了美7師九個營中的八個營,而且投入了韓2師。美軍預計死傷200至250人,結果死傷不下2000人(中方統計為8000人)。中國人民志愿軍除第15軍全部投入外,還投入第12軍副軍長李德生率領的一個師。換句話說,在上甘嶺,中美兩軍把一場原本規模不大的小戰斗,打成了一場大戰役。
先后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李奇微和克拉克將軍,分別對朝鮮戰爭說過一段有意思的話,今天讀來別有趣味。李奇微說:“要不是我們擁有強大的火力,經常得到近距離空中支援,并且牢牢控制著海域,中國人可能已經把我們壓垮了。”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名義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的克拉克將軍說:“這協定暫時停止了,我虔誠希望它永久終止了,那個不幸半島上的戰爭。對我來說,這亦是我40年戎馬生涯的結束。它是我軍事經歷中最高的一個職位,但是它沒有光榮。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次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
在上甘嶺,中國人民志愿軍同樣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一支純粹從田野里走來的軍隊。這支軍隊的士兵是農民,將軍也是農民,只不過他們的將軍是比士兵更早幾年或十幾年投身戰爭的農民。上甘嶺戰役六十多年后,這支軍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兩個軍委副主席雙雙陷進腐敗的泥坑,觸目驚心的事實告訴我們,一支農民的軍隊要成為一支現代化軍隊,必須經歷脫胎換骨的蛻變,道路曲折又漫長。如果覺得一支軍隊擁有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就能立于不敗之地,這不僅不切實際,也是幼稚可笑的。
1972年,上甘嶺戰役整整20年后,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意味著新中國建立后中美相互隔絕的局面終于被打破。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抓住機遇,促成中美兩國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從而結束了長達30年之久的不正常狀態。又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緊追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實現大國崛起,再次令世界震驚。近六十多年共同走過的歷史證明,不打不相識,中美兩國和則皆大歡喜,斗則兩敗俱傷。
把一場戰爭寫進詩歌,或者為一場戰爭寫一首詩,前人早這么干過。我和梁粱先生曾主編反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外國現代戰爭詩集《我和死亡有一個約會》,便收集了22個諾貝爾獎獲獎詩人寫的戰爭詩。有趣的是,在世界文學界享有盛名的大作家博爾赫斯,對詩歌創作情有獨鐘,而在他最得意的詩作中,戰爭詩是最精彩的部分。美國著名詩人沃倫,還曾為美軍在二戰結束時向日本廣島投擲原子彈,發起核攻擊,寫過一首長詩,那首詩的名字叫《新黎明》。
坦率地說,我寫這首《上甘嶺》并非心血來潮,而是希望以詩歌為觸須和媒介,對那場驚心動魄的戰爭,對中美兩軍惟一的一次戰場大對決,還有對當下的國際政治、未來的戰爭格局,做出自己的判斷,發出自己的聲音。你可以說我天真,幼稚,不自量力。但我認為,一個詩人的心臟理應更大一些,理應有一定的縱深感;跳起來,也應該更強勁。面對當下這個瞬息萬變的大時代,如果我們的詩歌甘于沉默,或者只滿足于抒發內心的孤傲和小情調,可能難逃蒼白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