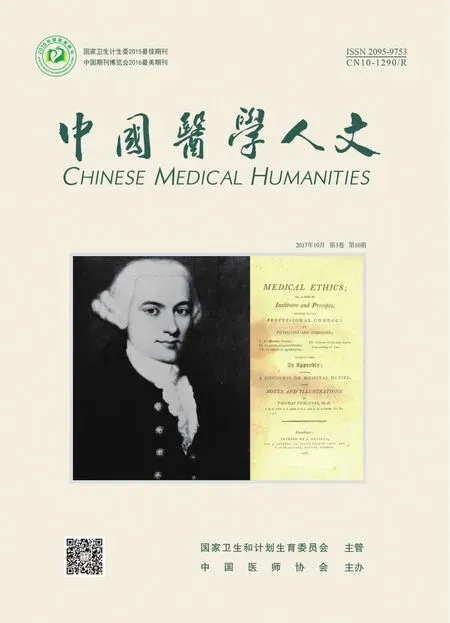行醫(yī)的 “七年之癢”
文/周劍平
行醫(yī)的 “七年之癢”
文/周劍平
從醫(yī)至今,恰好七個年頭,回頭望去,這七年的時間不僅沒有讓自己對醫(yī)學失去興趣,卻始終覺得自己收獲頗多,與醫(yī)學事業(yè)的這段感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倒是愈發(fā)情比金堅起來。這個世上的幸福有很多種,相信能將夢想轉化到現實便是這各種幸福中的一種,用醫(yī)學的話語來說,幸福就是可以讓自己不斷感受到腎上腺素持續(xù)飆升的狀態(tài)。每天來到醫(yī)院,總感覺自己有著無窮的動力、無盡的熱情乃至無邊的精力。從實習到住院,再到主治,無論哪個階段,始終如同海綿吸水般汲取著各種養(yǎng)分,激發(fā)著各種潛能。在這個從大學走入社會的第一個“七年”中,曾經志同道合的同學們選擇了其他各種職業(yè),亦或是留在了不同的醫(yī)院,在各自的專業(yè)領域實施各自抱負和理想。而我,作為其中的一員,依然是一名普通的臨床醫(yī)生,在醫(yī)學環(huán)境中,感受著這七年來醫(yī)療理念的不斷更新,在學習和適應的過程中不斷歷練自己,提高自我乃至反省自我。為醫(yī)之路,也因為這些,變得愈發(fā)精彩了起來。
無處安放的健康之惑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這自古以來都是一條無法逃避的自然規(guī)律,但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科學技術也正向著充滿著無限可能的未來發(fā)展,類似“精準醫(yī)學”的醫(yī)學目標正逐步成為大家爭相效仿的醫(yī)學模式。且不論這樣的模式是否適合不同國情和現狀的國家,就我所接觸到的醫(yī)療環(huán)境而言,“精準醫(yī)學”絕對尚處于“畫餅充饑”的階段。伴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fā)達,我們迎來了空氣、水和土地污染等各種環(huán)境污染,我們遭遇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巨大人口遷徙,各種社會-心理-疾病的新模式和新問題層出不窮,社會不斷進步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可見一斑。
回歸身體狀態(tài)發(fā)展的規(guī)律,我們可以看到,“健康態(tài)度”隨著年齡的改變正發(fā)生著顯著的變化。處于青春年少的我們,最大快樂便是缺乏洞察力,所以,可以無憂無慮、甚至肆無忌憚地活著,生活在我們看起來無所不能。但當我們逐步邁入暮年,內心對世間萬物的確定會被未知取代,自信被惶恐取代,青年時的不可一世蕩然無存,曾經看重的東西也變得不再重要。我們意識到心智上的不成熟則是最糟糕的自負,大多數人所覬覦的卻恰恰是我們所無法擁有的。健康的身體便是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事情之一。而現代醫(yī)學的理念熱衷于將所有一些“不幸”用一個“病”字來代替——哮喘、糖尿病、高血壓、性功能減退、肥胖、吸煙、焦慮和抑郁等等。而進入中年階段的我們就仿佛等待著自己被貼上各種相同或者不同的疾病標簽,有的人甚至會被同時貼上數個標簽,從而正式走進長期打針、吃藥的無底深淵中,各種求醫(yī)問藥和疾病討論也成為茶余飯后必不可少的話題之一。
輕重難辨的求醫(yī)問藥之惑
當前的醫(yī)生正忙于應對兩種人群,一種是對于自身的健康十分擔心的人群;一種是危重癥患者。前者的人群基數巨大,醫(yī)生們把較多的精力放在前者,就像我們的門診一樣,平均每天每個醫(yī)生的看診量可以達到百人之多。整體上,作為醫(yī)生,我們有這樣的一種印象,許多常見的疾病隨著時間的推移,患病人群大大增加。究其原因,類似像糖尿病、腎臟疾病乃至精神疾病等等的種類和界限進一步擴大,需要接受醫(yī)療隨訪和干預的人群也隨之不斷壯大。疾病界限的細微改變可能導致被貼上疾病標簽的人群比例顯著增加。根據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公布的醫(yī)療數據提示,以甲狀腺癌為例,2012年發(fā)病率是1975年3倍之多,但死亡率卻維持不變。我們不禁思考,對于疾病發(fā)病進行性增長這一現象可能的解釋則是檢測增加和診斷工具的改變。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我們疾病診斷的能力提高了,但疾病治療的本事似乎還未有顯著長進。從而在臨床工作中,我們有時會發(fā)現這樣的現象,同樣的疾病,一些剛被診斷和治療的患者可能會受益,但另一些人則將經受不必要的治療和產生副作用。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瑞金醫(yī)院
善始善終對待生命之惑
古人有云:剛柔交替、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關乎天文,已查時變;關乎人文,以查實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以禮儀儀法教化和規(guī)范社會的人及其行為,化性成俗,并改造和成就社會的一種道德精神。而醫(yī)學人文則著眼于人類的健康和疾病,以關注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為重要內涵。醫(yī)學人文體現在對人及其生命的關愛,包括對人的生存、健康及心理精神的關懷。
從一個受精卵形成開始,代表著一個新生命的開始;從聽到新生兒第一聲啼哭開始,代表著那個新生命的誕生;善事容易,皆大歡喜。但面對疾病的折磨,特別是疾病終末階段的病人,無論對于患者還是家人,善終卻總是艱難。
以晚期肺癌為例,從發(fā)病開始,到確診,進而病情惡化,乃至最終死亡,大多會經歷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相對較長的疾病末期,癌癥患者的軀體和精神遭受死亡威脅和折磨的痛苦則更多。善終,在我們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中,是很難做到的。現在醫(yī)院搶救程序及大多數患者的家屬關注的焦點則是拒絕死亡,或者說盡可能地推遲死亡。程序化醫(yī)療讓走到生命盡頭的人,不能安詳離去,反而要忍受可能有損患者意愿和尊嚴的醫(yī)療,例如,毒性或創(chuàng)傷性抗癌治療,搶救措施和生命支持系統(tǒng)治療。這些絕非真正意義上的善終。后者指的是,幫助走到生命盡頭的人,安詳地離開這個世界,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需要盡可能減輕患者的心身痛苦,更為真實地尊重患者的意愿。事實上,這一點也是臨床困難之處所在,因為善終階段,醫(yī)生往往遵循的是與患者家人討論關于死亡的問題,往往忽視了患者本人對于治療的意愿表達,最終讓患者失去了自我選擇的權利。

沙漠綠洲 攝影/廖蜀宜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yī)院
醫(yī)者無法自醫(yī)之惑
每年年際交接的時候,醫(yī)院安排職工體檢過后,總會傳來這樣或者那樣的壞消息,每每在這個時候,醫(yī)護人員的健康狀態(tài)才會被有所提及,也些許提高了大家對自身健康的關注,但時日不多,又在忙碌的醫(yī)務工作中把健康幾乎忘記得一干二凈。
對于社會而言,醫(yī)生是一種十分重要的醫(yī)療資源,而且在培養(yǎng)醫(yī)生的過程中,社會也投入了相當可觀的綜合資源。且不知道中國社會培養(yǎng)一個住院醫(yī)生需要投入多少資金,就醫(yī)生自身而言,從入學至就業(yè),至少要花費超過5萬余元。事實上,這樣的經濟投資換來的社會回報率是相當可觀的,一名訓練有素的醫(yī)生在疾病預防、急救、疑難診治方面可以發(fā)揮巨大作用。作為社會大眾,我們已經習慣了將健康和醫(yī)生聯系在一起,我們總是說,白衣天使,是大眾健康的保護神,卻很少有人會關注醫(yī)生自身的健康。
事實上,成為醫(yī)生,與其他高風險職業(yè)一樣,注定要承擔較高的健康威脅。除了直接暴露在具有潛在傷害和風險的環(huán)境中,醫(yī)生也要面對壓力所致的心理疾病。通常情況下,醫(yī)生自己接受的醫(yī)療服務往往是不足的,而且醫(yī)生對于自身的照顧遠遠少于他們對于病患的關心。一旦醫(yī)生受到了本可避免的疾病傷害,就會造成公共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不必要的浪費、病人的損失、給同行帶來的壓力,甚至會中斷當事醫(yī)生職業(yè)發(fā)展道路。
首先,醫(yī)生也是普通人,和所有的病人一樣,也會遭受各種急慢性疾病的威脅,隨時可能完成身份轉換,由醫(yī)生變?yōu)椴∪耍疫@種疾病風險相對較高,因為他們的工作本身便使他們始終處在多種疾病的包圍之中,且不說病人有可能將疾病傳給醫(yī)生,例如,2003年的SARS,2009年H1N1禽流感,2011年的甲型流感等等,醫(yī)生由于自身的工作強度大,節(jié)奏快,休息時間少,很少因為自身健康原因接受醫(yī)療服務,缺乏對自身健康的重視。其次,醫(yī)療工作本身對于醫(yī)生的職業(yè)素養(yǎng)要求高,需要具有精湛的醫(yī)療技術,同時要具備較強的責任心以及強大的心理素質,因為臨床情況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治療反饋差,病人情況惡化,病人各種痛苦以及面對各種疑難雜癥。再者,醫(yī)生也是社會人,同樣要面對各種社會壓力,工作壓力大,收入低,缺乏家庭支持等等因素長期存在。
行醫(yī)七年,內心的不惑還有很多很多,在與患者的交流中,我們依然會面臨著各種無法解決的問題,例如,食物對于健康的“威脅論”似乎總是會引起大眾階段性恐慌,不免造成“這個不能吃,那個不健康”的種種印象,從好的方面來看,這是大家有意關注健康的表現,但這也在無形之中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煩惱。有些時候,“專家”的建議還是需要適當忽略的,畢竟危險需要判斷和認真對待,但生活總是還要繼續(xù)。但對著病人說“不”可真心沒有那么容易,病人通常十分信任醫(yī)生,他們總是會說:醫(yī)生,你覺得這件事應該怎么處理?當然,醫(yī)生的決策往往受制于各種指南,即使有時內心認為并非必須,參照指南的要求給予患者治療,因為這樣做,不僅不會受到指責,而且就治療本身而言,相對更為簡單。因此,醫(yī)生們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激進醫(yī)療、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的隊伍中。
醫(yī)者,我們需要做的則是給予患者足夠的尊重,提供患者或是親屬理性的建議,恰當的時機,適當的治療。醫(yī)學需要人文與藝術,這也是現代化醫(yī)學對于醫(yī)生所提出的要求。誠然,我們需要知道什么時候病人更適合治療,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也應該知道什么時候病人不需要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