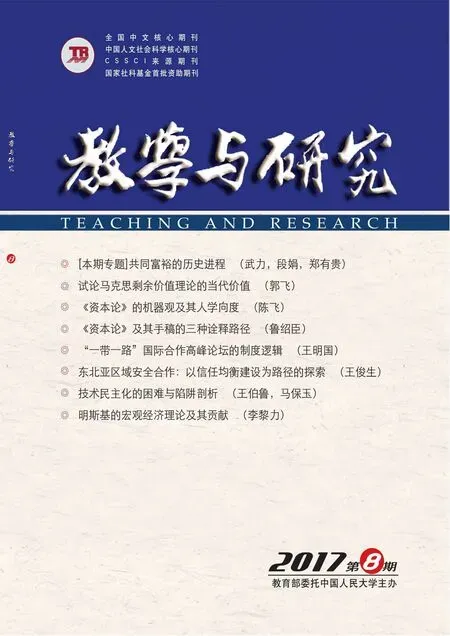東北亞區域安全合作:以信任均衡建設為路徑的探索
東北亞區域安全合作:以信任均衡建設為路徑的探索
王俊生
東北亞;安全合作;當務之急;恐懼均衡;信任均衡
導致東北亞各國安全領域最為恐懼的局面在過去幾年有增無減,由此帶來了相對穩定與相對和平,但這種穩定與和平不僅脆弱,且風險極高。如何實現東北亞安全由恐懼均衡走向信任均衡成為該地區安全合作重要方向。國家間信任關系生成需要五個因素:利益、制度、偏好、信用、秩序。東北亞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該地區權力轉移、各國安全觀對立、歷史因素、“面子政治”等四方面。本文指出,為建立信任均衡,在軍事安全層面,要推動有關國家間建立溝通機制、推動國防白皮書發布以及重大軍事行動前信息發布。在非軍事層面,要擴大該地區利益合作關系,加強多邊對話制度建設,塑造各國更多趨同偏好,調和不同安全觀差異,樹立國家信用,通過“中美雙領導體制”營造穩定秩序等。
東北亞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已有諸多論述。“東北亞已成為最充滿活力、戰略價值最大的地區”。[1](P888)“東北亞地區對中國有著特別重要的地緣、經濟、政治與安全意義”。[2](P198)近年來東北亞區域安全合作呈現兩個令人擔憂的悖論:其一,“在東北亞存在著經濟領域合作和相互依存深化而安全領域合作程度低下的所謂‘亞洲悖論’現象”。[3]其二,“東北亞國家所持有的安全理念大致經歷了從絕對安全到相對安全,從個體安全到共同安全,從均勢聯盟安全到多邊合作安全的轉變”。[4]筆者也曾詳細分析過該地區各國(包括朝鮮)對開展多邊安全合作的積極態度。[5]這種背景下該地區安全緊張態勢卻有增無減,典型反映在朝鮮半島問題上。
如何務實推動東北亞地區安全合作已成為亟待回答的問題*究竟哪些國家屬于東北亞地區仍存爭議,本文主張從地緣政治角度,東北亞地區應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日本、朝鮮、韓國、蒙古七個國家。。本文認為,當前東北亞安全特點是恐懼均衡,這是該地區安全合作的最大障礙。導致恐懼均衡的根源在于各國間缺乏合作所需的基本互信。“東北亞地區各國安全互信缺失,已嚴重阻礙了該地區開展多邊安全合作”。[6](P2)為實現東北亞安全合作,推動該地區安全局勢從恐懼均衡走向基于信任的均衡至關重要。
一、信任關系與東北亞安全合作
當前東北亞安全局勢走向與中華民族復興均處于關鍵時刻。這包括中美權力轉移體現出結構性變化特點、朝鮮半島局勢演變處于臨界點、中日權力轉移發生結構性變化與日本安全戰略正走向新方向、俄羅斯戰略走向也體現出新特點。中國自身崛起也是影響東北亞安全局勢走向的最大因素之一。“目前是近代以來中國掌控周邊大局能力最強的時期”,[2](P251)對于事關中國周邊外交與中國崛起核心次區域的東北亞地區,中國究竟應如何緩解其高居不下的緊張局勢,如何運籌帷幄未來和平與合作秩序,是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的重要課題。需指出的是,“對中國來說,構建秩序的目標不是為了獲取霸權,不是要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勢力范圍,而是要塑造一個穩定、和平、合作、發展的地緣區域環境”。[2](P251)
國際關系理論對于如何實現地區和平與合作已有許多探討,這包括民主和平論、經濟互相依賴論、霸權穩定論以及國際機制論等。對于民主和平論,“美、日一直自詡為‘民主、自由、法制、尊重人權’的國家,聲稱東北亞及世界各地不穩定的根源是一些國家存在不民主、不自由等”。[7]事實上,不僅東北亞許多國家對于民主的界定與西方截然不同,亞洲的價值觀與西方的價值觀必然有不同之處,而且即使在西方學界對該理論也存在很多批評。[8](P769)
對于經濟相互依賴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列強間經濟關系深深交織在一起,但這并沒能阻止戰爭爆發。如上所述,東北亞地區安全緊張態勢有增無減的大背景就是該地區經濟相互依賴加深,“1986年到1992年,亞洲內部的經濟出口從31%增長到43%,到2010年這個數字占到亞洲貿易總量的56%”。[9](P54、66)前世界貿易組織首席經濟師羅柏年2013年11月表示,“亞洲內部的貿易額增長一向高于全球平均值”。[10]亞洲內部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最典型的反映在中日韓三國之間。
由國際公共產品理論發展起來的霸權穩定論不僅在理論上遇到諸多挑戰,而且也不符合東北亞現實。“霸權存在只有當其控制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的時候,顯然東北亞現在已不再存在霸權。美國單邊主義在世界上已經遇到許多挑戰,挑戰最大的地區當屬東北亞”。[8](P784)
對東北亞安全合作研究最多的當屬多邊安全機制,背后邏輯即是國際機制和平論。但總體上看,“東北亞地區還不具備建立多邊安全機制的條件。冷戰后的所有嘗試都失敗了”。[6](P6)筆者也曾指出,“目前在東北亞建立多邊安全機制不僅不現實,而且在朝核問題懸而未決背景下,倉促建立起來的機制也未必就能帶來該地區和平與合作”。[5]
況且在新時期推進該地區多邊安全機制時,歷史上日本帝國主義靠殖民侵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傷疤仍會不時重現于人們記憶,尤其涉及領導權之爭時。這進一步給該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建設帶來障礙,也凸顯出構建信任合作關系的緊迫性與重要性。“東北亞大國關系利益協調的機制化欠缺,地區安全合作制度的缺失,最根本原因還是缺乏彼此信任度,大國間政治互信及相互尊重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11]“要建立各國所接受的安全合作機制和模式,必須首先在東北亞地區建立促進各國相互信任的機制。因此,如何克服信任缺失和安全困境,培育各國對彼此的信任才是東北亞地區安全合作的關鍵”。[12]
二、信任、安全合作以及兩種均衡
考慮到本文研究旨在促進東北亞安全合作,以及在實現路徑上應由恐懼均衡向信任均衡轉換的假設,因此,這里需要在理論上厘清信任與安全合作的關系,尤其要區分兩種均衡的本質區別,以及國家間信任關系的生成邏輯。
1.信任與安全合作。
關于信任與安全合作,學界普遍認為,“信任對促進安全合作非常重要”。[1](P903)“信任關系更容易促使國家采取國際合作和多邊主義的方式解決問題,盡管信任別國面臨背叛風險”。[13](P252)一旦缺乏信任,“會增大安全合作成本、降低合作效率”。[1](P889、894)“對欺騙的防御心理,使得國家間即使擁有共同利益與合作動機也不一定會自然達成合作”。[14](P268-286)有學者在對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論、復合相互依存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等進行深入研究后發現,“在世界體系中,相互依賴的基礎是合作,而實現合作的關鍵因素是信任”。[15]本文主張信任有利于國家間安全合作,“信任是國際合作與沖突的微觀基礎,因此,國家間建設戰略互信和政治信任是一項重要政策目標”。[16]
2. 信任均衡與恐懼均衡。
國家間合作的動因比較復雜,要區分合作是否由信任產生并非易事,特別是相對于威懾帶來的恐懼而言。本質上講,“前者是基于相信另外一個國家會履行信任的責任(比如邊界信任措施)而進行的合作,后者如基于核大國間的互相毀滅而建立的合作”。[17](P381)本文由“信任”和“恐懼”引申出兩個新概念:“信任均衡”與“恐懼均衡”。
均衡本是博弈論的核心概念,指博弈達到的一種穩定狀態,沒有一方愿意單獨改變戰略。這里借用該概念修飾“信任”意指由各方的信任關系所達成一種穩定狀態,從而實現該地區國家間和平與合作。同樣,這里借用“博弈論”中“均衡”概念修飾“恐懼”,意指由各方間的互相“恐懼”達至一個貌似相對穩定的狀態,巨大不確定性又使得各方不愿意輕易改變使彼此“恐懼”的戰略或政策。其結果是要么恐懼延續,要么為恐懼“加碼”。由此可見,“信任均衡”和“恐懼均衡”都會形成表面的穩定狀態,這就需要解釋兩個問題:其一,兩者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其二,何以表明兩種均衡實現了轉換?
兩者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出發點是“合作共贏”,后者出發點是“零和博弈”;前者主張對話方式解決分歧,后者往往通過施壓恐嚇方式解決問題;前者不僅高層領導互訪頻繁,而且民眾等互動交流也常常熱絡,體現為友好相處,后者則往往局限于高層領導間互動,普通民眾之間關系冷淡,兩國關系常體現為劍拔弩張;由于敵意認知與多層面交流缺乏帶來誤判上升,后者的穩定局面明顯脆弱且風險性極高,一方常常為了減小自身恐懼而不斷加大對另一方施加“恐懼”的砝碼,其結果極易形成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導致雙邊與地區局勢長期處于緊張狀態在國際關系中屢見不鮮,冷戰期間的美蘇關系即是如此,當前最典型例子體現在朝韓關系上*由于下文還將討論朝韓關系,這里僅簡單以此為例來指出恐懼均衡帶來國家間關系的特點。。朝鮮聲稱其核試驗以及頻繁進行的導彈試射是面對美韓軍事威脅的自保行為,也是迫使美國改變對朝政策的策略使然*筆者2016年6月27日—7月1日在訪問朝鮮期間與朝方人員交流時再次得出該觀點。也即朝鮮多次進行核試驗和頻繁進行導彈試射不僅有國防建設的目的,同時仍有想以此為籌碼“迫使”美國和朝鮮進行談判的考慮。。美韓則以此為由不僅頻繁舉行針對朝鮮的聯合軍演,而且越來越向實戰方向發展,斬首部隊也加入其中。其結果不僅半島局勢緊張狀態高居不下,而且極為危險。
相反,信任均衡則容易形成國家間關系的良性循環。以歐盟國家間關系為例,拋棄了歷史上敵友涇渭分明、沖突與戰爭頻發的狀態,二戰后該地區國家間關系長期呈現出和平穩定態勢,很重要一點就是彼此信任關系,歐洲為此還特意建立起一系列信任措施*比如:[瑞典]英·基佐:《建立信任措施:歐洲經驗及其對亞洲的啟示》,《現代國際關系》,2005年第12期;曹云霞,沈丁立:《試析歐洲的信任建立措施及其對亞太地區的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1期。。盡管很難想象東北亞地區國家間關系有朝一日能趕上歐盟國家間關系,但由于恐懼均衡與信任均衡所帶來國家間關系的巨大差別,尤其考慮到當前東北亞地區國家間關系呈現出典型的恐懼均衡加劇特點*針對東北亞地區國家間關系為恐懼均衡的特點,下文將詳細論證。,推動該地區國家間關系走向信任均衡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恐懼均衡”(balance of fear)并非“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后者主要應用在核威懾領域,強調彼此對對方有構成重大傷害的潛能,從而維持平衡與安全。本文的“恐懼”主要指各方對彼此政策中的“敵意”部分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不確定性的擔心。“均衡”則如上所述,指各方對彼此的擔心同時上升達至一個貌似穩定的狀態,這種均衡難以測量,只是反映國家間關系的大致狀態。

圖1 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實現路徑
作為中國周邊次區域中安全困境最為嚴重的東北亞地區,[18]其和平與合作的實現路徑應如圖1所示那樣,首先從建立安全互信開始,逐步過渡到積極區域安全合作、機制建設,最終實現該地區積極的和平與穩定。由此可見,東北亞地區當務之急要構建安全信任關系,這就需要從理論上首先回答信任關系生成的邏輯。
3.國家間信任關系生成的邏輯。
對于“信任”的探討最成熟學科當屬社會學。根據“社會學中信任的建立需要理由、偏好與規則三個要素”,[19](P33)國家間信任的生成也應包含三個要素:利益、制度、偏好。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信任建設中利益關系和情感偏好的重要性。信任別國很難解釋為什么不懷疑他國會出于自利(self-interest)目的,這首先出于利益考慮。“你信任我,是因為這種信任符合你的利益。反過來,我信任你,也是因為這種信任關系符合我的利益”。[20](P421-456)在此基礎上,有學者詳細分析了“偏好”對建立信任關系的重要性,“國家間信任與兩種因素相關:一是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與評估;二是個人或國家的心理感受,包括領導人或國家的個性特質、心理認知以及情感偏向等”。[21]這里的“外部環境”更多指利益考慮,“國家心理感受”正是情感上的“偏好”。
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進而把規則從利益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單獨要素。“國家間信任分三個層面,基于國際交往經驗的信任,互惠是核心;基于國際行為體具有社會、文化共性的信任,它根源于國際社會履行的義務和合作規則(比如是否會改變現狀等);基于制度的信任,這種信任是建立在非單個國家的規則、國際規范和制度的基礎上”。[22]“只有各國際行為體基于信任的理由、偏好和規則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建立國際信任”。[22]
此外,有學者還指出國際秩序對于建立信任關系的重要性。[22]所謂“國際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礎上形成的國際行為規則和相應保障機制,通常包括國際規則、國際協議、國際慣例和國際組織等,這里國際秩序(或地區秩序)在一定意義上等同于國際(或地區)和平與穩定。由此可見,信任是形成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反過來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或地區)環境有利于國家間形成信任關系。反之,如果一個地區處于失序環境中,混亂與猜忌充斥其中,必然不利于國家間信任關系形成。綜上,國家間信任關系的生成邏輯可用圖2表示。

圖2 信任關系的生產邏輯
三、當前東北亞安全合作被恐懼均衡主導
近年來東北亞整體區域安全合作往往試圖通過大國協調與集體行動推動,圍繞朝核問題的解決模式即是如此。但大國協調常常因中美猜忌而不能取得較好效果,集體行動也是如此,各方往往互相指責,最終合作效率低下,甚至無果而終。背后主要根源在于各國間互相恐懼,美國擔心中國、中國擔心美國、中國擔心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美國擔心中俄戰略合作、朝鮮擔心韓國、韓國擔心朝鮮等等。這種擔心與恐懼在過去幾年呈現有增無減之勢。
對中國而言,主要擔心三方面:其一,美日與美韓同盟超出雙邊范疇而對中國的威脅。“雙邊聯盟體系可以實現體系內國家排他性的基本安全,但卻導致了地區大國間的信任赤字,尤其是中美兩國間戰略互疑已成為地區安全問題最為深層的原因”。[4]其二,該地區核擴散;其三,該地區安全緊張局勢。這三方面近些年均有增無減。美日與美韓同盟得到加強,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也得到一定推動。2014年12月,韓美日三方簽訂《情報共享協議(TISA)》,規定韓日兩國將以美國為媒介間接共享相關情報*共享方式為,韓國和日本宙斯盾艦探測的情報通過美軍陸地轉播臺交換。。2016年6月28日,韓國、美國、日本海軍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以應對朝鮮導彈為名舉行了導彈防御(MD)聯合軍演。2016年7月8日,韓美軍方同時宣布將在韓國領土部署美國“薩德”系統,這不僅遠遠超出半島防御范圍,而且在日本將部署該系統背景下,韓國此舉會再次實質性推動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朝鮮新任領導人上臺后已進行了三次核試驗,大大重挫了該地區國家為防止核擴散而做出的努力。日本與韓國國內主張獨立“擁核”的聲音再次增大。[8](P779)這顯然是中國不愿意看到的,特別是在該地區安全緊張局勢有增無減背景下。
美國在東北亞地區最為擔心兩方面:其一,中國崛起,逐漸排除其在該地區影響力。米爾斯海默明確指出,“美國在21世紀初可能遇到的最潛在危險便是中國將成為東北亞霸權”,“隨著中國力量增長,中美兩國注定會成為對手”。[25](序言)亨廷頓從文化和權力兩個角度推演出類似結論,“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中國作為東亞占主導地位地區大國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將對美國核心利益構成威脅”。[26](P254、259)其二,該地區核擴散,以及朝鮮核武器具備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美國這兩方面的擔心近些年也有增無減。中美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兩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地位與影響力正由此前美國占主導地位向中美二元均衡的格局發展。[27]朝鮮不僅進行了多次核試驗,而且還多次進行中遠程導彈試射,其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強。
日本在東北亞地區的最大擔心有以下幾點:其一,中國崛起,日本在該地區主導地位徹底喪失。自甲午戰爭打敗中國與日俄戰爭打敗俄羅斯以來,日本曾長期獲得東北亞主導地位,二戰結束后,日本仍試圖竭力維持這種地位。這其中部分原因或許是“因為日本擔心中國在強大后進行報復,因而時刻處于本體性安全危機的困擾中”。[21]其二,中韓接近;作為該地區最大經濟體和第四大經濟體的中韓兩國,在對日歷史問題上立場較為相近,中韓接近將極大削弱日本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其三,朝鮮的核武與導彈發展。這些顯然也都有所增大。不僅中國實力迅速增強,日本在東北亞地區前所未有地極可能淪為二流大國,而且過去幾年中韓在針對日本歷史翻案等問題上立場確實更為接近,兩國在對日施壓上也展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實質性合作。
韓國在該地區的最大擔心在于:其一,朝鮮的安全威脅;其二,在半島問題上以犧牲韓國主導權為代價的中美協調。這兩方面在韓國看來也有所增強。朝鮮在連續進行核試驗和導彈發射情況下,來自朝鮮的實質性安全威脅的確進一步加大了。對于后者,韓國《中央日報》2016年3月18日刊發的一篇文章比較有代表性。文章指出,美國和中國圍繞朝鮮半島問題表現出的動向頗為可疑,令人不禁懷疑雙方是否已經就短期內消除目前嚴重緊張局勢以及從長期出發并行討論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和平協定問題達成某種共識。文章稱,“就在韓國外交當局大肆吹噓韓美、韓中關系一切順利的時候,韓國可能已經淪為兩大強國象棋盤上的卒子”。[28]對于韓國的所謂“擔心”,筆者雖然不能茍同,但近些年半島問題的解決進程仍以中美協調為基調的事實沒有改變,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后,中美圍繞如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實質性合作進一步加強。
進入21世紀,綜合材料藝術因其拓展性,在美術學院教學體系中有了重要地位。在此之前,美術學院藝術專業的重點是“國、油、版、雕”四個傳統門類,隨著新材料、新技術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發揮作用,綜合材料藝術語言在中國語境中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到現在,中國藝術家使用綜合材料和多媒介(或非傳統媒介)創作的藝術作品,開始在西方嶄露頭角,徐冰、陳箴、黃永砯、隋建國、宋冬、毛同強等都可視為是這方面的重要代表。
對朝鮮而言,最大擔心體現在三方面:其一,來自美國的威脅。“考慮到朝鮮對美國盟友的威脅、對美國視為威脅的國家與團體的武力支持,對朝鮮進行政權更替是唯一能讓美國滿足的最終結果”,[29](P32)因此長期以來,美國都被朝鮮視為政權安全的最大威脅;其二,冷戰結束后隨著與韓國實力差距進一步擴大,朝鮮顯然擔心來自韓國的顛覆與吸收統一;其三,考慮到與中國關系的重要性,有理由相信朝鮮確實擔心中朝關系惡化對其國家安全帶來影響。朝鮮這些擔心近年來均有增無減。美韓針對朝鮮聯合軍演的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向實戰方向發展,斬首行動也包含其中。過去幾年韓國政府到處推宣統一,不免給人“統一即將來臨的印象”。同時,源于朝鮮核問題上的戰略分歧,中朝關系仍然看不到改善勢頭。
俄羅斯最大擔心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其影響力被排除出東北亞局勢之外,“(俄羅斯)積極參與該地區的各種安全對話與合作,其目的在于保證其不被排斥在地區安全事務之外”。[30]其二,來自美國的壓力,“奧巴馬政府對俄羅斯區域戰略的核心任務在于隔離俄羅斯復興與中國崛起”,[31]也就是說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目標不僅要遲緩中國崛起,同樣也要遲緩俄羅斯復興。其三,隨著東北亞某些國家的復興,俄羅斯擔心歷史上其搶占的領土被這些國家提出主權索求,或者實質性占領。“從俄羅斯領導人的角度看,這種現實和潛在的領土要求,對其東部安全構成威脅”。[30]
如上所述,近年來在東北亞安全事務上中美協調加強,俄羅斯地緣影響力確有下降之勢。來自美國的壓力也有增無減。在俄羅斯西部面臨北約已擴展到其“門口”和反導系統已部署背景下,美國在其東部強化與日本的同盟以及欲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無疑給俄羅斯安全帶來更大壓力。對于俄羅斯所謂擔心東北亞相關國家提出領土索求,盡管不太可能發生,但由于俄羅斯“遠東地區土地面積為620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從蘇聯解體時的805萬人減少至約640萬人,每平方公里僅1人”,[30]俄羅斯確實擔心鄰國居民向該地區擴張。隨著韓國“歐亞倡議”與中國“一帶一路”實施,客觀上會加強與該地區的經濟合作與人員往來,這也有可能加劇俄羅斯擔心。
比較而言,蒙古安全環境有所改善。在與俄羅斯維護傳統友好關系基礎上,與中國、美國的關系均有所提升。當然,蒙古在東北亞安全局勢上的影響力較為有限。
綜上可見,東北亞各國雖然在經貿、政治等領域的雙邊或者區域關系主要特點并非完全是恐懼文化,但導致東北亞各國安全領域最為擔心的局面在過去幾年里均有增無減,在軍事安全領域呈現出典型的恐懼加劇特點,這些互為恐懼的局面同時上升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狀態。與此同時,東北亞地區大致維持了相對和平,本文將其稱之為恐懼均衡導致的和平,這種和平顯然呈現出冷和平與消極安全狀態的特點。
已經有很多研究指出東北亞冷和平與消極安全狀態根源在于核威懾、冷戰格局等因素*比如:《朝美罵戰背后難以破局的東北亞冷和平》,《環球網》,2015年2月6日。參見: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2/5613037.html.。本文之所以指出恐懼均衡也是導致東北亞冷和平與消極安全的一個重要根源在于兩方面:其一,恐懼均衡是導致東北亞地區冷戰格局、歷史問題、領土問題等難以解決的重要原因,固化了該地區的冷和平與消極安全狀態;其二,近些年該地區國家間的互相恐懼不減反增,使得該地區安全局勢表面上呈現一定穩定性,實質不僅脆弱而且風險極高。2017年以來朝鮮半島戰爭局勢曾經一觸即發再次體現出這一點。如何弱化和消除這種恐懼就成為東北亞安全合作上亟待解決的問題。
各國恐懼加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信任缺乏加劇。以同期中美與中日不斷攀升的信任赤字為例,郝雨凡教授指出,“中美存在的問題很多,但最核心的是在動機和意圖上彼此懷疑”。[32](P263)中美兩國攀升的“信任赤字”必然使得兩國發生錯誤“鏡像認知”和相互“妖魔化”的可能性增加,直接后果就導致“雙方傾向于從最壞前景出發制定針對對方的政策”*王鴻剛:《中美“合作伙伴關系”新定位評析》,《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2期;朱立群:《信任與國家間的合作問題——兼論當前的中美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對于中日關系而言,“領導層的交惡和國民感情的遇冷,造成了中日間‘負能量’的螺旋式上升。軟實力在中日外交中幾乎蕩然無存”。[33]
導致上述各國對外恐懼有增無減和信任赤字不斷攀升的背后根源可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東北亞地區權力轉移仍在繼續,并有加速之勢,地區安全層面結構極不穩定。“權力轉移的過程加大了安全困境,同時增加了新的安全擔憂”。[6]有學者甚至認為“美國、日本對中國崛起意圖的猜忌主要源于這個”。[1]況且,權力轉移本身就會引起各國間信任變化。這正如朱鋒教授指出的那樣,在東北亞地區“中國持續崛起所帶來的權力變更首先產生的不是政策和戰略變化,而是微妙復雜的心態、知覺和認知上的變化”。[34]
第二,各國安全觀對立,特別是美國雙邊同盟與地區其他國家之間的對立,“美日安全同盟是最具破壞性的力量”。[4]“美日對朝鮮的敵視政策是朝鮮半島動蕩的主要根源之一,美日對中國崛起的警惕、防范與制約使東北亞難以建立起各國間真正的信任以及和平、穩定的戰略關系,美日對俄羅斯的冷淡也使俄與美日的關系難以真正成為建設性的合作關系”。[7]冷戰結束后東西方陣營之間的國家缺乏信任,“尤其反映在中國、俄羅斯對于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走向的不確定性的擔憂”。[1]
這歸根結底源于各國所秉持的安全觀不同,“中俄秉持新安全觀,美朝傾向于傳統的安全觀念,日韓則搖擺于兩者之間”。[4]在不同安全觀支配下,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再平衡”網絡將中國視為平衡對象。以日本為中心的“價值觀同盟”網絡體系將中國排除在外。朝鮮偏執的安全觀使得其幾乎與整個地區為敵。“這些對沖網絡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他國安全的一種排斥、提防或否定。因而,網絡內部國家間獲得的本體性安全越多,不同網絡之間的本體性安全危機反而愈嚴重,相互提防的各種網絡使各國間難以形成一種不設防的心理狀態,進而引起了東亞國家間信任的嚴重流失”。[21]
第三,歷史因素及歷史遺留問題。這包括中日歷史問題與領土問題,韓日慰安婦問題與領土問題,日俄領土問題,朝韓對峙與統一問題等等。事實上,安全觀對立的部分原因也與歷史傳統有關。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美國缺乏多邊主義傳統。“二戰之前,美國與蘇聯、英國、德國在歐洲的分權就已開始,因此二戰后很容易建立一個分權的習慣。而在東北亞則正好與此相反,二戰前就是美國主導,二戰后美國習慣通過雙邊同盟進行主導。因此,美國缺乏在這個地區推行多邊主義和分權的習慣”。[6](P12)事實表明,二戰結束后的歷史遺留問題以及冷戰的遺留問題致使該地區信任建設十分困難。
第四,東北亞國家的“面子政治”使得信任建設更是雪上加霜。[1](P893)由于東北亞各國政治文化以及近代歷史滄桑巨變,各國在對外關系中均特別看重“面子”問題。特別是存在歷史問題與現實利益沖突背景下,各國間妥協難度加大,有時候“面子”比實際利益的“里子”顯得更為重要,這就增大了相互猜忌,給信任建設進一步帶來了難處。
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作為一個常量的前提條件下,東北亞國家間信任降低與恐懼加劇的直接后果就是該地區安全困境加劇,“而要克服安全困境,只有從加強合作開始,而這又要以加強東北亞國家間的信任為基礎”。[12]這再次表明,實現東北亞地區從恐懼均衡向信任均衡轉變已經是該地區加強安全合作的當務之急。
四、東北亞安全合作如何實現信任均衡?
通過上述信任生成的邏輯可見,東北亞地區在信任建設上已經采取了以下措施。在軍事安全層面:其一,相關國家間已建立了直接或間接的溝通渠道,避免因誤解而產生沖突。以中國為例,中俄兩軍于1993年11月建立了國防部長定期會晤機制,1997年11月建立了總參謀部戰略穩定磋商機制。2004年10月普京總統訪華時,兩國元首又同意建立國家安全磋商機制;2015年12月31日,中韓國防部直通電話正式開通。截至2016年1月,中韓國防政策工作會議已召開15次。
中朝近年來盡管因核問題上存在戰略分歧,兩軍交流受到影響,但兩國1961年簽訂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仍然生效。2016年7月11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55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互發賀電。“條約”明確規定“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于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這表明在緊要時刻,兩國軍事溝通有機制保障。
相比之下,中日軍事溝通滯后。1998年和2000年分別實現國防部長互訪和兩軍總參謀長互訪以及1997年至2002年副部級年度防務磋商舉行3次后,迄今處于停滯狀態。
其二,有關國家對本國的國防戰略進行公布。自2009年1月發布《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以來,中國每年都會發布國防白皮書。日本政府自1970年以來每年都發布國防白皮書。韓國自冷戰后每兩年發布一次國防白皮書。
其三,在軍事行動或演習前發布信息,讓其他相關國家及時了解情況。1994年9月3日,中俄兩國元首簽署了《關于不將本國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的聯合聲明》,同年中俄兩國還簽訂了《中俄兩國預防危險軍事行動活動協定》。
在非軍事層面,該地區有關國家間的以下做法有利于信任建設。(1)自貿協定簽訂,共同利益擴大。2015年6月1日,中韓簽訂自貿協定。(2)建立了相關多邊機制,有利于各方更多溝通與交流。該地區已經形成中日韓三邊對話機制和六方會談機制。目前中日韓三邊首腦對話已經重啟。六方會談“是新形勢下中國第一次從區域構建的角度試圖創建東北亞新區域關系與合作框架”。[2](P246)盡管六方會談復談暫時面臨重重困難,但除朝鮮外的各方均普遍認為其是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乃至構建未來東北亞多邊機制的重要平臺。(3)中日2005年組成歷史研究聯合小組,有利于共同偏好形成。(4)相關方在地區重大問題上的協調秩序,這不僅反映在此前多輪六方會談談判上,也反映在近些年中美俄等國針對朝核問題的協調上。
與此同時,與信任程度較高的地區——比如歐洲與東南亞——相比,東北亞地區信任建設還任重而道遠。即使上述已采取的相關措施也只是零星個案,別說普遍推廣,就是離占主導的方向也差距甚遠。下一步在軍事安全層面還需從以下方面入手:建立中日軍事溝通機制;推動俄羅斯、朝鮮、蒙古發布國防白皮書;加大各國在軍事行動或演習前信息發布,這方面可邀請其他國家軍事觀察員參加軍事演習以及加強軍事人員的互訪與交流。各國還應逐步建立可供對方驗證軍事行動及信息的途徑,并推動限制某些特別軍事行動的規模、時間或強度。
在非軍事領域,則應從以下方面入手:第一,繼續擴大該地區利益合作關系。從表面上看,東北亞國家在政治與安全問題上利益兼容性越來越小,利益沖突越來越突出,但實際上這些國家的共同利益呈現擴大趨勢。由于各國間互相依賴越來越大,一個不穩定的地區安全局勢往往帶來各方利益“共輸”局面,尤其在經貿領域。應該說冷戰結束以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背景下,各國幾乎都把發展經濟提到了與維護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盡管經濟依賴并不必然帶來信任與合作,但經貿共同利益確實是促進安全合作和信任建設的“壓艙石”,“經濟合作是東北亞合作中最為迅速、成效最為顯著的領域,在東北亞共同利益中最能產生外溢效應”。[35]這方面要繼續做大各國共同經濟利益的蛋糕,下一步尤其要注重中日自貿區和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并逐步以中日韓自貿區帶動東北亞自貿區建設。同時,加大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有關國家經濟合作倡議的對接。
第二,應盡快建立對話制度化的機制,讓對話常態化與習慣化。“缺少多邊合作傳統,在(東北亞)地區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尚未建立對話機制,使得(該地區)各國難以發現戰略利益匯合點,戰略互信當然無從談起”。[35]為此,一方面應盡快推動六方會談重啟,另一方面要推動符合該地區多邊安全合作趨勢的新對話機制,尤其是朝鮮半島由停戰協定向和平機制轉變的“停和機制”。“對于朝核問題,不能要求朝鮮必須首先‘棄核’然后才解決其他問題,而要和其他問題同步解決”。[6](P13)“停和機制”主要為了緩解和消除該地區冷戰格局,其結果也有利于該地區相關國家間的信任建立。
第三,要培養各國具備更多趨同的偏好,調和不同安全觀差異。如果東北亞相關國家能建立歷史聯合研究小組,比如中日韓,那么研究成果就有望縮小各方在歷史問題上的差距,也更容易被三國民眾所接受。這方面還可以推動由退休高官和著名學者組成“名人論壇”,共同討論東北亞各國間現實的安全利益分歧并為該地區未來安全秩序進行研究,同時引導輿論。為調和不同安全觀差異,要合理安排美國同盟體系與該地區共同安全利益的關系。美國同盟體系是其東北亞安全戰略基石,任何觸動美國同盟體系的安排都不大可能取得成功。這種背景下,務實安排的一種可能是通過“美韓+X”“美日+X”等三邊機制方式,實現美國雙邊同盟與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對接。
第四,鑒于一國是否信任他國主要取決于該國對他國信用的判斷,各國對彼此的政策應呈現連續性。在這方面,美國與韓國的對朝政策連續性尤其需要加強。同時,已經達成的協議要嚴格遵守,否則會極大影響其信用,信任也無從建立。
第五,可嘗試在該地區形成“中美雙領導體制”*“雙領導”與“共治”不一樣。有關在東北亞地區構建“中美雙領導體制”的必要性、可行性、具體路徑等可詳細參見王俊生:《中美雙領導體制與東北亞安全:結構失衡與秩序重建》,《國際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為互信關系建立構建穩定秩序。“歷史證明,每個國際體系都是被當時處于領導地位的大國制定規則和管理”。[36](P150)“共同利益的匯聚及其制度化、所涉各國共擔責任、大國承擔主要責任已成為國際合作的基本戰略路徑”。[37]習近平主席2016年4月在美國出席會議時也指出,“大國協作是處理重大爭端的有效渠道”。[38]這其中“最主要的還是中國和美國的作用”。[39]
[1] Gregory j. Moore. Constructing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Historical Northeast Asian Dyadic Cultures and the Potential for Greater Regional Coopera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Issue 82, 2013.
[2] 張蘊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研究、參與和思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3] 韓獻棟.美國“亞太再平衡”背景下韓國的外交安全戰略[J].現代國際關系,2015,(3).
[4] 韓愛勇.東北亞大國協調與復合型安全合作架構的建立[J].當代亞太,2013,(6).
[5] 王俊生.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進展與出路[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12).
[6] Camilla T. N. S?rensen.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in Northeast Asia: A Lost Game or the only Way to Stability[J].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2013.
[7] 楚樹龍.東北亞戰略形勢與中國[J].現代國際關系,2012,(1).
[8] Brendan Howe. Three Futures: Global Geopoly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J].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5,39(4).
[9] T. J. Pempel.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111(5).
[10] 專家表示亞洲區域內部貿易成為全球貿易重要“發動機”[EB/OL]. 新華網,2013-11-07.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07/c_118053333.htm.
[11] 楊魯慧.東北亞大國關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區安全共同治理[J].東北亞論壇,2012,(4).
[12] 李淑云,劉振江.信任: 東北亞區域安全合作的關鍵因素[J].外交評論,2007,(1).
[13] Brian C. 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 [英]迭戈·甘姆貝塔.我們能信任信任嗎?[A].鄭也夫主編.信任:合作關系的建立與破壞[C].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
[15] 李淑云.信任機制:構建東北亞區域安全的保障[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2).
[16] 尹繼武.國際信任的起源:一項類型學的比較分析[J].教學與研究,2016,(3).
[17] Aaron M. Hoffman.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8, No.3, 2002.
[18] 王俊生.“安全困境”的形成與緩解——以冷戰后東北亞安全為例[J].教學與研究,2014,(11).
[19] Luhmann N. Trust and Power[M]. New York: John Wiley,1979.
[20] Abbott, Kenneth W.,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0, 54(3).
[21] 包廣將.東亞國家間信任生成與流失的邏輯:本體性安全的視角[J].當代亞太,2015,(1).
[22] 楊揚.社會學視角下的國際關系信任理論——兼析東亞區域合作中的互信[J].太平洋學報,2012,(7).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C].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24] 王日華.中國傳統的國家間信任思想及其啟示[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3).
[25]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M].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6]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27] 王俊生.中美雙領導體制與東北亞安全:結構失衡與秩序重建[J].國際政治研究,2013,(4).
[28] [韓]金英喜.警惕美國與中國串通[N].中央日報(韓),2016-03-18. 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49362&category=002005.
[29] Gregg Andrew Brazinsky.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security Cooperation Innortheast Asia[J]. Asian Perspective, Vol. 32, No. 2, 2008.
[30] 季志業.俄羅斯的東北亞政策[J].東北亞論壇,2013,(1).
[31] 呂平.奧巴馬政府對俄羅斯、蒙古戰略透視[J].西伯利亞研究,2013,(6).
[32] 郝雨凡,張燕冬.無形的手[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33] 孫晶.走出不信任與對抗情緒的詭局——從國民感情和軟硬實力轉化看中日關系[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5).
[34] 朱鋒.東亞安全局勢: 新形勢、新特點與新趨勢[J].現代國際關系,2010,(12).
[35] 門洪華,甄文東.共同利益與東北亞合作[J].外交評論,2013,(3).
[36] Byeong Cheol Mun.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Hegemony, Concert of Powers, and Collective Security[J]. Asian Perspective, 2012,(36).
[37] 門洪華.中國東亞戰略的展開[J].當代亞太,2009,(1).
[38] 習近平.大國協作是處理重大爭端有效渠道[EB/OL].人民網(河北頻道),2016-04-03. http://he.people.com.cn/n2/2016/0403/c192235-28070637.html.
[39] [韓]李正男.韓國對中國在東北亞安全領域角色的認知[J].現代國際關系, 2011,(11).
[責任編輯劉蔚然]
RegionalSecurityCooperationinNortheastAsia——AnExplorationBasedontheConstructionofBalancedTrust
Wang Junsheng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cooperation; top priority; balance of terror; balance of trust
The most alarming situation in the security areas in Northeast Asia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ow to realize the security situation from the fear equilibrium to the trust equilibrium in Northeast As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The growth of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needs five factors: interest, system, preference, credit and order.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lack of trust in Northeast Asia lies in four aspects: the power transfer in the region, the opposi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security views, the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face polit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build a balanced trust, countries shoul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among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at the military security level. On the non-military level, countries should expand their interests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reconcile differences in security views, establish national credit, and create a stable order through the system of dual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王俊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 1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