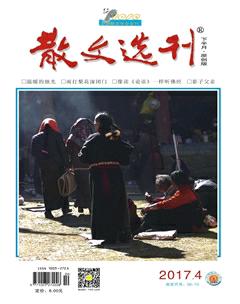港口韭菜
楊寶軍
“頭茬韭,花香藕,新娶的媳婦,黃瓜紐。”這是流傳于蘇北水鄉的民謠《世上四大鮮》。
韭菜作為“四鮮中的頭鮮”,令居家百吃不厭。談到泰州港口(現姜堰區華港鎮)韭菜, 泰州、姜堰、揚中乃至在整個江蘇久負盛名。
韭菜原名“救菜”。西漢末年王莽篡位,為斬草除根,還想殺掉16歲的劉秀。劉秀逃出京城后起兵討伐王莽,不料兵敗,逃生途中饑渴難耐,求救于一個農戶。主人夏老漢見劉秀非同一般,就把他扶進舍中,因為缺飯少菜,夏老漢便炒了無名野菜讓劉秀充饑。饑不擇食的劉秀連吃三碗野菜方才緩過神來,他問老漢什么菜如此好吃,夏老漢說是無名,劉秀說,今天,它救了我的命,就叫它“救菜”吧。后來,劉秀稱帝,封夏老漢為“百戶”,賞地千畝,專門種植“救菜”,直送皇宮。由于以“救”作名不太合適,便專門為 “救菜”之“救”造了一個字“韮”,后人又把“韮”簡化為“韭”,從此“韭菜”便名傳于世。
劉秀吃的韭菜是否就是港口韭菜無從考證。只是港口垎田, 四面環水,岸高坡陡,土地肥沃,排灌方便,適宜種植韭菜,這是不爭的事實。
港口農民種韭菜相沿已久。品種有雪韭、黃韭、獨根紅等, 鼎盛時期,種植面積近萬畝。
港口韭菜除考究種子、育苗、移栽等環節外,最主要的是水肥管理。炎熱夏天,每天起碼澆兩次水,太陽剛出時澆一次,日落時分再澆一次。垎岸岸高坡陡,澆水要用一丈多長的竹柄水瓢,一瓢一瓢地從河溝里舀上岸。瓢舀不到的地方,還要用戽子澆。再說施肥,除了罱泥扒渣之外,還要絞水草捂在韭菜行子里。從早春到秋末,每割一茬都要布一遍水草。越冬前堊家腳灰、人畜糞不談,還要罱泥罱渣覆蓋韭菜。水草和泥渣中含有螺螄、蜆子、小魚、小蝦等多種有機肥,既當肥料,又能保持土壤濕潤。港口韭菜從不用化肥,鮮嫩爽口,回味無窮。
來年立春過后, 菜農們早已將小鍬磨得亮晃晃的, 不等天亮,開始“夜雨剪春韭”,根部有泥,葉面帶露珠的韭菜, 晶瑩透亮,分外鮮嫩,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港口韭菜。菜農割韭菜很講究技巧。刀子不挨著根割,一定要稍離根部遠一點,這樣韭菜才不會受傷。
捆扎韭菜要有相當本領。頭茬韭菜較短,要想捆圓捆大十分困難,除非六十歲開外的老農。等到二、三、四茬……老農捆起來的韭菜,每捆足有四五十斤。姜堰、泰州、揚中等地的菜販子只要看到像足月孕婦的大捆子韭菜,就知道這是地地道道的港口韭菜,很快被搶購一空。
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港口一帶的農民每家自留地種厘把二厘韭菜,就能開銷全家老小的油米醬醋鹽……韭菜可謂是港口人的救命菜。但是,那時的韭菜也被戴上了“資本主義尾巴”的帽子。生產隊隊長一旦發現哪戶韭菜多了,就會連根鏟除。
農戶賣韭菜更是件心煩的事。記得小時候的一個春天,媽媽一夜沒睡,將自留地里割的兩籃子韭菜挑到十八里外的泰州賣錢。她告訴我們, 賣得的錢除一部分用來量米外, 其余的同我們姐弟每人買塊布料做新褂子過夏,我們高興得一夜沒合眼,巴望媽媽早點回來。不料, 直到第二天挨黑,媽媽才從泰州兩手空空回到了家。籃子、扁擔和帶去的桿秤全不見了。媽媽沮喪著臉告訴我們,夜里碰上“紅袖章”了。原來, 她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步行好不容易到了泰州楊橋口, 剛想歇會兒,就被戴紅袖章的執勤人員盯梢了, 媽媽左拐右拐,以為甩掉了“尾巴”, 躲在一深巷的角落里正準備與買菜的居民交易, 哪知道被盯梢的“紅袖章”逮個正著。結果媽媽視為“投資倒把分子”,韭菜沒收不談,還被關了一天, 直到她做了深刻的口頭檢討后才放了回來。每當我吃到韭菜就會想起母親當年那辛酸的往事。
生活條件好了,韭菜的食譜也多了。如單炒的話,須旺火爆炒立刻出鍋。這樣鮮香撲鼻,色澤誘人。油少或火小,炒的時間過長,味道會大打折扣。如果不單炒, 還有多種搭配炒法。韭菜炒螺螄、韭菜炒蜆子、韭菜炒雞蛋、韭菜炒蝦仁都是極好的吃法,韭菜炒百葉居家最常見,喝酒吃飯再好沒得。
韭菜辛辣,既促進食欲又有良好的藥用價值。《本草綱目》中說:“韭籽補肝及命門,治小便頻數,遺尿。”民間稱之為“洗腸草”。“男不離韭,女不離藕”。現代人還稱韭菜為蔬菜中的“偉哥”。
如今,港口人不再為韭菜提籃吆喝了。清晨, 長在田里綠滴滴、翹嫩嫩的韭菜,眨眼工夫,就會隨南來北往的菜商行銷各大超市,走進千家萬戶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