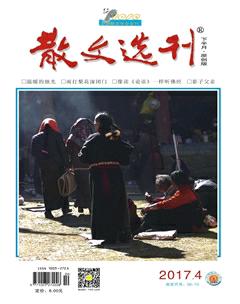二百五
黃劍英
這事應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我父親的職業是地質隊的探礦員,一年里有半年的時間在外地工作,半年的時間在家休探親假。
閑居在家的父親最喜歡釣魚了,一提及釣魚就眉飛色舞。可母親卻極力反對,想方設法打擊父親釣魚的熱情,但不管用。而為了得到釣魚機會的父親態度也很溫順:一是主動包攬家務,買菜、做飯甚至洗衣服;二是賠著笑臉討好母親,每次釣魚前都要硬塞二三十元錢給母親,求她笑納。每次母親都會假裝一臉不情愿地、半推半就地、罵罵咧咧地收下了。
我家對門的表舅在農機廠當廠長,閑暇之時也愛釣魚,可兩人的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表舅去釣魚,早餐不是蛋炒飯就是大肉包子,父親卻是開水泡飯。表舅釣魚一回家,舅媽就熱毛巾熱茶地伺候著,兩個女兒一個接過魚簍后替他捶肩捏背,一個動手剖魚做飯。而父親卻要餓著肚子收拾魚準備全家的晚餐。當父親的臉上露出委屈的神情并咕噥出幾聲抱怨時,母親就一聲怒喝:“不稀罕!我叫你去釣的?”嚇得父親脖子一縮,立馬不敢吱聲。唉,為了釣魚,父親什么都能忍。
一天,父親又去釣魚了。午飯后母親要我幫她找一件放在床頂的東西。我站在凳子上面,雙手在蓋著塑料布的床頂摸索,不一會兒就摸到了一塊滑滑的涼涼的東西。拿下來一看,是一張通紅的黨員證,這無疑是父親的。打開黨員證,里面夾著三張鈔票。兩張百元大鈔,一張五十元面值的(在那時二百五十元錢可不是小數目)。我想,父親可能認為將它們藏在黨員證里,它們便可以安全地投入黨組織的懷抱里了。可現在,它們竟然無處遁形地暴露在站在床邊的母親眼皮底下。似乎輕而易舉地逮住了它們的母親,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立刻大嚷起來:“這個老狗骨,竟敢‘扎筒(私藏錢)!”母親的大嗓門像吹集結號一樣,一下子就召來了好些個鄰居,他們都圍攏過來看:“沒想到河清姑丈也私立小金庫了。”“美仙姑,你又不讓河清姑丈釣魚。他早上要吃碗粉,買個包子,交罰款,所以,只有私下藏錢了。”
人們更多的不是替父親鳴冤,而是佩服他將錢藏得隱蔽。我卻不以為然,父親是探礦員,他深諳地底下的寶貝多種多樣、奇巧無比的隱藏方法,他隨便借鑒一二,藏好這區區幾張紙又有什么難的呢?
母親可能是因為得到這筆意外之財的緣故,興奮得滿臉通紅,嗓門愈加大起來:“大家都別聲張,我倒要看看這老狗骨到時怎樣現好。”于是乎,從那時起院子里的每個人心中都深藏著這件有關“二百五”的事情,就連“四合院”內的空氣也憋住不漏出半點風聲。
自那以后母親就像是個掌握了父親“犯罪”確鑿證據的刑警,在等著狐貍露出尾巴來一樣,行事之時便有了一種凜然氣勢,仿佛她就是正義的化身。而我的心情是頗為復雜的,既有對不住父親,成為母親幫兇的忐忑,又有對父親藏錢行為的驚訝。要知道,父親是個出名的好男人,這一點連母親都不否認。她常說:“幸虧我嫁了你父親這樣的人,換作別人,早就被打死了。”有時我甚至覺得母親的跋扈就是父親慣出來的。而父親在釣魚這事上對母親的忍讓態度,我想肯定也和他私藏“二百五”這事有關。從那天起,母親不再叫父親的名字,也不再喚他“老狗骨”了,而是直呼“二百五”!其實,父親有一個大氣而詩意的名字——黃河清。對于這個名字,我曾著實佩服過給父親起名的爺爺好一陣子。黃—河—清,要令黃河清澈見底,這是何等的膽識與氣魄。
“你這個二百五!”“你怎么搞的?二百五!”“二百五,今天別去釣魚!”每當此時,院子上空就飄蕩著母親得意揚揚的愉悅和鄰居們沒事偷著樂的竊笑。我很納悶為何父親在這一聲聲含沙射影中,竟然一點都不曾嗅出有關“二百五”的異樣氣息。
日子就在母親一句句“二百五”的呵斥聲、我的不安和鄰居們急切盼望好戲開場的等待中,一天天地過去了。
十幾天后,父親終于知道了那個他原本以為只有天知地知和他知的秘密早已不是秘密時,便哭喪著臉要母親將“二百五”還給他。
“想得美!你這個二百五!”母親斷然拒絕道。
可憐的父親低頭喪氣,像個犯了錯的孩子,一聲不吭……
奇怪的是,自那以后,再也沒有聽過母親喊他“二百五”了,而父親依舊熱情高漲地釣他的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