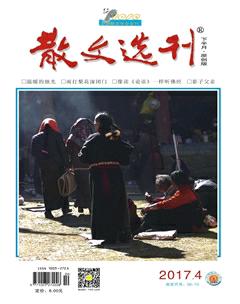影子父親
一心
“你能不能少說點兒!”父親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矮著身子小聲地說,語氣中夾雜著哀求和埋怨。
室內一片沉默,窗外高大的樟樹上,茂密的葉子在秋風中嘩嘩作響。
我看了看一臉沮喪的大哥,又看向臥室,母親躺在床上,眼神茫然而絕望。
我的心猛地一沉,后悔自己口無遮攔,說話不注意。
母親中風后,曾轉到康復醫院治療。不小心,腿在輪椅上被碰傷了,又恰好是癱瘓的那條腿。糖尿病人的傷口不好恢復,幾家醫院都不肯接受治療。我們只好在家竭盡全力地護理,但傷口依然越來越大。
我看著傷口無奈地說:“醫生說,再嚴重只能截肢了。”我忘記了,大家的心理本來就纖弱如絲,我還要狠狠地去拉扯一下,而最痛的一定是父親。
父親坐在沙發上,愣了一會兒,忽地醒過神兒來,彈起來沖到母親身邊,抓著她的手,小聲地安撫著,聲音有些沙啞,聽起來虛弱而蒼涼。近些年,受多種疾病的折磨,母親的身體越來越差,脾氣也越來越大。父親處處讓她,有時被激怒了,也跟她爭吵幾句。可吵歸吵,母親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他怕母親摔倒。
“你媽看上去很好強,其實脆弱得很,她離不開我。”父親曾一臉自豪地跟我說。他以為自己很強大,此生給母親撐起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帝國大廈,沒有什么能夠攻克它。可這場重病,卻讓他的大廈轟然倒塌。住院沒幾天,母親的病情逐漸加重,不能動,不能說,不能吃。下危重通知書的那天,我們剛好都不在,是父親簽的字。他仿佛一下子老了,挺拔的軍人身姿佝僂下來,一緊張就掏出速效救心丸服用。只要我們被醫生叫出去,一回來,他的目光就警惕地在我們的臉上掃來掃去,察覺有什么異樣,無論誰勸,他都不肯回家休息,只能睡在醫院的一張窄椅上,也睡不踏實,一聽到母親咳嗽他就爬起來。我們兄妹幾人輪流值夜,逼著他休息,可發現他睡著時常常做噩夢,蜷著身子,一頭汗,手攥得緊緊的,掰都掰不開。他的神經繃得太緊了,怎么行?
我們決定請一個護工,晚上照顧母親。可父親不同意,一向溫和的他血紅著眼,向我們吼道:“你媽不會說話了,要翻身、咳痰,護工晚上睡著了,才不會管呢!不行!”
我也急了,提高嗓門說:“這病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日子長著呢!你已經是快八十歲的人了,不注意休息,你如果累垮了,我們照顧誰?”
在我們的堅持下,父親做了讓步,晚上回到弟弟家睡覺,但白天執意要去醫院,我們也只好隨他了。因為放心不下母親,他總是想辦法拖延時間,很晚離開醫院,晚上又常常失眠,睡不了幾個小時,第二天早上又總是趕第一輛公交車到醫院。
在醫院,他一刻也不肯休息,給母親按摩,獨自跟她說話,用針管一點點給她喂流食,推著輪椅在走廊里轉來轉去……
過度的勞累,讓父親差點倒下。一天半夜,父親房間燈亮了。弟弟也醒了,起來一看,他捂著胸口,面色蒼白,才知道他胸悶心慌。弟弟嚇壞了,知道父親心臟不太好,況且兩年前放過支架,趕緊送他到醫院。經過一系列檢查,確定是太緊張、太勞累造成的胃病。
父親如釋重負,去醫院的路上步履如飛。母親正憂心忡忡地等著他,一聽說沒大事兒,用唯一能動的右手一遍遍摩挲著父親的臉,激動得淚流不止。父親也有種失而復得的驚喜,一手緊緊抓住母親的左手,一手為她擦拭淚水。我們也潮濕了眼,走出病房,讓他們享受這份不幸中的幸福。
傍晚我“押解”父親走出醫院,一再叮囑他要保重身體。他滿口答應道:“你放心吧,我以前想得很明白,不怕死,可現在怕了,我死了你媽怎么辦?為了她,我也要好好活下去!”
父親獨自走向車站,形單影只。暮日余暉,將他花白的頭發染成了枯黃,清瘦的身影被拉得很長,很長。
從康復醫院回來,母親睡眠不好,我們建議輪流陪護,可父親一定要睡在母親身邊,他說:“你媽想說什么我都懂,在康復醫院的時候,晚上受了很多委屈,以后我絕不離開她。”
可他照顧母親,晚上常常睡不好,幾天后便憔悴不堪了。我們硬逼著他睡到二樓,半夜兩點左右,我聽到臥室外有腳步聲,走出房間,看到父親正躡手躡腳地準備下樓。被逮了個正著,他忙不迭地向我解釋道:“樓上太冷啦,樓下暖和,再說你媽需要我。”
看著他慌張地下樓,步履蹣跚。我的眼淚不可遏制地流了下來,父親這一年老了許多,他一生輾轉,從四川到東北,到青藏高原,再到江南,幾十年的跋涉,他已經像一輛疲憊的老馬車,卻依舊載著愛和責任徐徐前行。他不再看看了幾十年的《新聞聯播》,不再練練了幾十年的氣功,不再讀讀了幾十年的《易經》。他只關注母親,關注她每一個眼神和手勢的內容——
“你媽今天心情不錯,吃飯有進步……”
“你媽這陣兒好像瘦了……”
“你媽今天在寫字板上寫著不想活了,說是拖累我們了,唉……”
“你媽……”
母親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她的喜怒哀樂就是他的喜怒哀樂。父親全然沒有了自我,他活成了母親的影子。
我曾經固執地認為人生是蒼涼的,赤身而來,赤身而去。可我的老父親卻讓我感受到了別樣的溫暖:在你孤獨的生命航程里,有這樣一個擺渡者,始終撐著一船風雨一船愛,陪伴你渡過歲月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