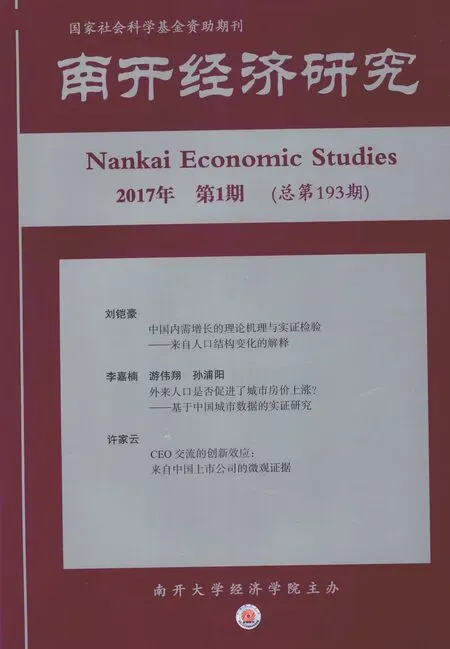CEO交流的創新效應: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微觀證據
許家云
CEO交流的創新效應: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微觀證據
許家云*
CEO在不同企業之間的交流是否能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目前國內還尚未有文獻對此進行定量研究。本文將 1999—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數據進行匹配,構造了CEO交流的微觀樣本,并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統地評估CEO交流對流入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即CEO交流效應)。結果表明:CEO交流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效應,并且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具有持續性,而且是逐年遞增的;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因CEO是否具有海外留學及工作經歷、性別差異、年齡差異以及企業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顯著的異質性;我們還特別關注了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發現 CEO交流在總體上顯著地延長了流入企業技術創新的持續期,但不同類型 CEO的流入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存在差異。本文從微觀層面證實了中國上市公司CEO交流確實能產生顯著的創新效應,這意味著鼓勵和促進 CEO在企業之間的交流對于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生產效率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CEO交流;上市公司;技術創新;傾向得分匹配
一、引 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過度依賴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弊端日益凸顯,加快提高中國自主創新能力迫在眉睫。《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鼓勵企業設立研發機構,使企業真正成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應用的主導力量。那么,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又有哪些呢?已有的實證研究大多是從企業、行業或者市場層面的整體特點來剖析企業創新行為和決策,而往往忽視了作為企業管理者的 CEO在其中的作用①本文將具有“董事長、常務總經理、總經理、CEO或首席執行官”頭銜的企業管理者界定為CEO。。作為對企業整體運營管理過程全面負責的企業高層管理者,CEO對企業的研發決策具有核心作用,甚至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一些公司的“一把手”對公司的決策起決定性作用(Adams等,2005;Bennedsen等,2008;李小榮和劉行,2012)。那么,CEO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具體影響是怎樣的?迄今為止還沒有相關文獻對此問題進行全面細致的分析。鑒于CEO等企業高層管理者是企業決策的重要主體,因而系統地識別、評估CEO對企業創新行為及其績效的影響,可以為如何更好地促進微觀企業的創新能力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礎之上的。首先是基于公司治理結構的視角考察上市公司高管變更對企業績效的影響。Coughlan和 Schmidt(1985)最早考察了美國公司股票收益與高管變更的關系,認為高管變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股票收益。Warner等(1988)研究發現,股票收益與公司高管變更顯著負相關。Morck等(1989)發現,當公司業績低于整個行業的平均業績時,公司高管更有可能變更。Kaplan(1994)發現,日本大公司和美國大公司在公司業績與高管變更之間的關系方面并沒有顯著差別,但日本虧損公司更易發生高管變更。此外,日本公司的股票收益與高管變更的關系敏感度低于美國公司。此后,Kaplan和 Minton(1994)、Kang和 Shivdasani(1995)對日本的研究以及Kaplan(1994)對德國的研究均表明高管變更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相關性。其次是關于CEO與企業研發績效方面的相關研究。Chen等(2006)運用中國的臺灣省1996年至2001年IT產業公司數據來考察高管持股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高管持股能夠緩解委托代理問題并促進企業研發投資。之后,許多學者進一步將CEO的異質性引入企業績效的研究框架。朱紅軍(2002)的分析認為高管的年齡、大股東的變更和以前年度的經營業績是影響高管變更和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最后是企業間人才交流(流動)的技術溢出效應方面的研究。跨國公司的員工在職業初期以較低的薪酬來進行知識和技術的積累,在人力資本比較成熟之后,帶走在跨國公司學習到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流動到本土企業換取較高的薪酬。或者,組建新公司,將先前學習到的先進經驗運用于新企業,生產與原公司相似的產品與服務,進而會產生示范效應,直接引致技術在行業間的橫向擴散。國內外有很多實證研究表明該溢出途徑是切實存在的。Almeida和Kogut(1995)認為,在半導體行業研發方面,產生技術溢出效應的最重要因素是關鍵技術人員的流動。李平和許家云(2011)分析了海歸型人才流動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發現海歸由外資企業外流創辦新企業會引致技術的擴散和普及。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 CEO及其變更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而關于CEO與企業創新行為的研究相對較少,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其對企業研發投資的影響方面。基于此,我們關注的問題是CEO交流是否有助于促進企業創新①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CEO交流”是指CEO從一個企業到另一企業任職,它包含了兩個維度:一是企業的CEO發生了變動,即CEO變更;二是CEO的變動是從一個企業跳槽到另一個企業。?如果是,作用力度如何?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如何?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文獻的基礎之上,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有著本質的不同。本文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豐富和深化了已有的研究:(1)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首次將前沿性的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引入 CEO交流與企業創新問題的研究框架,從而在該問題的研究中可以較好地解決傳統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選擇性偏差和混合性偏差問題;(2)本文不僅考察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即期影響,而且也考察其對企業創新的動態影響,此外我們還對CEO進行分類,在此基礎上比較研究不同類型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差異性以及其在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異質性效應;(3)本文還首次采用生存分析模型考察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進而可以拓寬有關CEO交流與企業創新關系的研究視角。
本文其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第三部分為模型設定和方法說明;第四部分是實證估計結果及分析;第五部分進一步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最后是本文的結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間人才交流(流動)是技術溢出的重要方式。由于知識和技術具有人才依附性的特性,當某公司培訓的技術工人和管理人才外流時,會產生知識和技術在流入企業的擴散效應。作為企業經營決策的關鍵人物,CEO在企業之間的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可能更大。CEO在企業之間的交流一方面會增進其對流入企業績效的責任感和對任職期間成就的追求,另一方面,新任 CEO對待變革的態度往往更積極,對開發新產品和開拓新市場更加充滿熱情,從而富有精力的新任 CEO更傾向于做出推動企業創新的決策行為(Hambrick和 Mason,1984;Andersson和 Wictor,2003)。McDougall等(1994)、Madsen和 Servais(1997)以及 Westhead等(2001)的分析認為,從其他企業交流來任職的 CEO往往積累了相關領域的工作經驗,具有社交網絡廣闊和管理經驗豐富的優勢,從而其對促進企業研發創新意義非凡。
具體來看,CEO交流可能會通過以下兩個渠道影響企業的創新行為。
首先,投資拉動效應。第一,CEO將其在先前公司學習到的先進管理經驗應用到現任企業,在研發投資時可以趨利避害,避免創新活動的盲目性(Bloom等,2013);第二,“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CEO出于自身職業發展的需要往往會通過加大企業研發投資和創新產出的方式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在同行中的競爭力,上述舉措會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第三,新任 CEO往往充滿組織創新的興趣和對工作的新鮮感,更注重吸納各種先進管理方式來經營企業,傾向于做出更多的戰略變換,強調產品和市場創新(Hambrick和 Fukutomi,1991)。Grimm和 Smith(1991)對美國的研究發現,隨著任期的延長,CEO會做出較少的戰略變換,CEO逐步喪失組織創新的興趣和對工作的新鮮感,同時,會漸漸減少與企業的外部環境的聯系,缺乏改變戰略和投資的動力(Thomas等,1991;Miller,1991;Barker和Muller,2002;劉運國和劉雯,2007)。按照上述邏輯,CEO交流有利于企業的產品創新和市場創新。
其次,薪酬激勵效應。基于利潤最大化的視角,流入企業往往會通過為新任 CEO提供較好薪資待遇來激勵其工作的積極性,而對管理層的薪酬激勵可以抑制企業的委托-代理矛盾和 CEO的風險規避性,鼓勵他們從事包括研發創新在內的更多的風險性項目(Coles等,2006),從而促進企業創新。李春濤和宋敏(2010)基于CEO薪酬激勵的視角,利用世界銀行在中國 18個城市 1483家制造業企業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對CEO的薪酬激勵能促進企業進行創新;Lin等(2011)基于同樣數據的研究認為對經理人的激勵機制可以促進國內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CEO交流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并且,其可能會通過投資拉動效應和薪酬激勵效應促進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
三、模型、方法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也就是考察CEO交流與企業創新之間是否存在實際因果關系。在經驗研究中,選擇性偏差和混合性偏差往往會給估計結果帶來很大困擾。由 Heckman等(1997)提出的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可以較為有效地解決上述問題。PSM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構建一個與有 CEO交流企業(即處理組)在CEO交流發生之前的主要特征盡可能相似的無CEO交流企業組(即對照組),然后將處理組中企業與對照組中企業進行匹配,使得匹配后的兩個樣本組的配對企業之間僅在是否有CEO交流方面有所不同,而其他方面相同或十分相似,接下來就可以用匹配后的對照組來最大程度地近似替代處理組的“反事實”,最后再比較在處理組企業CEO交流后兩組企業之間創新行為的差異,由此來確定CEO交流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因果關系。

下面用logit方法估計如下模型:

由式(2)估計得到的概率預測值?p即為傾向得分,PSM 方法則是根據處理組企業與對照組企業之間 ?p值的相近程度對二者進行配對。需要指出的是,采用以上方法對樣本進行配對的有效性取決于以下兩個潛在假設條件:其一是條件獨立性條件(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其表示在控制了影響 CEO交流的共同因素之后,企業創新量的變化與 CEO交流決策是相互獨立的;其二是重疊條件(overlap condition),這一條件可以確保每一個處理組企業都可以通過傾向得分匹配找到與其相配對的對照組企業。
這里我們用馬氏距離配對法為處理組(即有 CEO交流企業)尋找傾向得分最為接近的對照組(即無CEO交流企業),將其作為前者的匹配對象。馬氏距離配對主要是基于這樣一種思想:對于任意的處理組企業i和對照組企業i1,i與i1間的距離di1為:

其中,Ui和Ui1分別為 i和i1的匹配變量值,C為對照組中各匹配變量值的協方差矩陣。因此,對于處理組觀測值 i,只有那些具有最小的di1值的一個或幾個對照組觀測值被選擇作為新的對照組。這里我們將配對比例確定為 1∶6。在進行馬氏距離配對之后,我們提取處理組企業i和對照組企業i1組成新的樣本,即匹配后的樣本。
以上就標準的傾向得分匹配的因果效應估計方法進行了說明,也即基于水平值(levels)的傾向得分匹配。不過也有學者建議在傾向得分匹配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采用倍差法(DID)來估計因果效應。這主要是因為倍差法可以處理諸如有CEO交流企業與無 CEO交流企業不可觀測到的共同趨勢問題,通過差分能夠消除非時變的不可觀測因素對配對估計結果的干擾,進而可能有助于提高估計效率。根據 Heckman等(1997)的方法,基于倍差法的傾向得分匹配的估計模型可表示為:

(二)數據說明
本文研究所用的樣本數據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中之一是國家統計局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本文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99—2007年,它統計調查的對象涵蓋了全部國有工業企業以及“規模以上”(主營業務收入大于 500萬元)非國有企業。該數據庫是目前國內可獲得的最為龐大的微觀企業數據庫。“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包括了來自企業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現金流量表中的八十多個變量并提供了關于企業身份、所有制、出口額、就業人數以及固定資產總額等方面的詳細信息。
盡管“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是目前國內可獲得的最為大型的微觀企業數據庫,具有指標豐富、樣本信息量大等特點,但它在一些關鍵指標的統計上存在一定的缺失。例如,“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缺少企業CEO交流的詳細信息,這里我們使用樣本數據的另一個來源——國泰安“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數據庫”進行綜合分析。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數據庫提供了中國上市公司管理層人員的基本情況、年薪報酬、持股數量、股權結構變動情況、董事長和總經理變更情況及股東大會情況等方面的信息。其中,我們可以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企業名稱與“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數據庫”中的公司名稱進行匹配,最終本文匹配成功的 1999—2007年的上市公司共有1,496家。
上述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數據庫”進行合并后所得的綜合性數據是本文研究的基礎數據,但由于各種原因,一些企業提供的信息不夠準確或尚未提供部分信息,結果導致原始數據中存在異常樣本。為了使后文的分析結論更加準確和可信,我們在合并數據的基礎上做了以下篩選和處理:(1)刪除新產品銷售額存在缺漏值或負值的企業樣本;(2)刪除雇員人數小于10的企業樣本;(3)刪除CEO信息缺失的企業樣本;(4)刪除工業總產值、企業銷售額、固定資產、營業利潤、利息支出以及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中任何一項存在缺漏值、零值或負值的企業樣本;(5)刪除1949年之前成立的企業樣本,同時刪除企業年齡小于0的企業樣本。本文最終用于分析的上市公司一共有1 463家。
表1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
以下我們就CEO交流企業、非交流企業以及不同形式CEO交流企業在創新量上的差異進行簡單的描述分析,具體結果報告在表2中。從表2中可以看出,非CEO交流企業的新產品銷售額均值為8,232萬元,而CEO交流企業的新產品銷售額均值高達21,782萬元,后者比前者高出13,550萬元,并且這一差異值在1%,水平上顯著。另外,我們還給出了細分 CEO類型的交流企業與非 CEO交流企業的新產品銷售額的均值檢驗結果。具體來看:其一,我們根據是否具有海外留學及工作經歷對 CEO交流企業進行分類,將交流企業劃分為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 CEO交流企業(CEO_F)和無
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CEO交流企業(CEO_H)兩種類型①對樣本進行分類時,對于一個企業樣本期內有多次CEO交流的情況,比如企業A第一次CEO交流時,流入的CEO有海外留學經歷,第二次流入的CEO沒有海外留學經歷,此時根據兩任CEO的任期長短來決定該企業的類型;如果企業A發生三次CEO交流,則根據三任CEO的比例大小來決定該企業的類型(比如三任中有兩任沒有海外留學經歷,則認為該企業為無海外留學經歷的CEO交流企業);發生多于三次CEO交流的企業情況與三次CEO交流的企業定義方式相同。此外,按照性別、年齡和學歷標準進行分類時方法相同。;其二,根據CEO的性別進行分類,CEO_W表示女性CEO交流企業,CEO_N表示男性CEO交流企業;其三,按照CEO年齡進行分類,CEO_D表示年齡大組CEO交流企業,CEO_L表示年齡小組CEO交流企業;其四,將交流企業按CEO學歷層次分為兩組,CEO_R表示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高學歷CEO交流企業,CEO_S表示具有本科學歷以下的低學歷CEO交流企業;最后,根據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將CEO交流企業劃分為國有上市公司(CEO_G)和民營上市公司(CEO_M)兩種類型。結果顯示各細分 CEO交流企業的新產品銷售額的均值都高于非 CEO交流企業,其差異值均至少通過 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初步的計量檢驗表明CEO交流企業比非交流企業具有更多的新產品銷售額。

表1 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

表2 CEO交流企業與非交流企業在創新方面差異的檢驗結果
四、估計結果及分析
(一)基本估計結果
在進入因果效應分析之前,我們首先采用 Probit方法和 Tobit方法分別初步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與創新強度的影響,構建如下回歸式:

其中,下標 i、j、k和 t分別表示企業、行業、地區和年份;vj、vk和vt分別表示行業、地區和年份的特定效應,εijkt是隨機擾動項;是企業 CEO交流虛擬變量,當企業 i有 CEO交流時取值為 1,否則為 0。在本文中,我們用新產品銷售額來衡量創新②由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對“研發支出”指標進行統計的年份僅為 2005—2007年,因此受到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最終選用“創新產出”——新產品銷售額來衡量企業創新。此外,本文也基于2005—2007年數據使用“研發支出”進行了類似的回歸,發現結果沒有顯著差異。。因此在式(5)中,當新產品銷售額大于 0時,企業創新決策虛擬變量 inno取值為1,否則為 0;在式(6)中,inno表示企業創新強度,用新產品銷售額占企業總銷售額的比重來衡量。根據既有的理論與經驗研究文獻,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Xijkt主要選取了資本密集度(zb)、企業規模(size)、企業年齡(age)、企業生產率(tfp)、企業利潤率(profit)和融資約束(fin),它們的衡量方法如本文第三部分所示。除此之外,我們還在中進一步考慮了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①計算公式,其中表示企業i在t年的銷售額表示行業j在t年的總銷售額。,用以控制市場結構因素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如果 herfind越大則表明企業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即壟斷性越強,反之則意味著企業的市場競爭程度越強。
表3第(1)列報告了企業創新決策影響因素的Probit估計結果,CEO交流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為正,并且都通過了 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 CEO交流與企業創新決策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 3第(2)列給出了企業創新強度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這里我們采用 Tobit方法對計量模型(6)進行估計,結果顯示,CEO交流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也均為正,并且至少通過 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考察期內,CEO交流與企業創新強度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此外,我們進一步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動態影響。我們將模型(5)和模型(6)中的CEO交流虛擬變量分解成一組CEO交流之后的年份虛擬變量,即:CEO_0 year,(企業有CEO交流當年)、CEO_1,year(企業有CEO交流后第一年)、CEO_2 year ,(企業有CEO交流后第二年),依此類推。進而將計量模型(5)和模型(6)擴展為:

很顯然,估計系數 ατ和分別考察的是 CEO交流后第η年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和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通過對計量模型(7)和模型(8)的考察,可以揭示出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動態影響,也可以回答類似于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是即刻發生的還是逐步發生的,以及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是否具有持續性等問題。
對計量模型(7)和模型(8)的估計結果分別報告在表 3第(3)列和第(4)列,首先討論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的動態影響。在CEO交流的當年,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的估計系數為 0.27,且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在 CEO交流后的第 3年,其估計系數上升為0.36,隨后估計系數進一步上升至0.50(CEO交流后的第6年)。這表明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不僅具有顯著的即期促進作用,而且它對企業創新決策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持續性,更進一步,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的積極影響在CEO交流之后的 6年里是遞增的。第(4)列的估計結果顯示,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強度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內是較為顯著的,而且也能持續一段時間,同時它對企業創新強度積極影響的程度在CEO交流之后的6年里呈現出遞增的趨勢。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CEO交流不論是與企業創新決策還是與企業創新強度之間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這種正相關關系在 CEO交流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有逐漸增強的趨勢。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據此斷定 CEO交流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下文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對此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

表3 初步估計結果
(二)基于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基本估計結果
這里,我們使用第三部分的傾向得分匹配模型進一步考察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因果效應。首先,我們使用方程式(2)估算傾向得分值,然后在此基礎上采用馬氏距離匹配方法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傾向得分匹配的有效性取決于條件獨立性條件是否得到滿足,即要求匹配后處理組企業與對照組企業在匹配變量(滯后 1期)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否則就說明匹配變量的選取不合理或者所選擇的匹配方法不恰當,在這種情況下傾向得分匹配是無效的。因此,在進行傾向得分匹配估計之前,有必要對樣本的傾向得分配對進行匹配平衡性檢驗。

表4 匹配變量的平衡性檢驗結果
匹配平衡性檢驗一般從兩個方面來判斷配對結果的優劣。一方面是考察各匹配變量在匹配前后的標準偏差,標準偏差越小,表明匹配效果越好,正如 Rosenbaum 和Rubin(1985)所強調的,如果匹配后的標準偏差的絕對值小于20%,,可認為匹配效果較好,以此為基礎的傾向得分估計是有效的。匹配平衡性檢驗的另一方面是考察處理組企業與對照組企業的各匹配變量在匹配后的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通常采用 t檢驗進行判斷。如果在匹配后的 t檢驗不顯著,則表明匹配效果是良好的。表 4報告了以2000年開始有 CEO交流的企業為處理組樣本并且給出了匹配平衡性檢驗結果。從表4中可以看出,匹配后各匹配變量的標準偏差的絕對值均小于 20%,,另外表 4最后一列的均值 t檢驗顯示,在匹配之后,處理組企業與對照組企業在資本密集度(zb)、企業規模(size)、企業利潤率(profit)、企業年齡(age)、企業生產率(tfp)以及融資約束(fin)等方面均不存在顯著差異。據此可認為,本文對匹配變量和匹配方法的選取是恰當的,以此為基礎的馬氏距離匹配估計結果是可信的。
表5報告了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影響的PSM估計結果。這里不僅考察了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的因果效應,而且也考察了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效應。另外,為了得到更為準確的結果,我們以2001年、2003年和2005年為例,對各年開始有 CEO交流的情況依次進行分析。從表 5可以看出,CEO交流可使企業的創新決策提高 0.12~0.19個百分點,并且估計系數均在 1%,水平上顯著。以上分析表明,CEO交流與企業創新決策之間存在顯著的即期因果關系。除此之外,CEO交流也顯著地提高了企業的創新強度,具體而言,CEO交流使得企業新產品銷售強度提高了0.06~0.10,并且估計系數至少通過 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上述分析都是基于水平值的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為了穩健起見,我們在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時還進一步采用了基于倍差法的傾向得分匹配估計(DID-PSM),結果如表 5第(3)列所示。與標準的PSM估計結果相比,采用DID-PSM方法得到的估計系數的絕對值有所下降,但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水平均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這進一步表明CEO交流與企業創新強度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因果關系。對此可能的解釋是:一方面,CEO將其在先前公司學習到的先進管理經驗應用到現任企業,在研發投資時趨利避害,避免創新活動的盲目性;另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 CEO往往充滿組織創新的興趣和對工作的新鮮感,更注重吸納各種先進管理方式來經營企業,傾向于做出更多的戰略變換,強調產品和市場創新(Hambrick和Fukutomi,1991)。

表5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影響的PSM估計結果
(三)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動態影響
上文通過PSM估計揭示了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具有即期的正向影響效應,那么這種正向的影響效應是否具有持續性?接下來我們進一步采用 PSM 方法深入地探究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動態特征。與上文類似,這里也是對2001年、2003年以及2005年開始有CEO交流的情況依次進行分析。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動態檢驗結果報告在表6中。以2001年開始有CEO交流的處理組企業為例,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的影響顯著為正,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的影響程度越來越大。例如,CEO交流后的第 1年①對于一個企業樣本期內有多次CEO交流的情況,以其第一次發生CEO交流的時間為基準。,CEO交流使得企業的創新決策比無 CEO交流企業提高0.13個百分點;CEO交流后的第3年,CEO交流使得企業的創新決策比無CEO交流企業提高0.21個百分點;CEO交流后的第6年,CEO交流使得企業的創新決策比無CEO交流企業提高0.33個百分點。對2003年和2005年開始有CEO交流的情況所進行的分析也能得到類似結論。這可能是因為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和研發的影響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企業研發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國內外眾多學者對研發投入的時間延遲效應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有些學者認為科技投入與產出之間存在著2年的時間延遲(Guan和Liu,2005),而有些學者認為存在3~5年的時間延遲(Scherer,1983;Acs和Audretsch,1991)。所以,只有在長期伴隨著企業研發和創新活動績效的發揮的情況下,CEO交流的技術創新效應才會逐步顯現。
另外,從表6第(2)列可以看出,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強度影響的時間走勢與企業創新決策基本相似,即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程度隨著企業CEO交流年限的延長而增強。同時為了穩健起見,在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動態影響時還使用了DID-PSM方法進行估計,結果見表6第(3)列。與第(2)列的結果相比,不同年限CEO交流的系數值有所下降,但它們的符號以及時間走勢與前者基本一致。這就說明了CEO交流對企業創新強度影響的動態特征較為穩健。

表6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動態影響
(四)異質性分析
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CEO交流企業可以劃分為不同類型,為了更為細致地評估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因果效應,接下來我們采用PSM方法進一步比較研究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活動的異質性影響。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便于考察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異質性影響的動態特征以及出于節約篇幅的考慮,這部分只選取 2005年開始有CEO交流的企業進行分析。
首先,根據是否具有海外留學及工作經歷對CEO交流企業進行分類,將交流企業劃分為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 CEO交流企業(CEO_F)和無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CEO交流企業(CEO_H)兩種類型,相應的PSM估計結果報告在表7,Part 1中。結果顯示,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CEO的交流不僅顯著地促進了企業的創新決策,而且也顯著地提高了企業的創新強度。另外,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正向影響也具有持續性,并且其影響程度是逐年增加的。此外,結果顯示,與 CEO_H相比,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 CEO(CEO_F)交流對企業創新活動的積極影響更大。對其可能的解釋是,海外留學歸國人員大多在國外接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具有相關技術領域的海外工作經驗,而且更了解外資企業的經營戰略和企業文化。領軍型海歸人才往往掌握著先進技術和理念,具有跟蹤世界高新技術發展趨勢的能力(李平和許家云,2011),因而與本土人才相比,其對企業技術創新戰略的制定及創新績效的提高可能具有更大的積極影響。
其次,根據CEO的性別進行分別回歸,CEO_W表示女性CEO交流企業,CEO_N表示男性CEO交流企業,具體PSM估計結果見表7,Part 2。從中可以看出,男性CEO的流入對企業創新決策和創新強度的影響效應均明顯高于女性。男性 CEO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大于女性,這可能是因為由于創新活動往往具有風險高、投資大及周期長等特點,而女性 CEO在風險決策方面更為保守,從而其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相對較小。Gulamhussen等(2010)的研究表明,女性參與董事會與銀行呆賬損失準備金、貸款損失準備金正相關,說明女性更不愿冒險。Faccio等(2011)發現女性CEO經營的公司資產負債率和盈余波動性更低,且生存幾率更高,說明女性CEO更傾向于規避風險。
再次,依據 CEO的年齡在同年度同行業的中位數進行分組,CEO_D表示年齡大組CEO交流企業,CEO_L表示年齡小組CEO交流企業,相應的PSM估計結果報告在表7,Part 3中。結果表明,年齡大組CEO的流入對企業創新決策和創新強度的影響效應均明顯小于年齡小組。這可能是因為 CEO年齡越大,意味著其知識結構老化、認知能力下降、變通能力和處理信息能力降低(Taylor,1975),其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減小。同時年齡大的CEO也可能更加關注聲譽,隱藏或避免壞消息影響其已有聲譽和退休待遇,從而更不愿意做出較大的創新決策,更傾向于傳統的企業經營模式。
年齡越大的高管其風險厭惡程度更高,對公司變革、創新持消極態度,更傾向于采用保守和傳統的方式來經營企業。相比而言,年輕的高管對待變革的態度更積極,一方面他們具有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另一方面他們的學習能力與適應能力更強(Wiersema和Bantel,1992;Barker和Mueller,2002;劉運國和劉雯,2007)。

表7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活動異質性影響的估計結果
又次,將 CEO按學歷層次分為兩組,CEO_R表示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高學歷CEO交流企業,CEO_S表示具有本科學歷以下的低學歷CEO交流企業,相應的PSM估計結果報告在表7,Part 4中。結果表明,較高學歷的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和創新強度的影響效應均顯著大于較低學歷組別。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與個人的信息處理能力和創新能力成正比,從而如果企業CEO的受教育程度比較高,那么其專業理論知識往往較為深厚,對新的管理理念和生產方式的接受能力也較強,更愿意引領公司進行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如果企業的 CEO擁有較好的教育背景,那么其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會有較高的威望,也更傾向于對新方法和新技術的模仿和創新(Thomas等,1991)。另外,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積極影響具有持續性,并且其影響程度逐年增強。
最后,我們根據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將 CEO交流企業劃分為國有上市公司(CEO_G)和民營上市公司(CEO_M)兩種類型,相應的 PSM估計結果報告在表 7,Part 5中。結果顯示,在國有上市公司,CEO交流不僅顯著地促進了企業的創新決策,而且也顯著地提高了企業的創新強度。另外,與公司未分類情況類似,國有上市公司的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正向影響也具有持續性,并且其影響程度是逐年增加的。接下來我們來看CEO交流對民營上市公司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發現CEO交流對民營上市公司的創新決策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其影響效應甚至大于國有上市公司的情況。即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CEO交流在民營上市公司能夠更有效地促進企業的創新活動。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的創新利潤函數中包含了其他的一些政策導向性行為,政府色彩突出是我國國有上市公司CEO的重要特點,國有上市公司的CEO部分由政府任命,CEO交流不能體現市場導向,因而企業創新活動對 CEO交流的反應相對遲鈍。
五、拓展分析:CEO交流與企業創新持續期
在前述研究中我們較為細致地考察了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與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發現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活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這些分析均未涉及企業創新活動的持續期問題,而企業的創新持續期是企業創新動態的重要體現。那么,CEO交流是否有助于延長企業創新的持續期?對該問題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更全面系統地評估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只有持續和穩健的企業創新活動才能真正地為經濟的快速增長注入活力以及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接下來,我們將采用生存分析模型進一步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
我們先定義企業創新持續期為某個企業從有創新活動直至終止創新活動(中間沒有間斷)所經歷的時間長度(單位為年)。為了避免因企業進入退出市場行為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產生干擾,這里我們選取那些在 1999—2007年持續經營的企業作為分析樣本。企業終止創新活動被稱為“風險事件”,在本文中它是指企業的創新產出(新產品銷售額)為 0。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直接采用 1999—2007年樣本數據進行生存分析將面臨數據左側刪失(left censoring)和右側刪失(right censoring)問題。特別是當忽略左側刪失問題時,將傾向于低估企業創新的持續期,我們的處理方法是去掉左側刪失樣本,只選取在1999年沒有創新活動但在2000—2007年期間有創新活動的企業作為最后的分析樣本。另外對于右側刪失問題,可以在生存分析方法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陳勇兵等,2012)。
在生存分析方法中,常用生存函數(survivor function)來描述生存時間的分布特征。根據既有的研究文獻,我們將企業創新的生存函數定義為企業在樣本中創新持續時間超過t年的概率,表示為:

生存函數的非參數估計通常由Kaplan-Meier乘積項估計式給出:

其中,NK表示在 K期中處于風險狀態中的持續時間段的個數,FK表示在同一時期觀測到的“失敗”對象的個數(即終止出口行為的企業數)。
危險函數(hazard function)表示企業在t-1期出口的條件下,在t期停止出口的概率,表示為:

風險函數的非參數估計式可表示為:

在生存分析模型估計之前,我們首先采用Kaplan-Meier估計式(10)初步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圖1給出了有CEO交流企業與無CEO交流企業的創新持續期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其中實線部分代表無CEO交流企業,虛線部分代表有CEO交流企業。從圖1可以看出,有CEO交流企業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位于較高的位置,這表明,與無CEO交流企業相比,有CEO交流企業面臨著相對更低的創新終止風險率,即有 CEO交流企業的創新持續期相對更長。另外我們還注意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兩類企業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的差異也變得越來越大。

圖1 企業創新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
當然,影響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因素還有很多,不能僅憑上述 Kaplan-Meier生存曲線就判定CEO交流有助于延長企業的創新持續期。為了準確地揭示CEO交流與企業創新持續期之間的關系,下面我們使用更為嚴謹的計量分析。考慮到離散時間生存模型具有可以有效地處理結點問題、易于控制不可觀測的異質性和無需滿足“比例風險”的假設條件等優勢,本文采用離散時間cloglog生存模型進行計量分析,模型設定如下:

表8報告了企業創新持續期影響因素的生存分析估計結果,在所有回歸中均對不可觀測異質性進行了控制。其中,前5列是基于匹配前樣本的估計,后5列是基于匹配后樣本的估計,以第(1)列未對CEO進行分類的回歸為例,該列考察CEO交流整體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結果顯示其估計系數為負并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CEO交流可以降低企業終止創新活動的風險率,也就是說可以延長企業創新的持續期,這與前文Kaplan-Meier生存曲線的分析是一致的。rho值顯示,不可觀測異質性引起的方差占總誤差方差的比例約為 43%,,并且rho值的似然比檢驗也在 1%,水平上拒絕了“企業不存在不可觀測異質性”的原假設,從而在模型中控制不可觀測異質性是必要的。此外,在第(2)列中,我們根據CEO是否具有海外留學及工作經歷對CEO交流企業進行分類,當流入的 CEO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時,CEO_F=1,否則為 0;當流入的CEO無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時,CEO_H=1,否則為0。結果顯示,CEO_F的估計系數為負并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有海外留學及工作經歷的CEO交流顯著地延長了企業的創新持續期;CEO_H的估計系數也為負但并不顯著,這說明無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 CEO交流只能微弱地延長企業創新的持續期。在第(3)列中,據 CEO的性別進行分類,CEO_W=1表示女性 CEO交流企業,否則 CEO_W=0;CEO_N=1表示男性 CEO交流企業,否則 CEO_N=0。從表 8第(3)列可以看出,CEO_W和CEO_N的系數均為負,但前者的顯著性水平低于后者,且前者的系數小于后者,這表明,與男性相比,女性 CEO交流對延長企業創新持續期的作用相對較小。在第(4)列中,我們按照CEO的年齡進行劃分,CEO_D=1表示年齡大組CEO交流企業,否則為 0;CEO_L=1表示年齡小組 CEO交流企業,其他情況為 0。回歸結果表明,CEO_D的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而 CEO_L的回歸系數則顯著為負,即年輕的CEO交流更有助于延長企業的創新持續期。最后,根據 CEO的學歷層次對樣本進行分類,當CEO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時,CEO_R=1,否則CEO_R=0;當CEO的學歷處于本科及以下時,CEO_S=1,否則為0。第(5)列結果顯示,CEO_R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而CEO_S的系數并不顯著,此外,CEO_R的系數絕對值大于CEO_S,這說明高學歷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延長作用更大。

表8 生存分析估計結果
以上分析主要是基于匹配前的樣本進行的,為了考察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還采用傾向得分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分析。基于匹配后樣本的估計結果報告在表 8第(6)列~第(10)列中。我們發現,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絕對值與基于匹配前樣本的估計結果相比有所下降,但系數符號和顯著性水平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這說明估計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在對匹配后的樣本進行估計時,部分控制變量估計系數的顯著性出現了下降,這可能與匹配后的樣本量減少有關。
六、結 論
CEO在企業之間的交流是企業技術進步的重要渠道,但迄今少有文獻直接定量分析CEO交流對流入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的目的在于就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進行估計,進而為客觀評估中國上市公司 CEO交流的創新效應提供了一個來自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本文主要得到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基于 Probit和 Tobit模型的初步估計結果發現,CEO交流與流入企業創新決策以及創新強度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正向關系在 CEO交流之后的幾年里一直存在。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揭示了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因果效應。研究表明,CEO交流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因果關系,即CEO交流顯著地促進了企業的創新活動,進一步的動態分析發現,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具有持續性,并且其影響程度是逐年遞增的。
第二,為了更為深入地考察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因果效應,我們對樣本進行分類,在此基礎上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比較研究了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活動的異質性影響。首先從是否具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分類來看,與沒有海外留學經歷的 CEO相比,有海外留學經歷的 CEO,其流入能夠更加有效地促進企業的創新活動;其次由按照CEO性別、CEO年齡以及CEO學歷分組的估計結果表明,男性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大于女性,年齡大的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和創新強度的影響效應顯著小于相對年輕的CEO,高學歷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決策和創新強度的影響更大;最后從流入企業的所有制來看,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民營上市公司的CEO交流能夠更加有效地促進企業的創新活動。
第三,我們還特別關注了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通過采用離散時間生存分析模型的研究發現,CEO交流在總體上顯著地延長了企業創新的持續期。但不同類型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影響存在差異,其中有海外留學經歷的CEO交流比沒有海外留學經歷的CEO交流更有助于延長企業創新的持續期;與男性相比,女性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延長作用相對較小;年輕的 CEO交流比年長 CEO交流更有助于延長企業的創新持續期;學歷越高的 CEO交流對企業創新持續期的延長作用也越大。
因此,政府應當進一步加大力度鼓勵和引導企業高層尤其是海歸高層的流動,并且促進高管隊伍學歷層次的提升。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不同類型CEO交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存在差異,為了更有效地利用 CEO交流的技術創新效應來提升我國的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一方面,政府應該積極引導更多有條件的企業吸引具有海外留學和工作經歷的 CEO的流入,這類 CEO在技術創新上能夠掌握主導權,可以有效利用全球研發資源來獲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要促進企業高管隊伍的年輕化,上市公司要繼續大膽的提拔和使用年輕管理人員,使年輕人早日參與公司決策,這有利于企業研發投入和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
[1] 陳勇兵,李 燕,周世民. 中國企業出口持續時間及其決定因素[J]. 經濟研究,2012(7):48-61.
[2] 龔玉池. 公司績效與高層更換[J]. 經濟研究,2001(10):75-82.
[3] 李景海,林仲豪. 世界政治經濟演變、新產業政策與中國制造業的升級策略[J].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6(3):105-121.
[4] 李 平,許家云. 金融市場發展、海歸與技術擴散——基于中國海歸創辦新企業視角的分析[J]. 南開管理評論,2011(2):150-160.
[5] 李小榮,劉 行. CEO vs CFO:性別與股價崩盤風險[J]. 世界經濟,2012(12):102-129.
[6] 劉小玄,李雙杰. 制造業企業相對效率的度量和比較及其外生決定因素(2000—2004)[J]. 經濟學(季刊),2008(3):843-868.
[7] 劉運國,劉 雯. 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與R&D支出[J]. 管理世界,2007(1):128-136.
[8] 王 建,李思慧. 研發經費異質性、創新能力與科技金融政策[J].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5(4):160-172.
[9] 張斌盛,唐海燕. 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吸收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資本流量指標的視角[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112-117.
[10] Acs Z. J.,Audertsch D. B.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M].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
[11] Adams R. B.,Almeida H.,Ferreira D. Powerful CEOs and Their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5,18(4):1403-32.
[12] Barker V.,Mueller G. CEO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R&D Spending [J]. Management Science,2002,48(6):782-801.
[13] Bennedsen M.,Perez-Gonzalez F.,Wolfenzon D. Do CEOs Matter?[R]. Working Paper,Columbia University,2008.
[14] Bertrand M.,Schoar A. Managing with Style:The Effect of Managers on Firm Polici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169-208.
[15] Bhide A. How Entrepreneurs Craft Strategies That Work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4,72(2):150-61.
[16] Bloom N.,Eifert B.,Mahajan A.,McKenzie D.,Roberts J. Does Manage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India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128(1):1-51.
[17] Chen H. L.,Huang Y. S.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R&D Expenditures:Evidence from Taiwan′s Information-technology Industry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23(3):369-84.
[18] Clayton M.,Hartzell J.,Rosenberg J. The Impact of CEO Turnover on Equity Volatil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2005,78(5):1779-808.
[19] Conyon M. Directors Pay and Turnover:An Application to a Sample of Large U. K. Firm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8,60(4):485-507.
[20] Conyon M.,Florou A. Top Executive Dismissal,Ownership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2002,2(4):209-25.
[21] Coughlan A.,Schmidt R. Executive Compensation,Management Turnover,and Firm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5,7(1-3):43-66.
[22] Dahya J.,McConnell J.,Travlos N. The Cadbury Committee,Corporate Performance,and Top Management Turnover [J].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1):461-83.
[23] Faccio M.,Marchica M. T.,Mura R. CEO Gender,Corporate Risk-Taking,and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R]. SSRN Working Paper,2011.
[24] Felipe J.,Hansen R.,McCombie J. Correcting for Biases When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An Illusion of the Laws of Algebra? [R]. CAMA Working Paper Series,No. 14,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2004.
[25] Girma S.,G?rg H. Evaluating the Foreign Ownership Wage Premium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atching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2(1):97-112.
[26] Gilligan D. O.,Hoddinott J. Using Community Targeting to Provide Drought Relief:Evidence from Ethiopia [R].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Address:Washington,D. C.,2006.
[27] Guan J.,Liu S. Comparing Regional Capacities of PR China-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Paten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5,32:225-45.
[28] Gulamhussen M. A.,Santa S. F.,Portugal B. D. Women in Bank Boardroom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erformance and Risk-Taking [R]. SSRN Working Paper,2010.
[29] Hambrick D. C.,Mason P. A. 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30] Hambrick D. C.,Fukutomi G. D. The Seasons of a CEO′S Tenure [J]. Academic Management,1991,16(4):719-42.
[31] Heckman J. J.,Ichimura H.,Todd P. E.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m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7,64(4):605-54.
[32] Hermalin B.,Weisbach M. Endogenously Chosen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ir Monitoring of the CEO [J].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98,88(1):96-118.
[33] Kang J.,Shivdasani A. Firm Performance,Corporate Governance,and Top Executive Turnover in Japa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5,38(1):29-58.
[34] Kaplan S. Top Executive Rewards and Firm Performance:A Comparison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3):510-46.
[35] Kaplan S.,Minton B. Appointments of Outsiders of Japanese Boards: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4,36(2):225-58.
[36] Morck R.,Shleifer A.,Vishny R. Alternative Mechanisms for Corporate Contro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4):842-52.
[37] Olley S.,Pakes A.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J]. Econometrica,1996,64(6):1263-97.
[38] Rosenbaum P. R.,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J]. Biometrika,1983,70(1):41-55.
[39] Rosenbaum P. R,Rubin D. B. 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 [J]. American Statistician,1985,39(1):33-38.
[40] Salancik G. R.,Pfeffer J. Effects of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on Executive Tenure in U. S. Corpor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0,23(4):653-64.
[41] Scherer F. M. The Propensity to Pat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3,1(1):107-28.
[42] Taylor R. Age and Experience as Determinants of Manager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ecision Making Performanc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5,18(1):74-81.
[43] Thomas A. S.,Litschert R. J.,Ramaswamy K. The Performance Impact of Strategy-manager Coalignment: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7):509-22.
[44] Warner J.,Watts R.,Wruck K. Stock Prices and Top Management Chang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8,20:461-92.
[45] Weisbach,M. Outside Directors and CEO Turnover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8,20:431-60.
[46] Wiersema M. F.,Bantel K. A. Top Management Team Demography and Corporate Strategic Chan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2,35(l):91-121.
[47] Volpin P. Governance with Poor Investor Protection:Evidence from Top Executive Turnover inItal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64(1):61-90.
[48] Zajac E. J.,Westphal J. D. Who Shall Succeed? How CEO/Board Preferences and Power Affect the Choice of New CEO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39(1):64-90.
[49] Zhang Y.,Rajagopalan N. When the Known Devil Is Better than An Unknown God: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lay CEO Success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47(4):483-500.
JEL Classification:J63 L20 O33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CEO Transfer: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Xu Jiayun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Whether the transfer of CEO between different enterprises can affect enterprises′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re hasn′t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bove problems so far. Based on the firm-level micro data from 1999 to 2007,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CEO transfer on firms′ innovation by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causal effect between CEO transfer and firms′ innovation,the facilitation effect of CEO transfer on firms′ innovation is sustainable and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2)The effects of CEO transfer on firms′ innovatio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firm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whether CEO has overseas study and working experience or not,different gender,different age,and different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3)We als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effects of CEO transfer on firms′ innovation duration,we find that CEO transfer helps firm to raise the duration of innovation as a whole,but the effects are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EO transfer. This paper provides a micro-level basis for objectively evaluating the innovation effects of CEO transfer in Chinese firms,and it also provides some beneficia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encouraging and facilitate CEO transfer between enterprises.
CEO Transfer;Listed Companies;Technology Innovation;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 許家云,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情研究院(郵編:100084),E-mail:xujiayun321@163.com。本文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貿易自由化對中國企業自主創新及出口競爭力升級的影響研究”(71403135)、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一等資助項目“人民幣匯率變動、創新驅動與中國出口競爭力升級研究”(2016M59007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中間品進口、創新驅動與中國出口競爭力升級研究”(16YJC790114)以及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對京津冀外向型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TJYYWT16-018)的階段性成果。此外,特別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文章進行細致的評審和提出寶貴的建議。當然,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