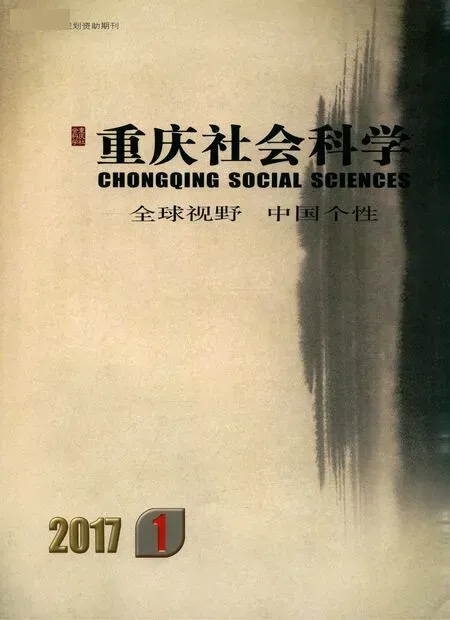人口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與生物學解釋*
楊檸聰 李尚澤
人口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與生物學解釋*
楊檸聰 李尚澤
全面二孩政策作為人口供給側改革的突破口,具有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重大意義。現階段,該政策面臨如下困境:生育觀念難以轉變,生育欲望消退;不孕不育高發,生育能力降低;醫療資源緊張,生育健康風險增加;人口素質下降,家庭觀念淡薄;工作壓力增加,養育精力減少;生活成本增長,住房條件難以保障。面對當前人口老齡化、年輕勞動力負增長,獨生子女增多、“失獨”風險突出,在學人數減少、教育規模萎縮,單身危機爆發、社會秩序遭受沖擊等背景,推進人口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
全面二孩政策 人口供給側改革 人口紅利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科社教研部 北京 100091;美國西北大學 美國芝加哥 IL60611
馬克思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人口承載著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要素。沒有人口作載體,家族、種族、民族,甚至國家就不復存在。如果這個群體組織“人丁興旺”,那么它在世間延續的可能性就更大。同時,人口的變化對經濟的發展也有著巨大的影響。亞當·斯密認為,“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2]也就是說,一方面,人口的增多本身會使微小的需求逐漸放大而刺激供給產業鏈的形成,并擴大市場容量;另一方面,人口在市場中本身也已經成為一種勞動力資本和智力資本,對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如果將人口簡化為資本的載體,那么人口的多少就代表著資本的多少,人口的流動就體現著實力的流動,人口流入的地方總是欣欣向榮,而人口流出的地方多是破落敗壞。
現階段,我國正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前進,這時就更需要源源不斷的人口為此提供動力。全面二孩政策作為人口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方面,具有經濟學和生物學的重大意義。
一、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背景
研究人口供給側改革就必須先考察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時間范圍內減少了新生人口的出生率,因此,在一段時間后,它就必然導致年輕勞動力的減少和老齡人口在人口結構中的占比增加。另一方面,由計劃生育政策衍生而來的獨生子女政策雖然在控制人口規模方面作出了貢獻,但同時也導致了諸如“失獨家庭”增加、在學人數較少、教育規模萎縮、單身危機沖擊社會秩序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發生,這都需要引起注意。
(一)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
人口老齡化是指在一定時期內,老年人口的增長幅度和速度大于新生人口的增長幅度和速度。也就是說,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增加。當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0%之時,即可認為這個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期。從2012年末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85億,占總人口的13.7%,相對2011年同比增長了0.47%。根據預期,到2020年,我國老年化人口將會達到1.6億,在2030年達到2.3億,2040年達到2.9億,并在2050年的時候接近3億,那時候我國將進入嚴重老齡化社會。[3]因此,在人口總量波動較小的情況下,老年人口比重將越來越大,黃金年齡勞動力人口的比重將越來越小。
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參與勞動生產的人口減少,“勞工荒”“用工荒”問題將會凸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還意味著整個社會需要養老的人口數量將增多,社會養老金將面臨支付危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能取得如此大的發展成果,充沛的勞動人口是重要保障。因此,在沒有新科技革命能再次帶來生產力較大飛躍的情況下,經濟的發展速度放緩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相應地,國家福利政策的壓力也將必然增加,哪怕是延遲退休的政策得以全面貫徹,也難以長期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因此,不難看出,人口老齡化對我國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較大的挑戰,它既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
(二)年輕勞動力負增長,經濟進入新常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源源不斷增加的勞動力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跡奠定了基礎。但從2013年開始,我國15~64歲的總勞動力人口在達到9.98億的頂峰之后迅速下降。從2016年開始,我國40~60歲的人口已經開始超過15~39歲的人口。這意味著我國未來經濟將面臨年輕勞動人口供給的斷崖式風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些經濟學家設想通過產業升級的方法來挽救低迷的經濟形勢以獲得更大的人口紅利,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經濟的轉型升級是需要很多年輕勞動力人口的智力和體力作為支撐的。
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人體每天都會發生DNA和細胞的損失,但是年輕勞動力人口能夠輕松地自我修復;人進入老年階段之后,人體機能的修復能力就會有所下降,部分人就會患上各種癌癥和疾病。年輕勞動力代表著社會修復能力,雖然年輕勞動力充足的時候會出現如發達國家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問題,但它在發展過程中也自我修復了,可一旦年輕勞動力人口減少,同時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經濟問題就難以自我修復了。年輕勞動力人口的短缺還可能讓“中國制造”既沒有量又沒有質,這會讓中國的跨國企業和進出口公司陷入尷尬境地。充足的年輕勞動力人口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即使有很多專家為我國經濟發展開出各種處方,但是如果人口生育率不能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就缺乏持續支撐。
(三)獨生子女增多,“失獨”風險突出
鼓勵獨生子女的政策,在一定時期內限制了人口的擴張,降低了生育率,其政策帶來的效應是否有益,在哪一階段有益還需要進一步討論,但其帶來的風險近年來逐漸凸顯。穆光宗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其風險性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和獨一性。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為了“稀有品”。孩子承載著長輩們的全部希望。這也一定程度上促使“獨子難教”的情況時有發生。況且,一旦獨生子女出現生命危險,那么父母面臨的精神壓力、經濟壓力和養老壓力將會陡然增加。獨生子女一旦病殘,他們不但沒有能力贍養自己的父母,還有可能需要父母的照料。除此之外,就獨生子女父母來說,一個孩子帶來“空巢”的可能性更大,父母在孩子成家立業之后,就可能成為孤家寡人,要是孩子也遇上其他不幸,沒有兄弟姐妹相互扶持,那他自身的處境也相當堪憂。[4]同時,對農村人口“多生多育”的批評和蔑視是值得反思的,因為生育人口的多少并不是人口素質高低的評判標準,而是經濟能力相對較差的人口規避“失獨”和增加“家庭社會能力”的措施。也就是說,這只是生命物種為了延續的一種本能手段。
(四)在學人數減少,教育規模萎縮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的小學在校人數從1998年開始減少,大量的中小學被撤并,一部分教育資源被閑置和浪費,專職的小學教師也從1999年的586.1萬人減少到2011年的560.5萬人。1999年之后,我國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大學開始擴招。2011年,我國高校招生達到了681.5萬,但從2008年起,高考報考人數開始出現負增長,從而導致高校擴招的空間持續縮小,使得生源競爭日趨激烈。
(五)單身危機爆發,社會秩序遭受沖擊
婚姻和感情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隨著人口結構失衡導致光棍數量的擴大,穩定的社會秩序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數據表明,2002年日本有54%的25歲以上女性、43%的30歲出頭的男性未婚,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預計在2020年,有30%的日本家庭都是單身家庭,而首都東京地區的單身家庭比例將超過40%。香港的單身比例目前已經超過日本,北京、上海、廣州等發達城市的單身比例也正在追趕香港。同時,一項研究表明,工作壓力較大的,并長期單身的男性或女性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會更大。美國的保險業公司專門研究了這部分單身人口對社會的影響,發現單身人口出現汽車事故的比例遠遠高于已婚人群。因此,他們對單身人士設定的汽車保險繳納金額要遠高于已婚人群。他們甚至預測,大量光棍的存在將會對保險業和金融業構成威脅。[5]數據表明,2010年之后,我國的單身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預計在2022年,單身人口數量將超過2000萬。
除上述方面外,老無所養、購房年齡增長等也是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參考的背景。人口數量對民族、國家的興衰具有重要的影響。在當今國際環境依然不容樂觀的背景下,增加人口依然是基本導向。然而,現階段通過全面二孩政策來增加人口數量還面臨著諸多困境。
二、全面二孩政策可能遭遇的困境
實施和推行新政是有一定難度的,也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和推行也是一樣。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物質文明的發展,節育和享樂觀念的擴張,以及現代城市生活和住房壓力的增加,一部分青年人難以再改變生育致貧的觀念,也難以再承擔起“優生優育”的家庭責任。同時,生育能力的下降、生育風險的增加、養育精力的減少也使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陷入困境。
(一)生育觀念難以轉變,生育欲望消退
生育觀念是人們對待生育行為的意愿和態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受種族主義、優生學和人口學的影響。19世紀以來,影響人們生育觀念的首先是種族主義。種族主義的目的是為了讓社會有更少的“劣等人”和有更多的“優等人”。[6]在西方國家內部,雖然白色人種的經濟地位比有色人種要高,但是窮人和有色人種以及貧窮國家整體的高生育率引起了“高貴”種族主義者的擔心,他們擔心自己將會被劣等人種“逆淘汰”。為了防止這種逆淘汰,1912年他們在倫敦成立了國際優生學大會。他們毫不避諱地談到:“優生學不是人類的發明,而是眾所周知的普世價值,即優等人生存下來,劣等人被消滅。”[7]優生學會在后來得到了洛克菲勒的支持,很多上層人士也成為了它的會員。他們在窮人、有色人種和發展中國家宣傳計劃生育,試圖改變下一代人的階層結構,但是他們并不遵守節育的觀念,和他們宣揚的相反,他們生育孩子的數量往往比其他人都要多。后來這種觀念成為了一部分人的政治工具。不論是種族主義、優生學還是人口學,它們最初都是為“優等人”而服務的,其直接目的是為了消滅“劣等”人口對他們的生存危脅。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堅持“人多力量大”的古老哲學,但后來由于城市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城市居民工作和住房等現實壓力的增大,避孕和節育的觀念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的共識。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全面實行計劃生育,“少生、優生”等口號逐漸深入人心。即使有學者批判優生理論的缺陷和不足,但也難以扭轉“生育致貧”對人們的社會心理影響,或者說,要改變這種想法,還需要更長一段時間,至少它應該會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效用發揮前后有所變化。
(二)不孕不育高發,生育能力降低
根據醫學統計,近30年來,我國的不孕不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1%~3%快速上升到12.5%,也就是說在八對孕齡夫婦中就有一對不孕不育。而用國際上對不孕不育的統計標準來看,我國原發性不孕率高達17%。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不孕不育將成為僅次于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的第三大疾病,而較大的精神壓力、性混亂導致的生殖器感染都是不孕不育的原因。
根據2016年上半年國家衛計委披露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分別下降到了20.1/10萬和8.1%,比2000年分別下降了62.1%和74.8%。但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婦死亡率不跌反升,比2015年同期上升了30.6%。雖然目前還無法確切證實孕產婦死亡率上升與全面二孩政策有關,但從醫學角度來看,晚婚晚育的觀念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引產和墮胎,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齡產婦再次懷胎的健康風險不斷增大,從而使生育成功的概率逐漸減小。當然,這也和全面二孩政策加劇了婦產醫療資源的供求矛盾有一定的聯系。
不僅如此,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癥以及不良飲食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女性卵巢功能異常,子宮發育不良、性機能異常,從而降低了女性受孕的可能性。而從男性方面來講,與1940年相比,如今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都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并且精子活力也在下降。
(三)醫療資源緊張,生育健康風險增加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涉及女性孕產的過程。可以預見的是,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發展起來的孕產醫療設施難以滿足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要求。從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年,也就是2016的情況來看,全國眾多醫院出現了孕婦激增、產科門診爆滿、產科床位短缺的情況。有的孕婦為了預約產檢甚至不得不派出整個家庭晝夜幫忙排隊。孕產醫療資源的供給不足。這一方面會導致高危產婦可能在生育過程中得不到良好的救治而死亡,還可能促使部分醫院采取“短、平、快”的剖腹產以減少孕產婦在醫院的生育時間,從而提高病床的利用率和其他孕產婦的治療率。
世界衛生組織曾建議,在普通醫院,剖腹產的比例不應該高于10%,即使在專門收治疑難雜癥的特殊醫院,剖腹產的比例也不應該高于10%。但是在我國,剖腹產的比例目前已經高達46%,而有的婦產科醫生則認為可能會達到60%甚至70%。當然,這也和年輕孕產婦懼怕生產的疼痛,誤認為自然生產會影響體形等有關。剖腹產帶來的健康風險不容小覷。它會破壞子宮的完整性,有剖腹產史的孕婦在今后的妊娠過程中出現子宮破裂的概率會增加。因此,剖腹產不僅會增加生育的健康風險,還會降低婦女再生育的意愿。
(四)人口素質下降,家庭觀念淡薄
獨生子女政策一般被認為是實現優生優育、提高人口素質的手段。從一定程度上來講,人口的心理素質比身體素質更重要。年青一代雖然在生理上早熟,但在心理上晚熟。一旦承受的經濟壓力增加,他們的“心理撫養能力”就會隨之下降。由于多子多女的家庭可以創造有利于孩子全面發展的人文環境,因而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的能力也趨于強大。而獨生子女家庭培養的孩子往往擁有較強的個性。這部分人口在社會中往往注重自己而忽略他人,甚至在長大之后也缺少對父母應有的敬重和貢獻社會、服務社會的情懷。20世紀80年代初的部分獨生子女由于難以適應人才市場的需要而成為“啃老族”。同時,他們在進入婚姻之后也有可能較少地承擔家庭責任,這使得女性沒有安全感,不敢生育孩子。“閃婚”、“閃離”等名稱甚至成為特定時代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離婚率持續增加,1978年僅有28.5萬對夫妻離婚,而2011年就共有211萬對夫妻離婚。高離婚率的產生一方面是因為獨生子女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雙方父母過度干預子女家庭的行為。由于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口流動性的空前增加,西方享樂文化的滲入,家庭人口之間交往時間也相應減少,給婚姻帶來了諸多隱患,當婚姻瓦解時,這個家庭的人口再生產也會停滯。
(五)工作壓力增加,養育精力減少
在農業社會,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緩慢的生活節奏往往與糧食作物的生長周期和天體的運動周期相關。他們的生產活動主要是與自然打交道,雖然物質生活并沒有工業社會那么發達,但他們的心理是相對滿足的。因此,在農業社會下的人口自殺率較低,而心理安全感較高。從農業社會簡單生產生活的方式來看,他們是可以預測每天的或者未來幾十年的生活狀態的。而同時由于交通和信息交往的滯后,農業社會的人口較少在日落之后進行社交活動,這為家庭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也給生育人口和養育人口提供了更多的精力,但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后就不一樣了。大工業化生產在給農業人口或者無產者提供就業機會的同時,也讓城市和農村出現了斷裂。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和物質生活水平的裂痕往往也伴隨著許多家庭的撕裂。在城市就業的部分人口往往將妻子留在了農村,由于工業化生產往往需要勞動力保持連續性的生產工作,因而這部分人口聚少離多的家庭生活方式難以給他們帶來優良的養育條件,同時也單方面地增加了他們養育孩子的負擔。即使拋去這部分人不論,我們也會發現在城市生活中的許多“就業替代”現象。馬克思甚至感嘆:“一個除了自己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這些無產者只有得到有產者的允許才能進行勞動,也就是說他們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夠生存。”就業壓力的增加和就業機會的減少往往會使社會中產生許多 “生產性過剩人口”,這部分失去“飯碗”的人往往在最初茫然不知所措,社會心理安全感驟降,不僅身體在城市中游蕩,其心理也在游蕩。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他們不僅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生育孩子,也擔心生育孩子將會造成物質、工作機會(包括升職)和技能上的損失。
(六)生活成本增加,住房條件難以保障
人口生產之后還需要養育,養育除了一般的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障之外,最重要的還是需要良好的居住環境,也就是住房條件。美國的生育率能夠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與其寬敞的住房和合理的房價有關。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的生育率只有0.9~1.2的原因則是其高額的房價增加了人們的生活成本,以及狹小的室內外居住空間抑制了人口再生產。在上海、北京、深圳這些城市,即便是沒有計劃生育,多數人也是養不起兩個孩子的,即使一部分人口在一定時間內滿足了生育的住房保障條件,但在一定時間后,是否還具有良好的生育能力又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很多育齡婦女陷入了有生育能力時沒有生育條件,而有生育條件時沒有了生育能力的矛盾之中。在重慶等城市,政府建設大量的廉租房、公租房以及增加房地產的供應量,使房價維持在合理的水平,讓更多的人口擁有進行人口再生產的基本住房條件。新生人口不斷產出而進入生產領域和人才市場,這也是近幾年重慶GDP增速在全國領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全面二孩政策的必要性解釋
盡管實施全面二孩政策還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和困難,但是面對其嚴峻的背景和形勢,積極推進全面二孩政策又是迫在眉睫的。從宏觀上闡釋其經濟學與生物學意義,讓更多人明白國家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全面二孩政策的經濟學闡釋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論假設人口的自然增長是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生產的增長充其量不過是算數級增長,這種增長間的差別將會導致大量的過剩人口出現,這種過剩人口將難以擁有糧食來維持生命,而這種過剩人口只能通過饑荒、瘟疫、戰爭、節育和經濟萎靡等手段來解決。雖然這種理論在短時間內具有一定的效用,但長期來看,這種觀點只是屬于消極的人口經濟發展理論。[8]因為事實正好與馬爾薩斯宣揚的人口論相反。從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來看,從1800年以來的200年中,忽略通貨膨脹因素不計以外,食品價格事實上已經下降高達90%,這就意味著即使世界上最貧困的人口也能夠填飽肚子。同時,人口作為創造生產、發展生產、創新生產的推動要素,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因此,它并非馬爾薩斯所言,過多的人口會導致經濟萎靡。根據庫茲涅茨的理論,人口增長可以促進消費品需求膨脹,而消費品需求的增加也會額外地刺激生產廠商的投資,再加上經濟全球化和貿易國際化的影響,人口規模較大的地方往往會形成經濟消費和經濟交易的聚集地,這種聚集地的形成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減少人口的生活成本。換句話說,人口本身就成為了推動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的生物載體,同時,人口增長也可以為基礎設施建設帶來規模經濟效益。
部分人為了避免“缺糧”而選擇了節育或者不育。長遠來看,這直接導致了參與勞作的人口逐漸減少。人口減少產生的“用工荒”“勞工荒”使人力成本逐漸上升,企業賺不了錢,勞動人口也無法獲得收入。人口作為需求與供給的兩端,哪一端不平衡都不行。人們有了消費需求,自然能帶動供給生產。當消費需求形成一定規模之后,供給生產也會逐漸擴大,消費與需求之間的產業鏈就能養活更多的人口,也有更多的人口能享受這種規模效應帶來的人口紅利。也就是說,人口資本的報酬和收益是遞增的。所以,不管是需求端還是供給側,消費者還是生產者,他們都是實實在在的人,這些人口是經濟發展的承擔者。因此,沒有充足的勞動力,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不普遍地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勞動人口數量的增加也難有起色。
(二)全面二孩政策的生物學闡釋
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暴露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之中,人類也不例外。口頭上承認普遍的生存競爭是較容易的,但要在思想上深刻認識到這一點需要一個過程。兩只狼在饑餓的時候為了爭奪食物而相互撕咬,可以說是真正的生存斗爭。生長在沙漠邊緣的一株植物,雖然更恰當地說它是依賴水分的,但也可以說是抵抗干旱以爭生存。每年結一千粒種子的植物,平均只有一粒種子能夠開花結果,那是因為它在傳種中就早已和生長在地面上的同類或者不同類植物相斗爭。我們容易發現,在田間收獲大量的谷物和油菜籽得以保存,正是因為它們的種子和吃它們的鳥類數量相比,占有絕對的多數。可以說每一種生物想在生存競爭中取得優勢并獲得生命延續,都必須極其努力地增加個體數目。因為在每一世代或間隔周期中,大的競爭毀滅都不可避免地降臨于幼者或者老者,但只要有多余的種子得以保留,那就可能再次生長。事實上,同種個體間的生存斗爭會比異種之間的斗爭更為激烈,因為同屬的物種通常在習性、體質、構造方面都十分相似。雖然我們無法在同類等量的物種競爭中占據優勢,但是數量的增加在有時候會變成力量的增加。
同一物種都必然會在它生命的某一時期、某個季節、每一世代或間隔時期,在生存斗爭中被大量毀滅。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社會和人類社會中的生存斗爭都是緩急交替的。毀滅經常是迅速的,而強壯和數量眾多的群體將會繼續生存和延續下去。人類作為生物種群中的一員也是如此。無論人類身體與大腦怎么進化,擁有怎樣改造世界的能力,也無法逃離自然界的基本問題——生存競爭。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開辟新大陸的創舉,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都是為了給本生物群的繁衍和發展創造更好的生存條件和需求供給市場。顯然,這種人類競爭的方式也從未超出生物鏈所遵循的法則。而要想在社會生物鏈中占據頂端位置,其物種數量是基本且至關重要的因素。因為歷史證明,數量少的種族很少能消滅或一直奴役數量多的種族,而基數大的種族往往消滅、吞并、同化基數小的種族。人不論是作為生物中的一員,還是脫離于一般生物的高級動物,都無法脫離生物競爭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而要想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就必須增加自己族群的數量,通過擴大人口基數來提高世代延續的概率。
四、結語
新陳代謝是生命現象的最基本特征,沒有人口的“生生不息”,就沒有文明的生生不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是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政治、經濟、國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賴于人口安全。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能夠持續發展。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長期的低生育率將威脅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國防、民族心理產生重大影響。人口興,則國興,人口強,則國強。全面二孩政策的直接目的便是增加人口,為國家社會發展提供可持續的動力。計劃生育的國策不會變,但是計劃生育的數量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人口問題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更是國家發展戰略的宏觀問題。實現人口供給側改革,為“兩個一百年”目標提供各方面的人才資源,還需要我們提出解決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諸多困境的有益方法。但不管怎樣,面對當前國內國際復雜形勢,它都是具有經濟學與生物學必要性意義的。
[1]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6 頁
[2]F.A.Hayek.The Fatal Conceit.T.J.Press,1989,p.120.
[3]《60歲以上人口已達1.85億》,《南方日報》2012年3月2日
[4][5][7]易富賢:《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年,第210、188、65 頁
[6]David Kennedy.Birth Control in American:the Career of Margaret Sanger.New Heav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116.
[8]左榮金:《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國際經濟評論》2010年第6期,第127頁
The Economic and B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Population Supply-side Reform
Yang Ningcong Li Shangz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as a breakthrough of reform of the population supply-side,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economics and biology fields.At present,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such as unchanged fertility concept with fading fertility desire,high infertility ratio with reduced fertility ability,few medical resources with more fertility health risk,decreasing individual quality with weak family concept,high working pressure with little fertility energy and high living price with housing condition no guarantee.In any case,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opulation supply side is imminent when we are in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population,negative-growth young labor and slow economy growth,more one-child family with more risk of no child family,few students with shrink education size and single crisis with breaking society order.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population supply-side reform,dilemma,economics,biology,necessity explanations
*該標題為《重慶社會科學》編輯部改定標題,作者原標題為《全面二孩政策——人口供給側改革的背景、困境及其經濟學與生物學必要性解釋》。基金項目:中共中央黨校創新工程課題 “社會主義制度與發展規律研究”(批準號:01012050011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