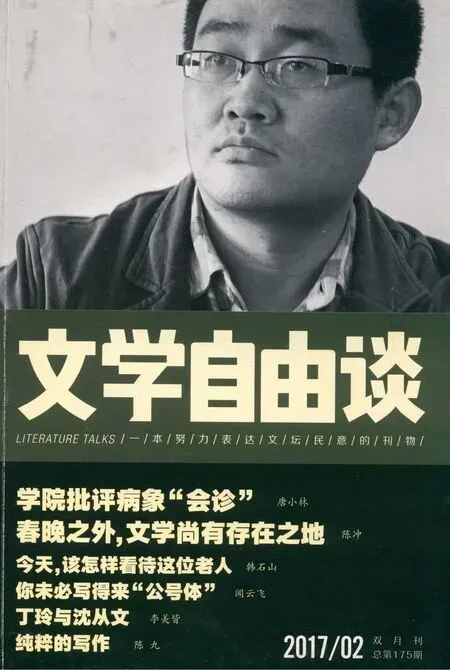詩歌的粉紅色調
2017-03-11 18:20:09任芙康
文學自由談
2017年2期
任芙康
詩歌的粉紅色調
任芙康
我昨天從天津來,明天回天津去,跟寒冷的北方,雖只有三兩日分手,但來到青綠的深圳,置身于比天氣更宜人的詩歌聚談,令人喜悅。畢竟,短暫的暖和,也是幸福。寫詩,被一些人認為是私人化、個體化的創作,似乎只有關在門窗緊閉的書齋里,才能寫出讓五百年之后的子孫頂禮膜拜的史詩。其實,可能大謬。詩歌詩歌,表明詩離不開歌;歌舞歌舞,表明歌離不開舞。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鮑勃·迪倫,一位民謠歌手,行吟詩人,卻創造出嶄新的文學表達。而下午的詩歌朗誦,聽說除了配音,還有伴舞,將會同樣告訴我們,詩歌寫作,只有摒棄盲目高雅的幻覺,承受地氣潤澤,經受生活滋養,領受時代恩惠,接受民眾鑒賞,方有望真實的興盛。
1964年,我14歲,捧著梁上泉的《山泉集》,仿效涂鴉。第二年春天,發表第一首詩歌。稿費兩元,買了100根棒棒糖,全班48位學生,加上班主任和語文老師,人手兩根。嘗過棒棒糖的甜頭,同學中多了好幾位詩友。到了二十來歲,有一天,照鏡子,突然發現自己,相貌呆板,跟詩人的模樣,完全不配。從此,再不寫詩。但依循曾經愛詩的慣性,就只是讀。再后來,又參加一些詩歌的評獎,就還是讀。讀來讀去,覺出自己的心里,比較接受聲響小的詩,比較接受色彩淡的詩,比較接受含義淺的詩,或者說,比較接受家長里短的詩。譬如,你們深圳,有位黃姓朋友的詩作,便是我喜歡的類型之一。在他從容的表達里,不見大呼小叫,劍拔弩張。……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