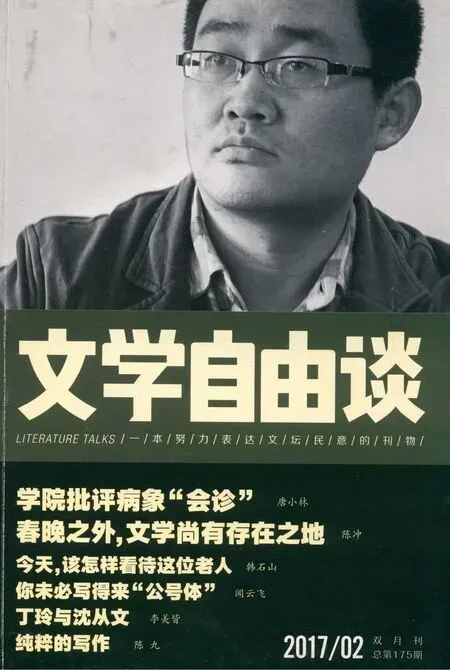發(fā)現(xiàn),只在一瞬間
2017-03-11 18:20:09董兆林
文學自由談
2017年2期
董兆林
發(fā)現(xiàn),只在一瞬間
董兆林
那年時令已經(jīng)入冬,天空有些陰沉,走在街上寒意襲來,禁不住縮緊了雙肩。待走進明鑒法師的新書《一葉一菩提》的發(fā)布會現(xiàn)場——大悲禪院的妙法堂,廳堂內(nèi)的溫暖撲面而來,隨之而至的還有沁人心脾的氤氳禪香。
這本明鑒法師的新著,其發(fā)布會地址,選擇在了始建于明末清初,天津目前唯一一座十方叢林寺院的大悲禪院,原因有二:一是這本書禪意十足,新書發(fā)布和寺院環(huán)境相得益彰;其次,明鑒法師出家前,本是天津的一位實力派畫家,師承津門著名畫家梁琦先生。2006年,他在44歲時披剃出家,虔誠于青燈黃卷,研習佛法,遍訪名山,求學問道,常駐于湖北黃梅雙峰山下的四祖寺,成為一名佛門弟子。因此,他的新書發(fā)布選擇大悲禪院,可謂適得其所。
上午十時整,焚香畢,三聲法鼓響過,明鑒法師的新著《一葉一菩提》的發(fā)布會開始。妙法堂并不闊大,布置得簡潔樸素。坐北朝南的觀世音菩薩像前,幾排鋪飾著黃絹的長桌長凳,相向而對,中間空地的琴架上擺放著一張古琴和一柄竹簫。主持人介紹說,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張瑤琴,身價不俗,它可是來自明朝的寶物。眾人訝然,細觀這深褐色的琴面,通體古樸潤澤,上面密布著一排排極細密的斷紋,仿若歲月流逝的印痕。佛法講緣,古琴穿越時空而來,悠遠的歷史氣息倏忽縈繞在我們的身邊。兩位音樂家操琴持簫聯(lián)袂為大家演奏了古樂《平沙落雁》和《高山流水》,一時古韻悠揚,委婉流轉(zhuǎn),似空谷傳音,余味綿長。……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