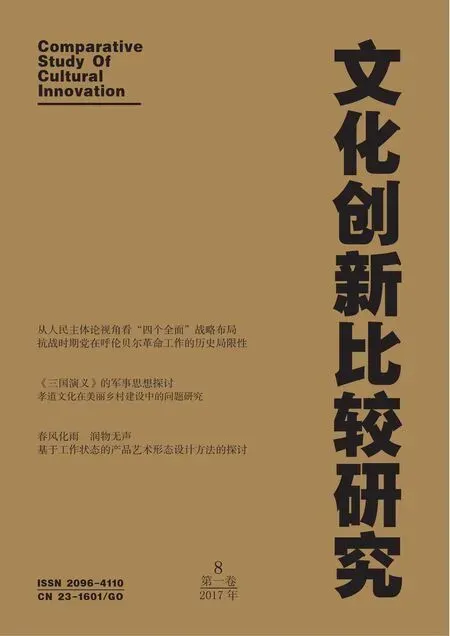《謝氏南征記》的敘事藝術(shù)
李宏偉
(中國(guó)青年政治學(xué)院中文系,北京 100089)
《謝氏南征記》的敘事藝術(shù)
李宏偉
(中國(guó)青年政治學(xué)院中文系,北京 100089)
《謝氏南征記》是韓國(guó)古代作家金萬(wàn)重創(chuàng)作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意在諷諫,因影射肅宗廢后和張禧嬪的荒淫亂政,出于明哲保身和主動(dòng)避禍的現(xiàn)實(shí)考量,小說(shuō)背景設(shè)置在中國(guó)明朝,作者有意將常用的敘事場(chǎng)景如花園、小妾居所百子堂、書(shū)房等做了反諷性處理,并將敘事空間擴(kuò)展到家園之外,對(duì)冥界、神界等非現(xiàn)實(shí)空間的運(yùn)用和開(kāi)拓不僅有效地展示了主要人物漂泊和離散的受難過(guò)程,而且反映出儒家理想在現(xiàn)實(shí)中的困窘。小說(shuō)敘事策略的成功運(yùn)用體現(xiàn)了韓國(guó)古代敘事藝術(shù)取得的成就。
《謝氏南征記》背景設(shè)置;敘事場(chǎng)景;敘事空間
《謝氏南征記》朝鮮古代文學(xué)史上一部重要的小說(shuō),由李氏朝鮮中期著名文人金萬(wàn)重 (1637-1692)創(chuàng)作。金萬(wàn)重,字重叔,號(hào)西浦,出生于世代為官的書(shū)香門(mén)第,曾祖金長(zhǎng)生是一代名儒,父親金益兼在1637年為抗擊女真族的入侵,棄筆從戎,戰(zhàn)死于江華島,兄長(zhǎng)金萬(wàn)基是肅宗國(guó)王(1674-1719年在位)的岳父,金萬(wàn)重自己有極高的才華和文學(xué)造詣,盡管如此,但因?yàn)楫?dāng)時(shí)朝廷內(nèi)部嚴(yán)酷的黨爭(zhēng),他被罷官、流放,最終客死謫所。他為后世所銘記,主要是因他的詩(shī)集《西浦集》、文學(xué)評(píng)論集《西浦漫筆》以及小說(shuō)《九云夢(mèng)》和《謝氏南征記》,特別是他在貶謫流放生活中創(chuàng)作的這兩部小說(shuō),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視為韓國(guó)古代長(zhǎng)篇小說(shuō)誕生的標(biāo)志。兩部小說(shuō)相比,中韓學(xué)界對(duì)《九云夢(mèng)》的研究遠(yuǎn)超出《謝氏南征記》,如果說(shuō)《九云夢(mèng)》中楊少游的經(jīng)歷是作者的理想,最終楊少游由儒入佛、回歸為蒲團(tuán)上打坐誦經(jīng)的性真的價(jià)值取向是作者在飽嘗宦海沉浮、仕途險(xiǎn)惡對(duì)現(xiàn)實(shí)徹底失望后自我在精神上的選擇,是作者的寫(xiě)心之作,那么《謝氏南征記》則不同,講的并非作者自身的故事,而是一部耐人尋味的勸諫之作。這樣一部小說(shuō)是作者金萬(wàn)重有意為之,他的真實(shí)處境是充滿后宮糾紛和朝廷黨爭(zhēng)的朝鮮肅宗時(shí)期,李氏朝鮮的肅宗(1661-1720)是李氏朝鮮的第19代王,1674-1720年在位。這位國(guó)王在他即位之前的1671年,與金萬(wàn)重的兄長(zhǎng)金萬(wàn)基之女結(jié)為連理,在他即位后,金萬(wàn)基之女成為肅宗王的正妃仁敬王后(后于肅宗六年即1680年死于天花),仁敬王妃死后冊(cè)立大臣閔維重之女為王妃,即仁顯王后,但沒(méi)有子嗣,后來(lái)寵愛(ài)張禧嬪,張禧嬪生育后不斷進(jìn)讒言誣陷仁賢王后閔氏,導(dǎo)致國(guó)王在肅宗十五年(1689年)廢掉閔氏立張禧嬪為王妃。黨爭(zhēng)是李氏朝鮮時(shí)期的政治重弊,肅宗時(shí)期南人黨與西人黨的爭(zhēng)斗十分激烈,朝臣與后宮總有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盡管張禧嬪行為不端,與肅宗的叔輩東平君私通,聲名狼藉,但南人黨支持張禧嬪,而且因?yàn)閺堨麐宓牡脤櫠值脛?shì),西人派對(duì)于張禧嬪的丑行力諫肅宗,反屢遭誅戮與流放。正如韋旭昇先生所言,“金萬(wàn)重屬于西人,憤于肅宗的昏暗,于是作《謝氏南征記》加以影射,用以諷諫。”廢掉仁顯王妃五年后即1694年,肅宗幡然悔悟,“又將閔氏復(fù)位,并把張氏降為禧嬪。”“據(jù)傳肅宗而后廢張氏,復(fù)立閔氏,是受了這本書(shū)的影響。”直到肅宗二十七年(1701年)仁顯王后閔氏離世,肅宗發(fā)現(xiàn)心有不甘的張禧嬪意圖重返王妃之位曾詛咒閔氏短命,于是下旨賜死張氏,此時(shí)南人黨潰敗,西人黨重起。金萬(wàn)重沒(méi)能等到這一天,他在1689年南人黨全盛時(shí)第二次被流放后,于1692年死于流放地南海,他既沒(méi)有等到仁顯王后被重立為王妃,更沒(méi)有看到張禧嬪被賜死的結(jié)局,但他的作品精準(zhǔn)地預(yù)示了這一切。在此,我們暫且不去討論肅宗的悔悟是否與讀到這本小說(shuō)有關(guān)系,但金萬(wàn)重的確是與王妃廢立相關(guān)聯(lián)的黨爭(zhēng)的親歷者和受害者,他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基本是真實(shí)可信的——《謝氏南征記》是金萬(wàn)重有意撰寫(xiě)的勸諫之作,既然如此,《謝氏南征記》敘事策略就值得深究,其高超的敘事藝術(shù)造就了小說(shuō)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和卓越的表現(xiàn)力,在當(dāng)時(shí)和后世受到讀者的喜愛(ài),本論擬就《謝氏南征記》的敘事藝術(shù)做深入的分析。
1 背景設(shè)置的隱喻意義
這樣一部現(xiàn)實(shí)感較強(qiáng)、主觀上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十分明顯的小說(shuō),其背景的設(shè)置就顯得非常重要。從現(xiàn)實(shí)角度看,稍有不慎,作品非但不會(huì)起到預(yù)期的勸諫效果,反而會(huì)給作者招來(lái)殺身之禍;從藝術(shù)的角度看,背景和人物同等重要,在作品的感染力方面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謝氏南征記》將小說(shuō)的背景設(shè)置在中國(guó)明朝世宗時(shí)期,是作者匠心所運(yùn),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義。
1.1 有效地避禍
作者分明是指涉本國(guó)現(xiàn)實(shí),卻往往將背景設(shè)置為別的國(guó)家,這樣的情況在中外文學(xué)史上都不少見(jiàn),而且這并不影響作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如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哈姆萊特》的背景是丹麥,這個(gè)憂郁王子在劇中身份是丹麥王子,但絲毫不會(huì)影響讀者對(duì)作品的理解,讀者會(huì)知曉莎士比亞在劇中要反映的是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英國(guó)人文主義者的矛盾與困境,與丹麥沒(méi)什么關(guān)系。背景設(shè)置在另外一個(gè)國(guó)度只是作者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而已。
《謝氏南征記》中,背景的設(shè)置首先出于避禍。如上文所述,金萬(wàn)重作為西人黨,在肅宗王寵愛(ài)南人黨支持的張禧嬪、廢掉仁顯王妃后,西人黨失勢(shì)的現(xiàn)實(shí)境遇下寫(xiě)作的這部小說(shuō)。一方面為仁顯王妃鳴不平,因一方面希望喚醒肅宗王,意識(shí)到朝廷黨爭(zhēng)與后宮寵辱關(guān)系密切。此時(shí),金萬(wàn)重正在因?yàn)辄h派之爭(zhēng)而罹難,被流放中,從作者的現(xiàn)實(shí)處境來(lái)講,需要避禍,將故事發(fā)生的背景設(shè)置在別國(guó)就顯得十分必要了。作者用發(fā)生在明世宗時(shí)期一個(gè)貴族家庭中的故事和官員在朝廷中經(jīng)歷的黨派爭(zhēng)斗影射朝鮮肅宗時(shí)期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于作者心目中的指定讀者——肅宗本人,影射總是比直言容易接受,對(duì)于作者,用一個(gè)中國(guó)的故事隱喻比直接議論當(dāng)朝事件要安全得多。
1.2 加強(qiáng)藝術(shù)真實(shí)
金萬(wàn)重如果僅僅是出于避禍的考慮,他可以將背景設(shè)置在中國(guó)或其他國(guó)家的任何一個(gè)時(shí)期,但事實(shí)并非如此。金萬(wàn)重是個(gè)官員,更是個(gè)小說(shuō)家。他要讓自己的故事真實(shí)可信,小說(shuō)的具體背景就不能隨便安排,明世宗時(shí)期是作者縝密思考后設(shè)置的背景。
《謝氏南征記》是以小妾迫害正妻為主線,同時(shí)牽扯朝廷中黨派斗爭(zhēng),針對(duì)的就是朝鮮肅宗王廢立王妃,從而造成黨派爭(zhēng)斗加劇的現(xiàn)實(shí)狀況。小說(shuō)中最重要的形象毋庸置疑是謝貞玉,可謂天下第一賢婦,突出謝貞玉這一特點(diǎn)需要與之相對(duì)的反面形象,就是劉延壽的小妾喬彩鸞,但作者對(duì)這個(gè)反面形象沒(méi)有做扁平化、簡(jiǎn)單化的處理,而是將其塑造成了骨肉豐滿、性格鮮明的形象。她容貌秀麗、善于彈唱,很有心計(jì),性格殘忍,為達(dá)目的不擇手段,甚至采取了一些怪異的法術(shù),如當(dāng)她得知身懷女胎時(shí),她請(qǐng)了有奇妙法術(shù)的李十娘用符箓和怪方將女胎變?yōu)槟刑ィ瑧烟ナ潞螽a(chǎn)下一個(gè)“眉清目秀、氣膚如玉”的男兒,才使得一家人如獲至寶,命名為“掌珠”,取掌上明珠之意,從而堅(jiān)固地樹(shù)立了自己在劉家的地位,也為隨后因謝夫人勸慰她勿唱流俗艷曲懷恨在心,在丈夫面前花言巧語(yǔ)陷害夫人打下了基礎(chǔ)。謝夫人不久也有了身孕,生一男子,名麟兒,喬彩鸞感到不安,再次求助李十娘,學(xué)到了用木人蠱惑丈夫的法術(shù),使得丈夫精神恍惚,沉溺于喬氏一人。
一般情況下,借助法術(shù),變女為男,迷亂丈夫心智,這是令人吃驚和難以置信的。金萬(wàn)重的高明之處就在于背景的選擇——明世宗時(shí)期。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號(hào)嘉靖,在位長(zhǎng)達(dá)45年(1521-1566在位),早期勵(lì)精圖治,后期崇信道教,癡迷于煉丹,荒誕不經(jīng),導(dǎo)致宮女反抗引發(fā) “壬寅宮變”。上行下效,小說(shuō)選擇在這樣一位崇奉道教的皇帝任內(nèi),為喬彩鸞種種荒誕行徑和李十娘的怪誕法術(shù)提供了一個(gè)大背景。
嘉靖帝因?yàn)榘V迷于道教,所以重用善寫(xiě)青詞的嚴(yán)嵩,這位“青詞宰相”結(jié)私營(yíng)黨、鏟除異己,擅權(quán)多年,在小說(shuō)中對(duì)此也有描寫(xiě),劉延壽的父親就是與嚴(yán)崇 (嚴(yán)嵩)不和而辭官的,劉延壽家里的無(wú)行門(mén)客董清為陷害主人投靠了嚴(yán)崇,在嚴(yán)崇失寵后被處以斬行。中國(guó)名垂青史的一代清官海瑞,為了勸諫追求長(zhǎng)生、走火入魔的嘉靖帝做了必死的準(zhǔn)備,直言死諫,對(duì)此在小說(shuō)中也有所表現(xiàn),小說(shuō)描寫(xiě)嚴(yán)崇倒臺(tái)后,嘉靖帝重用海瑞“為都御史,翰林學(xué)士劉延壽為吏部侍郎”。小說(shuō)就是這樣虛實(shí)結(jié)合,將虛構(gòu)的人物、事件放置在真實(shí)的歷史時(shí)空中,家庭中的善惡、朝堂上的忠奸通過(guò)栩栩如生的人物、生動(dòng)曲折的情節(jié)展現(xiàn)出來(lái),恰當(dāng)真實(shí)的歷史背景使得虛構(gòu)的藝術(shù)變得真實(shí)可感。
1.3 重視接受效果——忠言也需順耳
小說(shuō)中的丈夫劉延壽影射的就是肅宗本人,“為尊者諱”是儒家文化的傳統(tǒng),在小說(shuō)中謝貞玉所遭受的所有磨難都是奸妾所害,而劉延壽是因?yàn)楸粏滩墅[的木人法術(shù)迷惑了心智,是被蒙蔽者,是受害者,似乎對(duì)妻子謝貞玉對(duì)兒子麟兒的不幸經(jīng)歷沒(méi)有任何責(zé)任,事實(shí)上作為一家之主,沒(méi)有責(zé)任是不可能的,對(duì)劉延壽的赦免和他所負(fù)責(zé)任的規(guī)避,本質(zhì)上是對(duì)在廢立王妃事件中肅宗國(guó)王的免責(zé),對(duì)高高在上的國(guó)王只能警醒,不宜譴責(zé),采取這樣的立場(chǎng),《謝氏南征記》的“目標(biāo)讀者”——肅宗國(guó)王,被勸諫的可能性就會(huì)大大增強(qiáng)。在這一點(diǎn)上,金萬(wàn)重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其意識(shí)相當(dāng)明確,《謝氏南征記》是供人欣賞、輕松品讀的小說(shuō),不是上奏朝廷的書(shū)、表,希望國(guó)王回心轉(zhuǎn)意,需要用可感的藝術(shù)形象,而不是堂堂的大道理、逆耳的忠言。
2 敘事場(chǎng)景的反諷效果
在敘事作品中,場(chǎng)景往往具有特定的含義。比如戲劇、小說(shuō)中的花園場(chǎng)景,特別是在姹紫嫣紅的春天,花園往往與青春萌動(dòng)、溫馨相愛(ài)、繁華熱烈等美好的情愫相聯(lián)系,一般而言在此空間中發(fā)生的故事與場(chǎng)景營(yíng)造的整體氛圍是和諧美好的。但是,在《謝氏南征記》中,作者在常見(jiàn)的敘事場(chǎng)景中展示了不同尋常的內(nèi)容,寓言性地表明家族的被破壞、家庭成員的離散、家門(mén)的不幸,充斥著反常、不安、陰謀、動(dòng)蕩,家庭已不再是給家庭成員以安全與庇護(hù)的溫暖家園,由此造成了強(qiáng)烈的反諷效果。
2.1 花園場(chǎng)景
花園場(chǎng)景是古代家族小說(shuō)中的重要場(chǎng)景,貴族家庭中的花園,春日融融,品茗賞花,妻妾共享,何等風(fēng)雅!這一場(chǎng)景本應(yīng)是以春和景明的自然風(fēng)光預(yù)示妻妾和睦、家庭昌盛的天倫盛景。但在《謝氏南征記》中,花園場(chǎng)景卻上演了妻妾沖突,為家族的災(zāi)變埋下伏筆。在小說(shuō)第二回,當(dāng)時(shí)正值暮春,劉家花園百花爭(zhēng)艷,花香襲人,紅花綠柳,一派繁華景象,劉家正室謝夫人看到春光喜人,于是來(lái)到自家花園賞花,在如火如荼、熱烈春光的映襯下,謝夫人更顯得幽靜賢淑,人與自然動(dòng)靜相宜,表現(xiàn)的是夫人“宜室宜家”的品行,小妾喬彩鸞生下兒子掌珠不久,也來(lái)游園,興致高時(shí),吟唱起來(lái),雖聲情并茂,婉轉(zhuǎn)動(dòng)人,但從儒家的“樂(lè)教”觀念來(lái)看,卻是淫邪之曲,謝夫人好言相勸,喬氏聽(tīng)后陽(yáng)奉陰違,表面應(yīng)承,內(nèi)心懷恨,當(dāng)晚便在丈夫面前編造謊言、顛倒黑白地誣陷了夫人,由此播下不和的種子,引發(fā)了家族災(zāi)難。
自然中原本祥和的春天花園場(chǎng)景,卻暗藏殺機(jī),和美的春光下邪惡的暗流正在洶涌,醞釀著一場(chǎng)災(zāi)變。以至于全知視角的敘事者預(yù)言:“殆極將成大禍之根底。”花園場(chǎng)景的反常運(yùn)用給小說(shuō)打下陰郁的基調(diào),對(duì)小說(shuō)的敘事起到了預(yù)敘的效果。
2.2 百子堂
儒家強(qiáng)調(diào)百行孝為先,無(wú)后是大不孝。 對(duì)于封建社會(huì)中貴族家庭中的夫人而言,婚后無(wú)子,是否為丈夫納妾本來(lái)是一個(gè)十分棘手的問(wèn)題,但是謝貞玉作為賢婦,她要為夫家的昌盛著想,要為劉家延續(xù)子嗣后代,所以主動(dòng)為丈夫選擇了姿色秀麗、女工出眾的女子喬彩鸞為妾。喬氏進(jìn)入劉家后,一家之主劉延壽將喬氏所居之地命名為“百子堂”,直白地表明了劉家納妾的目的。百子堂在敘事中前后出現(xiàn)了三次,第一次出現(xiàn)是在第二回,一筆帶過(guò),第二次出現(xiàn)在第三回中,側(cè)面介紹了百子堂位于距離劉家內(nèi)府較遠(yuǎn)的地方,是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空間,第三次出現(xiàn)是在第八回,百子堂的荒誕感在第三次出現(xiàn)時(shí)凸顯出來(lái)。
從情節(jié)發(fā)展來(lái)看,喬氏在百子堂的生活貫穿了家族中的妻妾爭(zhēng)斗。在百子堂,她生了兒子掌珠,顧名思義,可以看出這孩子在劉家人心目中的位置。喬氏借助這個(gè)孩子地位得以提升,她又故意設(shè)計(jì)構(gòu)陷夫人,當(dāng)她的貼身侍女臘梅將掌珠殺死并嫁禍夫人后,喬氏終于如愿以償,謝夫人蒙冤被逐出家門(mén),經(jīng)歷著九死一生的顛沛流離之時(shí),喬氏作為劉延壽的正妻,登堂入室,入住了劉家內(nèi)府,掌執(zhí)著劉家內(nèi)務(wù)。但是喬氏卻完全沒(méi)有擔(dān)負(fù)起對(duì)家族的責(zé)任,甚至沒(méi)有對(duì)丈夫的忠誠(chéng)。在丈夫在朝廷值夜時(shí)公然與為她出謀劃策的董清在百子堂私會(huì),“家人無(wú)不切齒,而畏死含默矣。”終于被丈夫發(fā)現(xiàn)。百子堂最初承載著劉家綿延子嗣、光大門(mén)庭的愿望而設(shè),掌珠生于此死于此,掌珠死后,喬氏又在此生下了與情夫私通的孩子,原本出于儒家正統(tǒng)觀念為傳宗接代而設(shè)的百子堂,此時(shí)卻成為道德淪喪、傷風(fēng)敗俗、使家族蒙羞之地,目的與效果南轅北轍,百子堂成為一個(gè)反諷性的場(chǎng)景,體現(xiàn)了強(qiáng)烈的悖謬感和荒誕感。
2.3 書(shū)房
在古代貴族家庭中,書(shū)房是男主人的專屬領(lǐng)地,是公務(wù)在家庭中的延伸,與朝廷上的謹(jǐn)言慎行相比,在這里人的精神相對(duì)松弛,可以更多地流露對(duì)朝廷事務(wù)的真實(shí)想法和主張,具有一定的隱秘性和安全感,是相對(duì)私密的場(chǎng)所,設(shè)在家庭中的書(shū)房理應(yīng)給主人以安全和庇護(hù)。但是,在小說(shuō)中,劉延壽發(fā)現(xiàn)喬彩鸞在百子堂過(guò)夜后,喬彩鸞心有不安,借丈夫上朝之際,將董清招到書(shū)房,商議對(duì)策。對(duì)書(shū)房而言,這兩個(gè)人不是主人,是闖入者,他們的擅入,改變了書(shū)房場(chǎng)景的本源意義,充滿不祥之感。他們?cè)谶@里發(fā)現(xiàn)了劉延壽議論朝廷、譏諷嚴(yán)崇、針砭嘉靖帝求仙之事的詩(shī)作,董清拿著這“反詩(shī)”投靠奸相,去賣(mài)主求榮了。這場(chǎng)在書(shū)房醞釀的陰謀,造成書(shū)房的主人一家之主劉延壽的貶謫、流放,劉家再次蒙難。書(shū)房在這里,與本來(lái)具有的功能徹底背離,成為又一個(gè)充滿反諷的場(chǎng)景。
3 敘事空間的拓展與意義
既然家園不再溫馨祥和,離家出走倒是可能帶來(lái)轉(zhuǎn)機(jī),在《謝氏南征記》中展示了家庭之外的敘事空間,在敘事空間的轉(zhuǎn)換與拓展中表現(xiàn)了小說(shuō)曲折豐富的情節(jié),主要人物在現(xiàn)實(shí)空間中的遭厄和非現(xiàn)實(shí)空間的獲救,險(xiǎn)象環(huán)生卻又化險(xiǎn)為夷,他們絕處逢生的遭遇和跌宕起伏的命運(yùn)更容引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并喚起讀者的深切同情,較之于一般的家族小說(shuō)因其敘事空間的拓展,大大增強(qiáng)了小說(shuō)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3.1 荒山墳塋
謝貞玉被休后,被逐出劉家,令人稱奇的是她沒(méi)有回娘家,而是住進(jìn)了劉家祖墳旁的幾間草屋中,她的弟弟得知后專程來(lái)接她,但是被她謝絕了。因“敏于女工,造衣織布,以資生業(yè)。且有妝奩中些少首飾,賣(mài)珠繼糧,賴而不饑。”她如此堅(jiān)持,一是相信自己的清白,仍以劉家子?jì)D自居,丈夫不容她,她相信祖先會(huì)保佑她的;二來(lái)堅(jiān)信丈夫只是一時(shí)被蒙蔽,終會(huì)悔悟。所以在荒山中艱難度日,但是她的心思,喬氏和董清也明了,所以他們要斷了謝貞玉的念想,勾結(jié)董清的心腹冷振,一面由董清模仿劉延壽姑母杜夫人(因兒子在長(zhǎng)沙任職,她隨居長(zhǎng)沙)的筆跡,請(qǐng)謝貞玉前往長(zhǎng)沙,一面讓冷振在路上強(qiáng)娶謝貞玉,壞了謝貞玉的清白,也就斷了她與劉家的聯(lián)系。危難之際,謝貞玉似乎只有死路一條,但作者將筆蕩開(kāi),進(jìn)入另一維度的敘事空間。
3.2 異度空間
文本中三次對(duì)異度空間的敘事,都是以夢(mèng)的形式展示的,這表明作者具有自覺(jué)的創(chuàng)作意識(shí)——非現(xiàn)實(shí)因素要通過(guò)夢(mèng)境來(lái)展示。
《謝氏南征記》中通過(guò)三次不同的完整敘事展示了亡靈所在的冥界和神靈所處的神界。第一次是在幽暗的冥界。謝貞玉在劉家墳塋旁苦熬,卻意外接到姑母杜夫人的書(shū)信,信以為真,處境極為險(xiǎn)惡,早已過(guò)世的公婆告訴謝貞玉,因?yàn)椤坝拿髀肥猓坏孟嗑取保崾舅龝?shū)信有詐,墳塋草房不可久居,指示她南行五千里方能避難,并預(yù)言“茲后六年六月望日,泊舟于白萍洲而濟(jì)人,銘心不忘焉!”并且指明這里是九泉之下的非現(xiàn)實(shí)空間:“此地泉下,賢婦不可久留,須速歸去”。這段描寫(xiě)文字不長(zhǎng),意義非凡,死者為生者指明一條生路,從結(jié)構(gòu)上勾連了前后共四回書(shū)(第六回到第十回),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謝貞玉和劉延壽的兩次救助。在第十回,謝貞玉計(jì)算日期,到白萍洲,恰逢劉延壽被董清追殺,于是用一葉輕舟帶劉延壽脫離了險(xiǎn)境。第二次是來(lái)自娥皇女瑛等仙界神靈的解救。謝貞玉在乳母和丫鬟的陪伴下,歷盡艱辛來(lái)到長(zhǎng)沙,得知自己前來(lái)投奔的姑母杜夫人因兒子升遷成都知府,已經(jīng)隨遷了,可是錢(qián)財(cái)已盡,面對(duì)滔滔江水,謝貞玉再次陷入絕境,她決定投水自盡,剩下的有限的盤(pán)纏分給乳母和丫鬟,讓她們?nèi)ヌ由臍饨^之計(jì),小說(shuō)展示了一個(gè)神靈的世界,“高殿崔巍,廣庭肅肅,綴琉璃而蓋屋,綴白玉而為砌。燦爛炫耀,奪人耳目,可知其非煙火世界也。”正殿之上是娥皇、女英,兩側(cè)座上均是歷代賢婦烈女,娥皇禮遇謝貞玉并且預(yù)言南海觀音將會(huì)給她幫助。醒后依夢(mèng)中所見(jiàn)尋到黃陵廟,果然不久后有兩位女尼前來(lái)將謝貞玉接到“幽邃清凈,一塵不到”的佛門(mén)凈地水月庵。第三次是劉延壽到達(dá)被貶地,因瘴氣中毒,一病不起,生命垂危之際,有一位白衣夫人,攜壺而來(lái),表明壺中神水有療救瘴癘的奇效,神奇之處在于第二天竟然于平地之上出了一口清泉,劉延壽飲畢果然神清氣爽,瘴毒全消,劉延壽于是筑了一口井,造福于當(dāng)?shù)匕傩铡?/p>
夢(mèng)作為潛意識(shí)活動(dòng),可能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曲折反映,但不可能對(duì)現(xiàn)實(shí)發(fā)揮實(shí)際的作用,可是小說(shuō)中這三個(gè)夢(mèng)卻都介入了現(xiàn)實(shí)世界,異度空間中的鬼魂、神仙、菩薩等非現(xiàn)實(shí)力量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的受難者施行了拯救。這樣的想象與虛構(gòu)呈現(xiàn)出作者主觀意識(shí)和作品敘事者之間的矛盾,暴露了作者思想深處的困惑。孔子曰“勿語(yǔ)怪力亂神”,又曰“未知生,焉知死?”金萬(wàn)重作為儒門(mén)弟子是堅(jiān)持這一看法,但小說(shuō)中儒家君子、賢婦遭厄之際,對(duì)他們施以拯救的卻是與他們所信奉的儒家思想相抵牾的力量,反映了堅(jiān)持儒家道統(tǒng)的金萬(wàn)重在復(fù)雜矛盾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和險(xiǎn)象叢生的政治斗爭(zhēng)中,意識(shí)到他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在他受難時(shí)卻不能給他現(xiàn)實(shí)的救助,通過(guò)筆下異度空間的敘事,形象而深刻地表達(dá)了尊儒的知識(shí)分子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痛苦和矛盾,體現(xiàn)了儒家思想在社會(huì)矛盾和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無(wú)力和軟弱,使人們理解到在儒家正統(tǒng)之外,還應(yīng)該有更強(qiáng)大的力量承擔(dān)對(duì)儒家道統(tǒng)的補(bǔ)救。
《謝氏南征記》在朝鮮古典小說(shuō)中享有盛譽(yù),具有開(kāi)創(chuàng)之功,其敘事背景的異國(guó)設(shè)置、敘事場(chǎng)景的反諷性處理,敘事空間的虛實(shí)轉(zhuǎn)化等等敘事策略被后世小說(shuō)廣為借鑒,金萬(wàn)重在小說(shuō)敘事藝術(shù)方面的匠心獨(dú)運(yùn)在現(xiàn)實(shí)中成功“干預(yù)”了一代王室王后的廢立,在藝術(shù)領(lǐng)域,對(duì)朝鮮后世的小說(shuō)產(chǎn)生了久遠(yuǎn)的影響。
[1]孫萌.朝鮮家庭類(lèi)漢文小說(shuō)中的儒家倫理及其禮學(xué)背景——以《謝氏南征記》、《彰善感義錄》、《玉麟夢(mèng)》為中心[J].明清小說(shuō)研究,2016(3):205-217.
[2]周雪萍.韓國(guó)漢文小說(shuō)《謝氏南征記》研究[D].四川師范大學(xué),2016.
[3]景春婷.淺談《謝氏南征記》中的儒家思想[J].時(shí)代文學(xué)(下半月),2012(6):157-158.
[4]李寶龍.從神怪情節(jié)看韓國(guó)古代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因素——以《謝氏南征記》、《九云夢(mèng)》、《玉樓夢(mèng)》為例[J].延邊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5(3):37-41.
[5]韋旭升.談朝鮮古典小說(shuō) 《謝氏南征記》[J].國(guó)外文學(xué),1984(1):4-12.
I312
A
2096-4110(2017)03(b)-0031-05
李宏偉(1971-),女,山西侯馬人,文學(xué)博士,副教授,中國(guó)青年政治學(xué)院中文系任教,研究方向:比較文學(xué),中韓文學(xué)關(guān)系。
- 文化創(chuàng)新比較研究的其它文章
- 分析大學(xué)英語(yǔ)教學(xué)思辨能力培養(yǎng)模式構(gòu)建
- 高職院校跨境電商專業(yè)人才能力素質(zhì)模型研究
- 立體開(kāi)展共青團(tuán)工作對(duì)加強(qiáng)醫(yī)藥類(lèi)高校大學(xué)生人文思想建設(shè)的作用
- 淺析模具子系統(tǒng)制造實(shí)訓(xùn)課程的改進(jìn)措施
- 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翻轉(zhuǎn)課堂教學(xué)實(shí)踐
——以《建筑識(shí)圖與構(gòu)造》課程為例 - 高校管理會(huì)計(jì)體系的構(gòu)建與創(chuàng)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