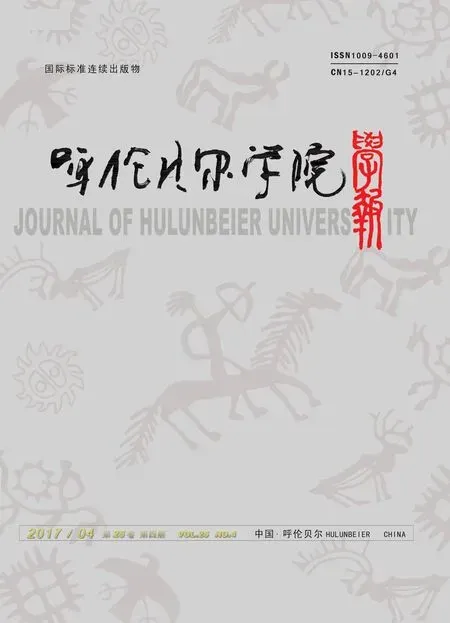論《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原始文化認同與現代性反思
王騰遠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 北京 100083)
一、對鄂溫克原始文化的認同
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分為“清晨”,“正午”,“黃昏”,“半個月亮”四個部分。如果將整部作品比作一首交響樂,“清晨”和“正午”無疑是充滿了抒情性和歌唱性的奏鳴曲,節奏輕快浪漫,作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來描述鄂溫克族人詩意的原始生活,來表達對于這種原始文化的認同感。
首先,在宗教信仰方面,鄂溫克人信仰薩滿教,這是一種以“萬物有靈”為思想核心的原始宗教。文本中多次提到鄂溫克人對自然的崇拜與敬畏。諸如,他們相信火中有神,因此“不能在火里吐痰,撒水,扔不干凈的東西”,被稱作“瑪魯王”的白色馴鹿不能隨意騎乘;樹有樹神,山有山神……鄂溫克先民在狩獵工具落后、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情況下生存艱難,對自然有著相當程度的依賴,因此對自然萬物既崇拜又敬畏。萬物有靈的意識,同時又是鄂溫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必備條件。這種敬畏又親密的關系使他們懂得感恩與節制。
“萬物有靈”同時又是鄂溫克人精神歸屬感的根據所在,自覺將自我歸入自然的一員,接受萬物平等。他們在山林中的生活寂靜,但并不寂寞。然而,在下山定居之后,那些遠離部族的年輕人從城市返回山中,竟會頓覺寂寞難耐,甚至無聊。這是喪失了與自然萬物的聯結,喪失原有靈性的表現。他們想方設法在原始文化中尋找精神的歸屬,使靈魂得到滋潤。由此可見現代人精神危機產生的原因之一便是與自然失去聯結。遲子建說:“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1]作者賦予萬物有靈的薩滿教浪漫的烏托邦色彩正是為了表達對于人與自然緊密聯結的原始文化的認同與向往。
其次,鄂溫克族人的性與愛單純美好。文本中講述了許許多多的愛情故事。林克與達瑪拉,伊萬與娜杰什卡,妮浩與魯尼,還有尼都薩滿的暗戀。不論是悲劇還是喜劇、幸福抑或不幸。這所有的愛與恨都如此強烈質直,不摻雜任何功利算計和心機的角逐,愛得熾熱也恨得入骨,這也是原始文化強大生命力的顯現。而現代人在絕大部分的情感中卻是行走在愛與恨之間廣闊的灰色地帶,這一地帶遍布著捆綁人靈魂的物欲色欲。文中多處性愛場面的描寫純凈又唯美。“希楞柱里也有風聲,風中夾雜著父親的喘息和母親的呢喃,這風聲是父親林克與母親達瑪拉制造的”,“那是最纏綿的一次親昵,也是最長久的一次親昵,我的身下是溫熱的堿土,上面是我愛的男人,而我愛的男人上面就是藍天”。原始世界里的性愛健康自然,沒有絲毫的猥褻,是在嚴苛的生存環境下對生命孕育的美好祝福。
最后,是鄂溫克原始文化中的生死觀。小說描寫了許多死亡:達西死于復仇,林克死于雷擊,達瑪拉死于舞蹈,金得死于愛情,果格力死于墜樹,瓦羅加死于熊的襲擊……“我已經說了太多死亡的故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亡。人們出生是大同小異的,死亡卻是各有各的走法。” 小說中除了作為敘述者的“我”,作者幾乎為每一個出場的人物都安排了死亡的結局,充滿了宿命的味道。他們出生,成長,經歷或長或短的人生之后又重歸自然。“ ‘靈魂不死’是薩滿教的核心觀念之一,按照薩滿教的靈魂觀,人死后靈魂各有歸宿,或升天或歸山或入地。”[2]這其中蘊含了鄂溫克族對生命的獨特認識:生命是神給予的,神靈有權決定何時將他們收回,他們平靜的接受宿命的安排。因此,鄂溫克族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表現出更大的堅強和坦然,悲而不傷。當外來的電影放映員感嘆:“你們這里真是世外桃源啊”,瓦羅加嘆了一口氣說:“哪里有什么世外桃源啊”。鄂溫克人也有自己的悲傷與憂愁,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不得不承受死亡突如其來的威脅與悲痛。悲痛之后,依然要充滿希望的面對生活,這是鄂溫克族人的堅韌之所在,也是”靈魂不滅”賜予他們對待生死坦然平和的態度。正如敘述者所說:“但我想生命就是這樣,有出生就有死亡,有憂愁就有喜悅,有葬禮也要有婚禮,不該有那么多忌諱。”
二、碰撞中的現代性反思與精神重建
庫柏在《發明原始社會》中說:“圖騰制構成理性主義的基礎神話,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象征的慣用詞,詩人們可以憑借他去追思一種更自然的時代,那時人的精神與自然和鳥獸同在,神話與詩性智慧也是普遍存在的,性欲本能不受禁止,這是人類學家的伊甸園;與之相對現代世界則是荒原。”[3]
小說中的鄂溫克族人是指馴鹿鄂溫克人,史稱“使鹿部”,“公元前兩千年居住在外貝加爾湖和貝加爾湖東北部的尼布楚河上游的山林苔原高地,18世紀遷至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大興安嶺,并從此世代生活在古老的原始森林中,被群山環抱,極少與外界接觸,較完整的保存了古老的生產生活方式。”[4]然而當小說中“黃昏”部分來臨時,伐木工進駐大興安嶺,從此山林的寂靜被撕開一個裂口,現代文明涌入,自由的游牧民族被迫下山定居。
當鄂溫克人離開世代生活的原始森林,來到荒原一樣的現代世界他們不得不面對理性的約束。在哈貝馬斯關于現代性的定義中,“理性稱為真理之源,價值之源,從而也成了現代性安身立命的根本。”[5]激流鄉的政治制度是理性,法律是理性,整齊劃一的鄉鎮街道是理性,對馴鹿的科學養殖方法是理性,看不到星星的四四方方的水泥房子是理性。海德格爾認為“人是被‘拋’到世界上的,是被一種存在的‘敞開狀態’中來,即身不由己的受到他所處的生存環境的擺布,人在這種敞開狀態中,在被擺布、被制約的條件下展開自己生存的可能性,展開自己生存的內容。”[6]鄂溫克人被拋到以理性為根本的現代社會中不得不經受本我被壓抑、本真生活淪落所造成的分裂。
當這支古老的民族真正開始在現代社會中生存時,原始文化與現代文明發生劇烈碰撞。這種碰撞,猶如歷史模型,清晰地再現了現代文明將人異化的歷史進程。“原始人猶如兒童,原始人是未被馴化的我們自己,我們本我的力量,力比多的,非理性的,暴力的,危險的,原始人是神秘者,與自然融合是自然之和諧的一部分;原始人是自由的,生活在最低‘文化水準’,而我們則處于‘高水準’”[7]。他們代表了本我,不受壓抑與復雜的欲望驅使,自由而舒展的本真存在,他們雖處于文化上的“低水準”,但并未遭遇精神貧瘠所帶來的虛空,不知寂寞為何物。當人有一天感覺到寂寞的時候,便是被放逐,再也無可復歸自然的世界。然而當他們脫離了原始傳統被放逐到現代社會,收走了獵槍,離開了森林與馴鹿,曾經根植于內心的精神依托被迅速瓦解,靈魂被抽空。
文本中,沙合力受利益的驅使販賣黑材被關進了監獄;索瑪耐不住寂寞,到處找男人幽會,去激流鄉做流產,“這個民族面臨著退化的命運”。2008年一份關于鄂溫克族生存現狀的調查顯示純正血統的鄂溫克狩獵民族僅剩60人,酗酒過度是導致鄂溫克人數驟減的原因之一。“酒賜予了鄂溫克族勇氣和力量,但過量飲酒卻在侵蝕這個民族的骨髓和靈魂,一份研究數據顯示,實行定居四十年來,因酗酒導致直接死亡14人,因酗酒后失控而導致直接間接死亡共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數是青壯年,目前獵民總數才 230多人”[8]。按照鄂溫克人的說法,沒有獵槍他們可以喝酒,但沒有了馴鹿就真的一無所有了。獵槍與馴鹿代表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原始文化元素,更是一種與自然的聯結所在,失去了獵槍與馴鹿意味著失去了與自然的聯結。當精神被放逐,被有形的鄉鎮與無形的體制壓抑之后,他們只能選擇酗酒來進行自我麻痹。
這種碰撞與分裂在伊蓮娜身上體現的最為明顯。她是鄂溫克族從大山里走出來的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后留在城市里做美術編輯,后來成為了一名畫家。在城市生活中經歷過兩次失敗的婚姻,酗酒,反反復復來往于城市與山林。“在山里住上一兩個月就會心煩意亂,嫌山里的生活太寂寞,跟外界聯系不方便,待煩了就返回城市”,然而過不了多久她又會回來,厭惡城市的喧鬧浮躁,更向往山中的清流小溪、星星、花朵。但過不了一個月,又會因為沒有電影院、沒有書店、沒有酒館、沒有電話而煩躁并酗酒,內心矛盾痛苦。比起一般下山定居的鄂溫克獵民及后代,受過高等教育在現代城市生活多年的伊蓮娜無疑具有更多現代人的特質。但她又是在鄂溫克部落中長大,鄂溫克族原始文化賦予她原初的記憶,并扎根于意識深處,構成了對世界最初的認知。海德格爾將現代性歸結為“源于存在的遺忘而導致的由于技術統治人而不是人統治技術,所造成的‘無家可歸’的狀態。”[9]。電影院、書店、酒館、電話,這些現代社會中出現的技術和設施占據了伊蓮娜大部分的精神世界。失去它們就會感到寂寞,深陷其中又感到虛無。伊蓮娜在城市與山林之間反復來往,正是現代人“無家可歸”的生存狀態的具體表現。
越來越多的現代人憑借原始文化的力量“去解脫沉陷于消費社會物質主義枷鎖中不能自救的靈魂,抵抗由現代性負面效應所導致的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機。”[10]伊蓮娜于痛苦和矛盾中終于辭了職帶著行李回到山中。“她說她厭倦了工作,厭倦了城市,厭倦了男人。她說她已經徹底領悟,讓人不厭倦的只有馴鹿、樹木、河流、月亮和清風”。她最終選擇了回到自己的部落,作為靈魂的救度。伊蓮娜的真實原型是一位叫做柳芭的鄂溫克族畫家。在2000年一個關于柳芭的訪談中,主持人問道她離開森林在城市生活這么多年,覺得自己變化最大的是哪個方面?柳芭說:“變得虛偽”。柳芭所說的虛偽或許不僅僅是指人際關系,更包含著對待生存的態度上。工業社會將越來越多的現代人異化為機器,而原始文化中則包含著順應人性的存在方式。浮夸的現代生活讓她離本真的自我越來越遠。伊蓮娜在自己的部落中結束了掙扎,重獲平靜,選擇了與自己的人性不相違的自由而本真的存在。這樣的情節安排是作者暗示的一條艱難而自然的回歸之路。
[1]遲子建,胡殷紅.人類文明進程的尷尬、悲哀與無奈——與遲子建談長篇新作《額爾古納河右岸》[J].藝術廣角,2006(02).
[2]曾娟.淺析《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薩滿文化[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5).
[3]庫博.發明原始社會(第 121頁).轉引自葉舒憲.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46.
[4]卡麗娜. 馴鹿鄂溫克人文化研究[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11.
[5][6]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7]葉舒憲.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59.
[8]廖杰華,顧展旭.純正血統鄂溫克狩獵民族僅剩 60人[N].廣州日報,2008-11-5.
[9]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79.
[10]葉舒憲.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