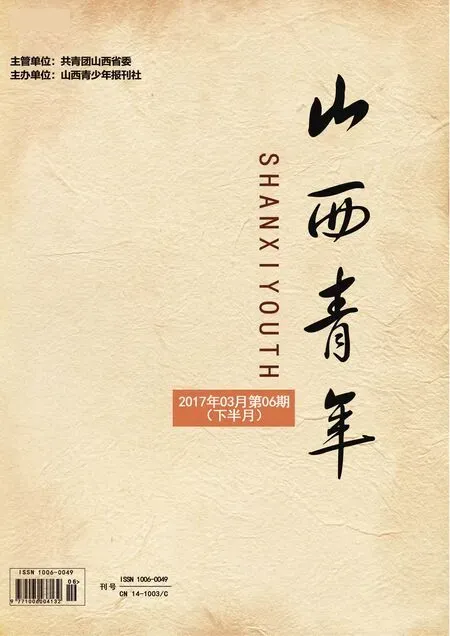網絡環境下人肉搜索行為的刑法規制
張 晨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32
網絡環境下人肉搜索行為的刑法規制
張 晨*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32
進入互聯網時代,網絡一方面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與繁榮,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個人的信息也暴露于“原野”,任何信息都成為戳手可得的產品,任何人在網絡上的留痕(包括涉密與非涉密)都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條增設了關于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條款,但是回避了“人肉搜索”這種同樣有可能泄漏個人信息,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是否將“人肉搜索”行為通過刑法規制,目前學理界都有不同的呼聲。
網絡環境;人肉搜索;刑法規制
一、問題提出
近年來,網絡上人肉搜索事件頻頻發生,從2001年的微軟陳某某事件到2006年2月的"虐貓事件",再到已經結束但媒體尚在討論的黃某某嫖娼事件,人肉搜索嚴重威脅著我們生活的正常秩序。在黃海波嫖娼事件,人肉搜索不僅把黃海波生活經歷、母子關系,女方當事人的年齡、性別等基本信息公示于眾,而且還將女當事人是雙性人的絕密隱私咆哮在網絡之中,最后女方母親請求媒體包容女方當事人,請求沈陽人原諒、接納女方當事人,本是一起普普通通的賣淫嫖娼違法案例,人肉搜索使得當事人承受了不對稱的責任,當事人的個人信息安全深受侵害,無節制地、超越底線地人肉搜索行為有著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實踐呼吁刑法規制人肉搜索行為。
二、理論爭鳴
一派主張人肉搜索行為不易犯罪化。首先人肉搜索入刑一定程度上是對《憲法》言論自由權的侵害。隨著時代的進步,“網絡已經成為公民發表自由言論和實施輿論監督權利的重要平臺,是最平民化、最應該受到保護的民眾表達權的公眾意見表達形式。”“人肉搜索”的廣泛應用拓展了言論自由的表現形式,強化了輿論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監督強度,盲目地將“人肉搜索”行為規定為犯罪,將嚴重影響社會公眾輿論監督的積極性,有礙民主政治深入人心;第二,人肉搜索入刑不符合刑法謙抑性原則,“人肉搜索”所搜索的信息多來源網上已經公開的信息,對于這些信息,是當事人在自覺不自覺的過程中公開,法律尚未有禁止公民獲取他人信息的規定,所以網絡推手搜集信息、整合信息、傳播信息并沒有違法,不存在侵犯當事人的隱私權,刑法更不應該過度干涉,對于行為人采用非法手段獲取他人隱私信息行為,則可能存在侵犯他人隱私或損害他人名譽的情形,但若此時的行為未達到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即使要追究責任,也不必納入刑法規制范疇。民事法律制度可以解決上述爭議問題,如可以通過侵害人承擔賠償損失、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恢復受害人的權利原始狀態,換言之,網絡侵權屬于民事問題,達不到刑法規定的標準,刑法規制,破壞法律的梯度性。第三,人肉搜索入刑,實踐操作難度大。目前“人肉搜索”的主體主要包括搜索發起人、提供真實信息的人、提供虛假信息的人、對被搜索人進行評論的人、純粹看熱鬧跟帖的人、網絡服務商等。可見,“人肉搜索”參與者眾多,在具體案件中,如果主張“人肉搜索”構成犯罪,如果要追究刑事責任,在實踐中會遇到沒有侵害人或者侵害人眾多的情形,網絡本身具有虛擬性,在當前尚未實行實名制的背景下,主體責任的追究不具有可行性,另外在追責過程中,證
據定性與固化存在一些技術性弊端,這與刑法所要求的法定刑、明確性、確定性不符。“人肉搜索”入罪的客體是隱私權,而我國民事法律尚未確立隱私權是法律具體權利。公民的隱私權和界限沒有法律上的依據,在對社會不良現象進行批評和侵犯他人的隱私權上沒有存在一個平衡點。因此,隱私權立法的缺失使得“人肉搜索”入罪缺乏成熟的前提條件。而在這些難題與障礙還未解決的情況下,主張“人肉搜索”入罪勢必會加大刑法規制的實現成本。
另一派觀點認為,一些人肉搜索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已經達到了刑法規制的資格線,同時目前的民事、行政責任的追究對嚴重的人肉搜索行為沒有起到震懾作用。從理論上看,支持人肉搜索行為犯罪化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從法益保護來看,達到刑法規制的“質”的要求,“人肉搜索”行為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自然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權,侵犯或者威脅刑法保護的法益,將其入罪化是刑法保護法益的需要;二是從應受刑罰處罰“量”的角度來論證,如果將犯罪的本質認為是應受刑罰處罰的社會危害性,造成嚴重后果的人肉搜索行為的危害性足以要求國家運用刑罰權來介入,我國刑罰兼具報應與預防犯罪功能,將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后果的人肉搜索行為入刑,既是對惡行為進行懲罰的表現,也是預防類似違法行為發生的重要手段。侵權人肉搜索行為入刑之后,行為者再藐視法律進行違法人肉搜索,在主觀故意的追求下發生,具有可責性,另外,雖然網絡沒有完全實名制,但是通過網絡的IP地址完全可以確定行為主體,人肉搜索行為犯罪在實踐中有著可操作性。
三、人肉搜索行為的刑法規制的進路
全國人大法工委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說明》中所言,增設關于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條款是由于“有些部門及部分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當前存在一些國家機關單位員工(如電信、金融等存儲個人隱私的單位員工)在工作過程中為了謀取私利,將其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非法泄露的情形,這些行為已經對個人的隱私權造成侵害,應當進行刑法打擊”。從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來看,這種行為有著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對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刑法已經對其規制。修正案回避了一個更為敏感的問題,那就是同樣有可能對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和個人隱私構成嚴重威脅的“人肉搜索”行為。草案審議之時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朱志剛的一番言論更是將已經被媒體炒的沸沸揚揚的“人肉搜索”推到了風口浪尖,“人肉搜索、網上通緝,泄露家庭住址、個人電話、公民姓名等基本信息,同樣對公民基本權益造成侵害,這些行為對當事人帶來的損害不亞于出售公民個人信息帶來的侵害,因此建議將人肉搜索行為在刑法中予以規范”。法律是一門實踐性的學科,刑法同樣也不例外,對于社會中層出不窮、爭議極大、可能對公民人身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的“人肉搜索”行為,刑法不能置身事外,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個人信息保護的條款,這對于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無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然而修正案并沒有將“人肉搜索”行為納入其中,但這并不意味著給我們對這種行為的討論劃分了禁區,相反我們更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明晰法理、為司法實踐和將來的立法提供理論參考,以更好地保護公民的權利。本著這種態度,本文對“人肉搜索”行為進行研究,提出將其入罪化的理由,并解析相關的法律問題,以刑法學理論對現實社會問題做出回應,提出系統的解決方案,并最終通過人肉搜索的研究探尋在我國建立合理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有著深刻的實踐與理論意義。
本文認為,一種行為是否入刑,應該嚴格按照立法原則或者“犯罪化”原理來界定,當前我國刑法立法原則是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框架之內框定,這就造成了刑法具有謙虛性同時具有擴張性,否定人肉搜索行為入刑的理由主要是從注釋刑法學刑法謙抑性角度來論證,鑒于目前沒有形成完備的行為犯罪化的規制機制,僅僅從理論上論證人肉搜索行為不易入刑,顯得空洞無力。主張人肉搜索行為入刑的觀點,單憑人肉搜索行為負面影響來界定其社會危害性,沒有考量到人肉索索行為本質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盲目的將其全部犯罪化,顯得偏頗。
一種行為是否犯罪化,應該從犯罪行為的本質來界定,馬克昌老師在《犯罪通論》中提出犯罪是應當受懲罰并且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顧名思義,行為的入刑必須符合兩個特征,一是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二是行為應當懲罰性,具體到人肉搜索行為是否需要刑法規制,首先要探討的是人肉搜索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行為可懲罰性,社會的危害性應當主要是從行為的后果來看,行為的可罰性應當主要從行為主體的心理態度來看,本文認為有些人肉搜索行為沒有道德底線,嚴重的侵犯個體的個人信息,對他人的隱私權、信息安全造成破壞,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侵害行為本身具有刑法可罰性。第二,刑法作為社會穩定的最后一道防線,人肉搜索行為的入刑應當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刑法的謙抑性包含了刑法的最后性、補充性、寬容性、經濟性,當前民事、行政法律的對人肉搜索行為規制效果并不令人滿意,這從反面說明個別人肉搜索行為入刑有著現實的必要性。第三,《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條在第二百五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這一增設的法律條文衍生出兩個罪名,一個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犯罪主體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主體,一個是非法獲取公民信息罪,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在一條法律出現兩類不同的犯罪主體,法律條文的款項之間存在沖突,除此之外,從立法者的意圖來看,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應當為非法獲取公民信息罪下游罪名,即獲取在先,出售、非法提供在后,非法獲取罪名的行為主體為一般主體,出售、非法提供更應該是一般主體,而非現行法律中的特殊主體,明顯不符合刑法的統一性原則。本文認為應該將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罪的犯罪主體改為一般主體,修改之后,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人肉搜索行為當然的囊括在其中,刑法253條第三款就可以規制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人肉搜索行為。
[1]葉慧娟.刑法框架下見危不助犯罪化的具體考量.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8(2).
[2]何澤宏,佘小松.價格違法行為犯罪化問題研究.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4).
[3]王永華.道德和法律視角下"人肉搜素"的雙重性及其健康發展.法制與社會,2009(2).
[4]劉理想.解析“人肉搜索”中的法律問題.消費導刊,2008(11).
[5]蘇志娟.對“人肉搜索”下的法律思索.法制與社會,2009.11.
[6]郭理蓉.寬嚴相濟視野下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從最高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標準>談起.河北法學,2008(4).
張晨(1986-),女,華東政法大學。
D
A
1006-0049-(2017)06-02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