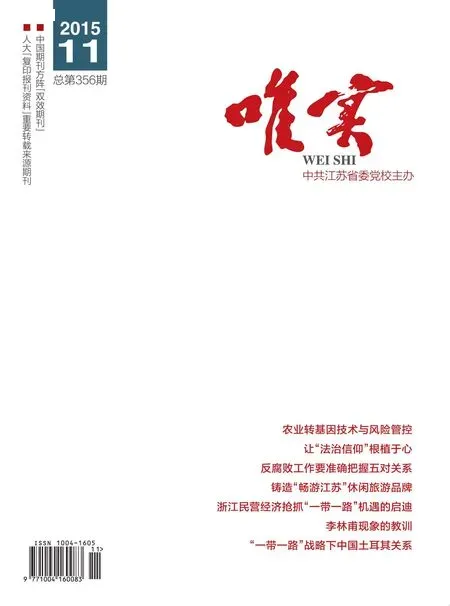從仁義之辯看先秦儒家義戰思想
鄭嵐公
“仁義”是先秦儒家重要的價值觀念,深深影響了先秦儒家的戰爭觀,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先秦儒家義戰思想,在我國傳統軍事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基于仁義觀的兩種戰爭表現形式
仁義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引發的仁戰思想與義戰思想便成了我國先秦早期的兩種主要戰爭形式:一種以“仁”為出發點,主張戰之有仁,有戰必仁;另一種以“義”為出發點,主張戰之有義,非義不戰。但是隨著周朝的解體與分封制的瓦解,基于血緣的“仁戰”思想因脫離戰爭實際而被“義戰”取代。
仁戰基于“仁”。先秦的仁,根據最新發現的考古研究成果(《郭店楚墓竹簡》),為“從身從心”,這與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或從千心”的引錄非常吻合,疑“千”字即為“身”①。從這點看,凸顯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是先秦“仁”的主要思想基礎,故“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直”。但是發自內心真實感情的“直”還必須有著“禮”的約束,否則,“直而無禮則絞”。二者的辯證關系為:直是禮的基礎,禮是直的保障,故“人而不仁,如禮何?”因此,孔子之“仁”既有發自內心的真實感情,同時又要受到“禮”的約束。這就促成了歷史上一例典型的“仁戰”案例:宋襄公與楚人戰于泓的案例。《春秋左傳》記載如下:“冬,十一月,己已,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后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基于“仁”的考量,將心比心,故“不重傷,不擒二毛”;基于“禮”的要求,故“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評:“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體現出當時仍有從血緣禮節的立場對待戰爭的風氣。這種風氣恰是基于這樣的背景:周王朝下面的諸侯互為親戚,相互攻伐仍然本著血緣情感,主張有禮有節,君子為戰;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利益鴻溝的擴大、戰爭實踐的豐富,仁戰已無法滿足當時的歷史要求,自然被建立在“利”基礎上的“義戰”所取代。所以代表新生階級利益的大臣子魚論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子魚代表了新生階級的利益,主張戰爭不必講仁,講仁就不必戰爭。其出發點脫離了情感的“仁”,而建立在戰爭的“利”上,認為仁愛與戰爭價值觀互相背離,用“仁”來指導戰爭必然會淪為迂腐,導致戰敗。
那什么是“義”呢?義者,宜也。從字源學看,“宜”的甲骨文是一塊放著食物的砧板,這本身就蘊含著“殺”和“祭祀”的含義。《尚書》中有“宜于社”、“宜于京”即為明證。隸書中的“義”字則更為形象:上面是一只“羊”,下面是一個“我”——“我”是一個人背著武器“戈”;“羊”則直關祭祀。《孟子》中就曾記載過用羊換牛做犧牲的例子。因此,“義”字更是透露出了“殺氣”與“祭祀”的含義。但是古人的“殺”與“祭祀”都有嚴格的時間規定,因此“宜”又被賦予了“合宜”的含義。所以,當今涉及“義”的成語時也多半和“暴力”與“制約”有關,如大義滅親、伸張正義、見義勇為、舍身取義、背信棄義等。這種約束不同于仁之基于血緣,而是一種基于利益的外在約束。因此,“義”強調“利”。所以,“義子”不同于“兒子”,需要道德或是協議來交換利益,建立約束;“義齒”也不同于“牙齒”,需要格外的愛護與清洗;“義戰”不同于仁戰,在強調“暴力”的同時,也強調“利益”的制約。
所以,義戰基于利,是建立在利益基礎上一種因契約破壞而發生的政治關系。需要注意的是,此處之利益,有時指大多數國家的利益,有時指統治階級的利益,有時又指百姓的利益。如何在這些不同利益之間求得平衡,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成為了先秦儒家考量“義戰”內容特質的關鍵。
二、先秦儒家義戰思想的內容特質
如何在戰爭與國利之間求得平衡,是義戰要解決的問題。先秦儒家義戰思想給出的解答就是:“循正道而戰。”循正道之戰就是義戰。因為循于正道,不怕失去民心;循于正道,不怕沒有援助;循于正道,不怕步入歧途;循于正道,滄桑也是光明。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循得正道自然能夠平衡利益。因此,循于正道的義戰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尊王攘夷”是“義”,它解答了戰爭的合法性問題。
先秦儒家認為,國家是保障人民利益的根本。國家穩定需要人民既各安其命,又各安其名,按照自己的名分履行自己的職責。不按名分就會出亂。因此,君主要有君主的樣子,臣民要有臣民的樣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分,國家機器才能更好地運轉。同樣,戰爭權亦如此。只有一個國家的國君才有戰爭權,否則,國家就會陷入戰亂。在孟子看來,“春秋無義戰”是名分的混亂而導致的戰爭權旁落——戰爭發動者不具備發動戰爭的權力,導致戰亂頻繁,國家分裂。儒家以君臣有義的價值觀為出發點,提倡周天子的權威。孔孟的義戰首先是以發動戰爭的身份是否合法為標準,孟子言:“春秋無義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孟子·盡心下》)。朱熹評注為:“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于義而許之者。”“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之所以無義戰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論語·季氏篇》)《公羊傳》中亦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減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公羊傳·僖公元年》)這就是戰爭合法性的一個標準。在周代鼎盛之時,凡諸侯相互侵伐,必由天子出征阻止,當天子無力征伐時,則由強而有力的諸侯來擔負阻止諸侯間相伐取地的責任,這是“義戰”的前提。先秦儒家以周天子的至尊地位來評價春秋戰爭的標準,體現出對于戰爭發動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訴求。
攘,為排斥、抵制,夷為外族;攘夷就是抵御侵略。抵御侵略是無可厚非的“義戰”。《春秋》說:“大一統之義,明華夷之別。”這就使得“攘夷”成為戰爭原因的正當性。管子最早提出“攘夷”。管子相桓公曾伐戎救燕(《春秋左傳·莊公三十年》),伐狄救邢(《春秋左傳·閔公元年》)、伐狄救衛(《春秋左傳·僖公二年》),代周天子伐楚(《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都體現出管子對于戰爭合理性的一種表述。孔子對管仲因攘夷而發動戰爭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說“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齊軍。孔子曰:‘義也。”可見,孔子也認為一個人領軍打仗,保衛國家就是義舉。“攘夷”體現的就是這種自衛且求生存的“義”——我們不侵略他國,但是他國若侵略我國,就一定要反擊。
綜上所述,在孔孟看來,國家領土的完整與國君權力的保障是義戰的重要標準,它對外體現了國家利益至上的觀點,對內體現了國家權力合法合理的觀點。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君主履行權力與承擔義務,才能保障百姓的利益在國家的庇護下得到保障,二者的利益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不論是尊王還是攘夷體現的都是“義舉”,戰爭必須發動!
其次,“慎戰”是“義”,它解答了對待戰爭態度的問題。
義戰不是濫戰,這主要體現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即為“慎戰”。《論語·述而》記載:“子之所慎,齊,戰,疾。”在孔子看來,戰爭和齋戒、疾病一樣,都是要慎重對待的,不可輕舉妄動,草率應備。孔子認為,戰爭關系國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要精心謀劃準備,全面布局思考,不能憑借一時沖動,草率出兵,否則,就是陷國君于不義,陷百姓于危難。《論語·述而》記載了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對話,子路曰:“子行三軍,其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憾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充分表明了孔子對待戰爭的慎重態度。
慎戰的思想還體現在先秦儒家“仁武相兼”的思想上。《史記》記載,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正因為文事與武事兼備,才使得魯定公與齊侯的“夾谷之會”化險為夷,兩國沒有貿然出戰,既維護了國家利益,也保護了百姓的利益。
慎戰的思想還體現在“軍旅有禮,武功成也”(《禮記·仲尼燕居》)的“以禮治軍”思想。在孔子看來,對待戰爭要慎重,對待治軍也要慎重,不能一味提倡軍不怕死的思想,而是要合乎禮節,講究信義,以義為上。孔子說:“君子以義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如果不用有一定約束的禮義來治軍,那么還沒有打仗,軍隊就亂了,義戰便無從談起。這就是周易師卦“師出以律”的道理,孔子晚年喜得易,可見這一觀點也是孔子所推崇的。
再次,“在乎一民”是“義”,它解決了民心所向的問題。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決定了其義戰思想的百姓立場。先秦儒家認為推翻暴君的戰爭也是義戰。《孟子·盡心下》記載,齊宣王請孟子評定“湯放桀,武王伐紂”這種“臣弒其君”的行為是否正當,孟子答稱:“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看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統治者德政不施,傷天害民,理應誅伐,推翻他們的戰爭亦為義戰。百姓反對的戰爭一定不是義戰,百姓愿意參與的戰爭一定是義戰。古代土地與國家完全依附,百姓依附于土地,喪失了國土,也就意味著喪失了基本生活權利。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有著維護自己生存權的能力,“教民以戰”是一個方面。在孔子看來,以民為本才能得到百姓的擁護,通過戰爭來保障基本生活權利,也恰恰是最大的以民為本,這樣的戰爭就體現出對百姓的“義”,戰爭也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因此,在先秦儒家看來,義戰還必須是民心一致的戰爭。百姓自愿參與的戰爭一定能夠獲勝,但是百姓反對的戰爭一定不是義戰。孔子提倡“教民以戰”,就是要百姓具備戰爭的能力和本領,知曉戰爭,萬不得已時可以通過戰爭保護國家和自己的利益,所以“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可見,孔子主張的“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教民習武,既是從愛民保民的立場出發,也是從百姓意愿作為考量,能否獲得民心的要件。這正是孔子“以生道使民”、“雖死而不怨殺者”的義戰思想。
荀子的觀點則更進一步表達了民心一致的重要性,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荀子·議兵》認為,人是萬物中最貴者,“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為天下貴也”。如何“一民”,即如何使人心一致呢?荀子認為重在“善附民”,即善于使人民歸附。荀子說:“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荀子·議兵》)并以湯滅桀、武王滅紂之例說明湯武因獲得人民支持而獲勝。荀子說:“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所以義戰必以愛民、仁義為本,這亦是戰爭的目的。
最后,崇尚武德是“義”,它解決了官兵修養的問題。
狹義的武德指武將的德行修養,廣義的武德指所有參與戰爭的主體的修養德性。義戰亦有對戰爭德性的要求,武將是戰爭的主體,因此,武將也必須將暴力與道德相結合。一方面通過德行來維護軍心;另一方面,通過對官兵德行的約束,達到對戰爭整體風格的約束。被孔子贊譽的《周易·師》卦認為:“師,貞丈人,吉,無咎。”就是主張軍隊必須要有有德行的長者來指揮。在儒家看來,在一定程度上,戰爭的風格是由武將及其下屬官兵決定的。有德行的武將,能指揮一場收獲民心的戰爭;無德行的武將,卻只能導致“至今野火野昏黑,天陰鬼哭聲嘈嘈”的人間慘劇,收獲春秋筆法的歷史判決。因此,武將必須具備一定的道德修養,這不僅關乎軍隊人心向背,更是關乎整個戰爭的走勢。
先秦儒家不提倡悍將、梟雄也是基于這個原因,只有將德兼備,才能成為儒家推崇的“儒將”。從這一方面看,先秦儒家義戰思想的修養要求其實是將道德范型融入軍事素養。另一方面看,既然強調義戰,那么戰爭的主體也必須擔負起這樣的操守——戰場的官兵除了“執干戈以衛社稷”外,還要具備“殺身成仁”、“舍身取義”、“明辨是非”的道德修養。先秦儒家主張軍人不僅要精通純粹的兵法,更要具備一定的德行。這就解釋了為何一些精通于戰爭的名將,如白起、韓信、高先芝等,軍事才能、成就卓越,反而不受儒家推崇,而郭子儀、岳飛、戚繼光等人卻大獲推崇的原因。因此,從傳統的標準看,儒帥或儒將是對一名將領最高的評價。只有武將具備德性,軍隊才能得到較好的控制,戰爭才能沿著正道運行,對國力與人性的損害才能降到最低。
三、先秦儒家義戰思想的現實價值
中國先秦儒家義戰思想是中國傳統的軍事智慧,它不僅是中國古代發動戰爭的一種判斷標準,更是一種敢于戰爭的底氣。直到今天,這種不畏于戰、不避于戰的底氣依然流淌在中華民族的血脈與骨氣之中。雖然義戰思想在當今波譎詭異的世界風云中很難完全地被履行,但是其理論價值與戰斗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尤其是當代軍人承載與弘揚的。
先秦儒家義戰思想有利于維護聯合國權威,維護國際政治新秩序。縱觀現代世界戰爭,戰爭的性質常因發動國種族、宗教、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和國家意志等諸多因素而得到不同的詮釋,因此,什么是正義之戰,什么是不義之戰,因立場不同而各有主張。如日本對待侵華戰爭的態度,還有1991年1月的海灣戰爭、1994年12月的車臣戰爭、1999年7月的科索沃戰爭、1999年的第二次車臣戰爭、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戰爭,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戰爭,都因各個國家的立場不同存在著對戰爭正義性的爭論。可以說,在國際戰爭上,正義的標準是難以界定的,沒有衡量標準,難免就會造成戰爭的肆意和正義的缺失。先秦儒家義戰思想倡導在統一模式和框架下發動戰爭,從而最大限度地規避了這種矛盾。如今,這種統一模式和框架就是在聯合國框架下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雖然聯合國不是獨立的國家,但是《聯合國憲章》規定了成員國的責任、權利和義務,以及處理國際關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基本原則及方法,代表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遵守《聯合國憲章》、維護聯合國威信就是當今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與方式。我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直倡導在聯合國框架下處理國際爭端,一直反對未經聯合國授權的任何戰爭,這是我國的傳統,也是當今時代世界發展的需要。我國會一直遵守這樣的傳統,維護聯合國權威,視任何一個違背聯合國決議、規避聯合國決議的戰爭為不義。
先秦儒家義戰思想有利于團結民心共同對敵。義戰不同于其他戰爭如武裝暴動、民眾起義叛亂或恐怖主義活動之處,在于民心與戰爭的一致性、人民參與與戰爭方式的整體性。因此,民心相背不僅是一個國家在和平時期能否治理好的標準,更是在戰爭時期能否勝利的關鍵。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說的就是“人和”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一場戰爭究竟應不應該打,能否打勝,人心是否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標準。人心不和的戰爭一定不會勝利,人心和的戰爭一定能夠勝利,萬不得已要戰爭的話,必須團結民心一致對敵,這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人民戰爭思想。人民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和指導戰爭的最高原則是戰爭發生的“正義性”、參與戰爭的“群眾性”,以及戰爭實踐的“整體性”,戰爭是否為義是群眾性與整體性的前提與基礎。只有利用全人民的力量打擊侵略者,保衛國家、民族,我們在戰爭中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一場戰爭能否凝聚人心,也是我們考量能不能打、是不是義戰的標準。倘若戰爭能夠凝聚民心,那么這場戰爭的性質也多半得到了倫理的支撐。
先秦儒家義戰思想有利于減少戰爭、維護和平。先秦儒家義戰思想基于“以民為本”與“慎戰”思想的儒家觀念,強調一切戰爭都要考慮到人民的利益與訴求,強調“不得已而用之”,并逐漸演變為出于自衛且求生存的戰爭動因。這種理論有助于減少濫戰、暴戰發生的可能,將戰爭發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以提倡義戰,不是提倡戰爭,更不是提倡濫戰,而是提倡一種道義之戰與理性之戰。倘若是義戰,我們要敢于承擔,敢于發動;同樣,如果不是義戰,也要敢于熄戰,敢于撤戰。
當然,我們在評價傳統義戰積極價值的時候,也應該看到義戰的局限性。單一的政治社會或可建立一個共識系統,斷定道德標準,但是兩個不同的政治社會就難以建立共識系統。所以現今戰爭動因紛繁復雜,紛擾不斷,很難完全以“一義”的標準一概而論。就如同墨子所謂的“一人一義”局勢,各個政治社會都以其價值為正義,這樣一來戰爭所遭遇的情況,就不單只是“知仁由義”的標準所能解決的。很有可能囿于這種情況,而導致義戰的討論范疇往往只限于哲理的思辨,難以落實為具體實踐。在當今國際環境下,作為大國,需要我們弘揚與承載的恰恰是義戰的這種精神與底氣,敢打義戰,能打義戰,并在堅持秉承的同時,為建立一個更好的國際秩序而努力。正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泱泱大國,何懼何畏;正道而行,道同而合;義薄國際,兼濟天下。在當今復雜的國際環境下,我們應該高揚傳統義戰思想!
〔本文系2013年國家社科青年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與踐行研究”(13KS052)、“傳統核心價值觀與當代軍人精神培育”階段性研究成果;2016年南京政治學院“十三五”規劃課題“培養‘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研究”(16ZY02-08)、“傳統軍事文化與核心價值觀”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
責任編輯: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