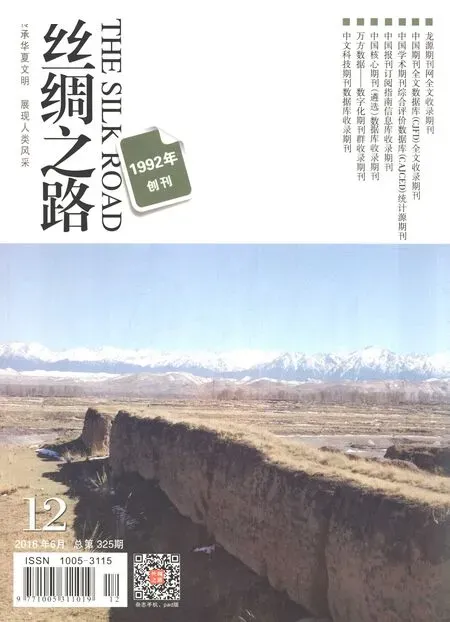淺析安娜與愛瑪形象的異同及其悲劇命運
王琴
(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甘肅蘭州730070)
?
淺析安娜與愛瑪形象的異同及其悲劇命運
王琴
(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甘肅蘭州730070)
[摘要]安娜與愛瑪是托爾斯泰小說和福樓拜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她們雖出身不同,個性不一,但悲劇命運極為相似。貴族小姐和永遠“生活在別處”的女版“堂吉訶德”都以自殺方式結束了生命。本文將對比二人形象,并以此為切入點,從金錢和情欲入手探究人物悲劇命運的成因。
[關鍵詞]安娜;愛瑪;女性形象;悲劇成因
一、安娜與愛瑪形象的異同
安娜是俄國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愛瑪是法國著名小說家福樓拜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作為男性作家視角觀照下的女性典型,安娜和愛瑪二人形象的相似性主要表現為:一方面,她們都是悲劇命運漩渦中掙扎的女性。有人說:“悲劇正是由于善良的人犯了錯誤而產生的。”①由姑母一手包辦婚姻的貴族小姐安娜奢談愛情。俄國貴族家庭典型的婚姻觀是以家庭和物質利益的考慮為先,孩子間的愛慕在其次。嫁給卡列寧后的安娜,生命活力一度被窒息,與情人四目相遇注定人生的交集,為愛傾其所有卻終被愚弄,走投無路選擇自殺。愛瑪似安娜般無婚姻自主權。在法國,“父母安排的婚姻”向來比任何國家都多,婚約只是岳父與女婿的協定,愛瑪是父親的私有財產。她婚后沉溺于浪漫小說,如同沉溺于“騎士小說”的堂吉訶德,在一種“病態的不幸”中,她所有幻想的本質是滿足“自戀”的傾向,現實生活與內心需求的巨大心理落差亟需彌補。另一方面,兩人都曾嘗試愛自己的丈夫。安娜了解丈夫并欣賞、順從于他,“他畢竟是一個好人:忠實,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業方面非常卓越”。②這種自我安慰是她盡力維持夫妻關系的努力,忍受不了就將愛轉移到兒子身上,也是19世紀俄國貴族家庭的普遍現象。對丈夫缺乏深厚感情的婦女往往會在對兒子的愛中找到“平衡點”并得以補償。愛瑪與情人糾纏后也有過“懺悔之心”,她攛掇丈夫做畸形足手術,手術后的晚餐時間兩人談天說地,度過了愉快的夜晚。
安娜與愛瑪的形象除相似性外又屬于兩個世界,代表不同的生活方式:首先,身份迥異、地位懸殊的她們體現出貴婦與平民世界的撞擊。仰仗貴族和丈夫的官僚身份,安娜似天鵝般徜徉在光芒畢露的上流圈子。農家之女愛瑪婚后只是中產階級家庭主婦,過著平淡無華的生活,遠遠張望著風光奢靡的貴族生活。其次,兩人所受教育不同。安娜一般留在家中接受母親和家庭教師的教導,貴族教育注定談吐舉止不俗。愛瑪接受的卻是修道院式教育。當時法國一般女子沒有機會接受正式學校教育,一些貴族家庭就把女兒送入修道院。愛瑪父親本著攀高的目的送她去學習貴族小姐的談吐,從此給其人生埋下“不幸”的種子。再次,兩人背叛丈夫后的行為選擇不同。安娜背叛丈夫后對此事未隱瞞多久。“我聽著你說話,但是我心里卻在想著他。我愛他,我是他的情婦,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惡你……隨便你怎樣處置我吧”。③極度畏懼丈夫,卻一心追求光明正大的愛情,絕不配合丈夫再演虛偽至極的家庭戲。愛瑪則從頭至尾向丈夫隱瞞了偷情的事實,包法利直至其服毒自盡后整理遺物時才意外發現情書,知曉一切……坦誠與欺騙,安娜出走后想和情人結婚,作為東正教徒,她可離婚,但由丈夫一方決定。愛瑪從未有再婚的想法,因天主教禁止離婚,并且“在法國,妻子通奸至今仍然是犯罪”。④最后,兩人宗教“約束作用大小”和“悔罪感輕重”不同。“基督教認為,人的情欲本身即罪惡。放縱情欲,靈魂就會墮落,就會遠離上帝而受到上帝的懲罰”。⑤女子偷情即罪惡的一大表現,人有“趨罪為惡”的傾向,負罪之感和悔罪之心尤為重要。安娜從未懷疑把她培養成人的宗教,婚姻是上帝的安排和旨意,背叛丈夫就是犯罪,總覺自己是壞女人的她羞恥心常常涌上心頭,發自內心的懺悔明顯而深重。愛瑪并不信教,在修道院就經常違反院規,后有人勸其信教便接受了。雖如此,悔罪感也不比安娜強烈,相反她考慮問題簡單,更注重對當下生活的把握和享受,偶有嘗試愛丈夫的努力,但很快拋開“自責之心”重新享受生活的歡娛。這或許是因東正教宗教氣息比天主教更濃厚,因而兩人接受的宗教教育對自身內化程度的差別也較大。
二、自殺悲劇的成因
“性格與環境的尖銳沖突”導致兩人的毀滅是一般性看法。劉俐俐分析《竹林中》時認為,武士自殺是因其憤懣無處發泄只好殺死自己。安娜和愛瑪的自殺行為中或許也帶有這種因素,但筆者將從金錢和情欲入手分析悲劇成因。
首先,必須了解她們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圣經》中亞當取肋骨造女人的故事寓意是:男人主宰世界,女人是其附屬品。19世紀20年代俄法兩國工業革命相繼興起,“18世紀60年代發軔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婦女命運也隨之發生巨大的浮沉變化,中產階級的婦女從社會生產和勞動領域離開,成為囿限在家庭天地里的‘家庭天使',而廣大的下層婦女為了彌補家庭生計的不足,或受雇于工廠……”⑥由此可知,工業化時期,中產階級婦女脫離社會生產和勞動而獲得解放。以前家庭是生活和勞動場所,如今其活動范圍僅限于家庭,“家庭天使”是19世紀西方中產階級男子對婦女的要求。愛瑪之家庭雖不可與安娜的貴族—官僚家庭相提并論,也算得上中產階級家庭。因19世紀的中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有別于貴族,因為他們沒有可炫耀的家世;他們也不同于平民,因為他們擁有財產,有一定的社會地位”。⑦鄉村醫生包法利有一定財產收入和社會地位,愛瑪只需相夫教子、洗衣做飯,又雇得起仆人,也只做女主人的管理工作。在典型“男主外、女主內”生活模式中,由于女性無獨立經濟能力,家庭從屬地位越來越突出。包法利雖膽小本分,看似強勢的愛瑪卻依舊是丈夫的附屬品。法國直至1942年頒布的法律依舊要求妻子服從丈夫。婚姻大事尚不能做主,何況嫁為人婦,父權、夫權制的色彩一直濃厚。生活中丈夫供給一切開銷但收入有限,愛瑪不斷買下奢侈品,偷藏且寫信討要診費,甚至借高利貸。一時奢華享受的背后潛藏致命危機,8000法郎債務無力償還,苦苦求人卻頻遭戲辱,無顏面對丈夫,精神恍惚之下吞下砒霜。安娜也深陷金錢的悲劇。耗在上流社會的交際費用從何而來?19世紀俄國貴族家庭內部關系是家長擁有無限統治權,妻子必須服從丈夫。然而隨啟蒙思想的盛行,婦女解放問題慢慢引起社會關注,貴族家庭內部關系趨于人道主義。但宗法制—專制關系的殘余依存,男人統治女人是其基礎。對安娜而言,卡列寧作為大家長擁有無限權力,主宰家庭一切財產和成員的命運,她必須依附于丈夫。了解人類基本婚姻形式(群婚制、對偶婚制、專偶制)就會發現,專偶制之所以產生,一重要原因即大量財富集中于男子之手,女性受經濟壓迫,丈夫對妻子有絕對控制權。安娜和丈夫即組建了“專偶制個體家庭”,丈夫是資產者,她相當于無產階級,家務勞動因不具社會公共性而沒有報酬。丈夫按時給她生活費,這種屈從一直延續至其出軌后。坦白私情后,她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丈夫手中,卡列寧諷刺她拋棄丈夫和兒子卻還吃著丈夫的面包,她只能默默忍受。卡列寧給她自由卻堅持要生活在一起,安娜無比痛苦,生孩子病危挺過來時斷然拒絕離婚,選擇了另一個男人,又成為其奴隸和附屬品。甜蜜期過后預感自己將被拋棄的命運又無家可歸,失去唯一物質依靠時死成了唯一出路。
其次,單純扮演男性情欲發泄者和愛情不幸犧牲品角色的兩人也必將毀滅。愛情是建立家庭的基礎,她們被迫接受的都是無愛的婚姻。父權制世界里,她們沒有話語權,只是代表被動性的他者,反抗并抓住婚外愛情要付出沉重代價。西方社會本就尊崇個人本位,愛情至高無上,為了它,她們不惜背負罪人包袱。愛瑪被人指指點點,但依舊沉醉于此。被羅道爾弗欺騙后大病一場,痊愈后又和賴昂重續舊情,徹底放縱情欲。可憐她被逼向絕路前懇求過一生付出愛情的兩個男人卻無濟于事,表面雖是金錢將其毀滅,但她臨死前痛苦的是愛情。相比愛瑪,安娜為愛情付出了更多。放棄兒子、名節、家庭及富裕生活即需莫大的勇氣。她的愛情源于邂逅,猝不及防、極具魅力,使其心醉神迷且不由自主地委身于另一個男子,置名節于不顧而私奔,也比愛瑪的婚外情更轟轟烈烈。她敢于沖破謊言的羅網,明確自己的地位,但和愛瑪的負情故事無異。弗倫斯基一度迷戀其美貌,從未在精神世界真正理解過她,他不理解她不舍兒子并害怕被拋棄的心情等,有的只是征服女人的自豪感。兩人的愛都表現出極強控制欲。安娜想讓情人以她為中心,愛瑪曾在潛意識里動過監視賴昂的念頭。拜倫說愛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種消遣,卻是女人的生活本身。安娜的癡情變成最后的瘋狂,私奔后重組幸福家庭的美夢被情人花心的本質擊碎,激烈爭吵引發精神恍惚和強烈報復欲望燃起的瘋狂狀態將其吞噬。當火車軋過冰冷的心時,她終于松了一口氣,一切的罪惡都已過去,只愿上帝饒恕。
此外,兩人都有性的壓抑。19世紀法國中產階級男子的普遍看法是:順從丈夫的性要求是妻子的責任,要求分享丈夫愉悅感的女人就非好女人,愛瑪婚姻生活的壓抑在所難免。安娜接受過嚴格宗教教育,丈夫又是虔誠的基督徒,兩性關系嚴守為生殖的原則,性快樂體驗被剝奪,因此都在偷情生活中享受性自由,出軌是對男性壓迫秩序的挑戰,也體現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欲望”(不論自身或他者的物欲情欲)是毀滅她們的兇手。女性悲劇背后的婚姻制度和男人所負擔的夫婦經濟責任等使夫妻平等成為幻想,男人在工作中實現自我,已婚女性卻往往在千篇一律的家務中消耗生命,陷入孤獨和無意義。兩性要獲得解放,正如波伏娃所言:要允許女性自立,讓其在這個世界上有事可做。
[注釋]
①⑤曹順慶:《中外比較文論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45頁、第71頁。
②③〔俄〕列夫·托爾斯泰著,周揚,謝素臺譯:《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頁、第278頁。
④〔法〕波伏瓦著,鄭克魯譯:《第二性》,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頁。
⑥⑦裔昭印等著:《西方婦女史》,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23頁、第328頁。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12-00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