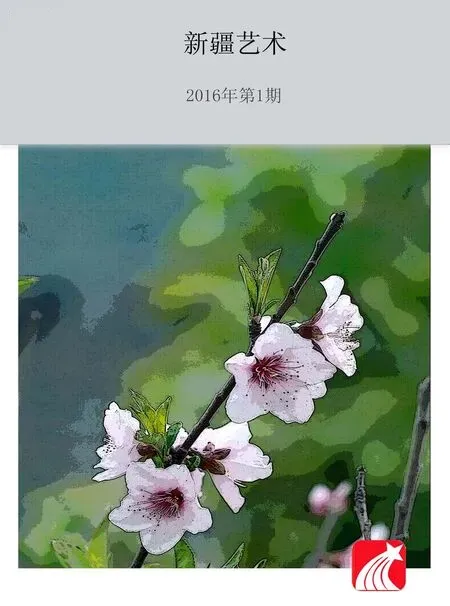韓樂然:新疆美術(shù)的先驅(qū)
□孤島

韓樂然自畫像(水彩,1940年)
生于東北畫西北的朝鮮族藝術(shù)家
2015年5月,我從新疆到澳門參加本人策展、澳門基金會(huì)主辦的“天山來客——阿童牧絲路風(fēng)情畫展”期間,負(fù)責(zé)接待的梁華全先生是一位“新疆迷”,他告知我:澳門基金會(huì)曾聯(lián)合中國美術(shù)館,在2007年舉辦過一位新疆現(xiàn)代美術(shù)史上的大畫家韓樂然的個(gè)人畫展,并說韓樂然是一個(gè)極具傳奇色彩的藝術(shù)家,至今在韓國還有不小的影響,2005年,韓國為表彰韓樂然所做的貢獻(xiàn),盧武鉉總統(tǒng)授予他大總統(tǒng)表彰,并由韓國國立美術(shù)館和中國美術(shù)館在韓國首爾舉辦了“民族魂·藝術(shù)情中國朝鮮族畫家韓樂然藝術(shù)展”。他還給我贈(zèng)送了一本畫冊(cè)《熱血丹心鑄畫魂——韓樂然繪畫作品集》,帶回新疆。于是,我在去年6月熟悉司徒喬之外,又開始品味研磨又一位與新疆緣分很深的新疆現(xiàn)代藝術(shù)家韓樂然……如今,他被這樣評(píng)價(jià)著:杰出的朝鮮族政治活動(dòng)家、人民藝術(shù)家。
政治和藝術(shù),兩個(gè)截然不同的詞,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火與水一樣,如今卻結(jié)合到韓樂然身上。
韓樂然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藝術(shù)家;
韓樂然是一位出生東北、死于大西北的朝鮮族畫家;

雨中天池之一(水彩,1946年)
韓樂然是一位將軍畫家,1939年,就曾由中共派到國民黨戰(zhàn)地黨政委員會(huì)任少將指導(dǎo)員,在抗日前線和兩黨合作抗日地區(qū)作抗日宣傳動(dòng)員。
韓樂然是一位從事革命地下工作的畫家,因此坐過監(jiān)獄,出獄后卻最終沒能夠活到1949年共和國成立。
韓樂然是第一位用油畫和水彩摹畫新疆克孜爾千佛洞壁畫、敦煌莫高窟壁畫的藝術(shù)家,是對(duì)克孜爾千佛洞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編號(hào)、整理、記錄的第一人,為中國藝術(shù)史做出了獨(dú)特的貢獻(xiàn)。
韓樂然是大畫家黃胄的美術(shù)啟蒙老師之一,作為革命青年的黃胄1943年有緣陪同到西安舉辦畫展的韓樂然,從寶雞到華山,再到八百里秦川寫生,最早從韓樂然那兒汲取寫生的技法和力量,后來,黃胄沿著他的足跡也來到新疆寫生、畫素描,并最終憑借新疆題材的畫作一舉成名。
著名評(píng)論家、中國美術(shù)館研究員劉曦林在《1930至1970年代新疆題材繪畫概述》這篇文章中,回憶了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到新疆寫生創(chuàng)作的諸位藝術(shù)家:魯少飛、沈逸千、司徒喬、韓樂然、黎雄才、趙望云等,他們是新疆美術(shù)史上第一批藝術(shù)家,給新疆種下了藝術(shù)的種子……他們成為新疆風(fēng)情寫生的先遣者,同時(shí)成為新疆現(xiàn)代人物繪畫的啟蒙者、播種者與拓荒者。他們不僅為我們留下了當(dāng)年生活的真實(shí)寫照,同時(shí)研究并再次發(fā)現(xiàn)了新疆風(fēng)景、風(fēng)情之美,使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重新躍然丹青。
其中,魯少飛、司徒喬、韓樂然三人不僅是新疆油畫、水彩的開拓者,也是中國從事油畫、水彩畫創(chuàng)作的先驅(qū)。魯少飛是韓樂然在劉海粟創(chuàng)辦的上海美專的同學(xué),于1915年至1918年在《新疆日?qǐng)?bào)》工作三年,為該報(bào)畫報(bào)頭、刊頭漫畫,曾全家五口都遷來新疆生活,1939年任上海《救亡漫畫》主編。1995年才去世的魯少飛這樣評(píng)價(jià)英年早逝的韓樂然:“革命的忠貞者,藝術(shù)的真誠者,兩者有機(jī)結(jié)合,品位真摯高境。”而弟子黃胄則題寫“光風(fēng)霽月、熱血丹心”來贊美老師韓樂然。就是一代佛學(xué)大師、書法家趙樸初也這樣評(píng)價(jià)韓樂然:“畫中史乘,筆底莊嚴(yán)”。

寶雞公路橋(水彩,1945年)

維吾爾族烤馕(水彩,1946年)
以藝術(shù)身份投身革命,以革命的激情繪畫
韓樂然,原名韓光宇,1898年生于吉林省延吉縣龍井村(今屬龍井市)一個(gè)貧苦的朝鮮族農(nóng)民家庭。他自幼酷愛圖畫課,放學(xué)后除了做家務(wù)就是畫畫,畫自己身邊熟悉的同學(xué)、老師、牛車、小河、花草、大樹……這些與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與自然,都是他描畫的對(duì)象。父親見他太著迷,轉(zhuǎn)喜為憂:“將來畫畫不能出莊稼,不能當(dāng)飯吃。”就不許他畫了。韓樂然便偷偷跑到村外的墳地里,在沙土地上涂畫。
1920年,韓樂然如愿以償?shù)乜既雱⒑K趧?chuàng)辦的上海美術(shù)專科學(xué)校學(xué)習(xí),1923年他到蘇州一帶旅行寫生,憑借寫生作品在上海舉辦了第一次個(gè)人畫展,不久組織成立了青年畫會(huì),開展進(jìn)步的美術(shù)活動(dòng)。
1921年冬,他有幸拜會(huì)了孫中山先生,心中萌發(fā)了最初的革命理想。
1923年,韓樂然在上海美專畢業(yè),并通過蔡和森等人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開始以藝術(shù)家的身份投身革命。次年,韓樂然受派到東北,在沈陽開辦了東北第一所美術(shù)學(xué)校——奉天美術(shù)專科學(xué)校并親任校長,聘請(qǐng)著名藝術(shù)家歐陽予倩等人任教,向東北學(xué)生系統(tǒng)教授繪畫技法和理論,傳達(dá)愛國思想。1925年下半年到1929年,韓樂然以中學(xué)美術(shù)教員等身份,在哈爾濱、齊齊哈爾從事秘密革命工作和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不久,他成立“革命同志會(huì)”,發(fā)展了首批黨員。
1925年11月,韓樂然受黨組織派遣,秘密去蘇聯(lián)學(xué)習(xí);4年后,韓樂然赴法國勤工儉學(xué),并進(jìn)入著名的巴黎盧佛爾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習(xí)西方美術(shù),一個(gè)個(gè)西方繪畫大師給他打開了視窗,誕生于19世紀(jì)60年代的法國“印象派”繪畫給了他巨大的沖擊,尤其是后期印象派畫家梵高、高更、塞尚等人的作品,讓他找到了藝術(shù)火山噴發(fā)口,狂舞的線條和激情的色彩讓他的水彩和油畫煥然一新。他學(xué)習(xí)大師作品,一邊到荷蘭、比利時(shí)、英國、意大利等國寫生,臨摹自然生活,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油畫和水彩畫,舉辦個(gè)人畫展,擴(kuò)大海外影響。
這時(shí),他還參與組織了很多愛國藝術(shù)活動(dòng),1932年在巴黎與劉開渠、唐一禾、常書鴻等發(fā)起成立“中國留法藝術(shù)學(xué)會(huì)”,在國內(nèi)刊物《藝風(fēng)》上介紹西方美術(shù)。1934年,他又聯(lián)合其他人發(fā)表《中國東北四省留法同學(xué)宣言》,反對(du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如果說郭沫若、艾青是追求革命與詩歌,而韓樂然則是擁抱革命與藝術(shù)。革命和文學(xué)藝術(shù)這兩種東西最需要激情,也最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風(fēng)干葡萄的建筑(水彩,1946年)

哈薩克婦女捻毛(油畫,1945年)
回國后,韓樂然以畫筆為旗為槍,投入到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給《反攻》(中共東北特委主辦的半月刊)畫了許多封面,創(chuàng)作巨幅油畫《全民抗戰(zhàn)》《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等。他拍攝了大量抗日現(xiàn)場照片,通過路易·艾黎、斯諾、史沫特萊等國際友人發(fā)往國外,進(jìn)行國際輿論引導(dǎo)。1938年冬,韓樂然隨郭沫若領(lǐng)導(dǎo)的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組織的作家藝術(shù)家訪問團(tuán)到了延安,在延安女子大學(xué)作《關(guān)于抗日時(shí)期民族藝術(shù)文化》的講演。同年,他被派到李濟(jì)深領(lǐng)導(dǎo)的國民黨戰(zhàn)地委員會(huì)任少將指導(dǎo)員,從事抗日宣傳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想不到1940年在陜西寶雞被國民黨特務(wù)機(jī)關(guān)秘密逮捕,關(guān)押在西安“特種拘留所”。黨組織通過李濟(jì)深和東北人士的多方營救,被關(guān)押三年的韓樂然重回自由,在西安舉辦了個(gè)人展覽。
之后,韓樂然偕妻女到大西北大地寫生,走過甘肅河西走廊、青海、新疆大地,描繪這里自然質(zhì)樸的民間風(fēng)情,尤其是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shù)民族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現(xiàn)在他的筆下。
在繼張大千以國畫的形式摹畫敦煌石窟壁畫之后,韓樂然首創(chuàng)以油畫、水彩等西洋畫技法,臨摹新疆克孜爾石窟的壁畫。據(jù)了解,克孜爾石窟的壁畫藝術(shù)有自己獨(dú)特的特點(diǎn),最明顯的是中亞犍陀羅風(fēng)格和黃金時(shí)期的龜茲畫風(fēng)……在克孜爾石窟,韓樂然還像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者一樣,對(duì)克孜爾石窟進(jìn)行編號(hào)、整理、記錄,進(jìn)行壁畫學(xué)術(shù)研磨,為我國研究克孜爾石窟藝術(shù)第一人,為中國藝術(shù)史做出了貢獻(xiàn)。
韓樂然分別于1946年4月和1947年2月兩次進(jìn)入新疆,除了在迪化(即烏魯木齊)附近活動(dòng)并創(chuàng)作外,東至哈密、吐魯番,南到喀什,捕捉一線的鮮活、生動(dòng)場景,在高昌國遺址,在克孜爾千佛洞,在草原,在哈薩克牧民氈房,在天池,在南疆維吾爾村落,在香妃墓……都留下了不少酣暢淋漓的生動(dòng)油畫、水彩和速寫素描。這些作品以人物為多,也有少量風(fēng)景作品,展現(xiàn)了少數(shù)民族的風(fēng)土人情和粗獷、荒涼的大西北自然風(fēng)景和古城古跡,并在蘭州、迪化(烏魯木齊)等地舉辦了十多次畫展。
韓樂然偕妻女赴西北寫生,還有一個(gè)潛伏的目的就是秘密從事西北地區(qū)高層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1946年夏天,韓樂然先后對(duì)國民黨的上層要員陶峙岳、張治中、趙壽山等進(jìn)行宣傳,為后來和平解放新疆做了一種必要的鋪墊。
1947年春,韓樂然再次去克孜爾千佛洞考察、臨摹壁畫。回到烏魯木齊后,韓樂然舉辦了一次個(gè)人畫展,想不到迪化的這次畫展,成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畫展……
這一年的7月,49歲的韓樂然乘坐國民黨軍用飛機(jī),由迪化(烏魯木齊)飛往蘭州,途中不幸遭遇空難,英年早逝,未竟的藝術(shù)夢(mèng)想隨空飄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韓樂然被追認(rèn)為革命烈士。1953年,韓樂然夫人劉玉霞把他的135幅代表作品捐贈(zèng)給國家,其中水彩畫85幅、素描9幅、油畫41幅,均收藏于中國美術(shù)館,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中國美術(shù)館研究員劉曦林評(píng)價(jià)韓樂然時(shí)說:“他是一座文化寶庫。”
以印象派的筆調(diào)描繪新疆和大西北
一翻開《韓樂然繪畫作品集》,就被他那種粗獷的寫實(shí)主義所觸動(dòng),以一種豪邁、流利的豪情,粗線條地勾畫著大西北和大西北普通的勞動(dòng)者,漢民、藏民、維吾爾農(nóng)民、哈薩克牧民,修路的鐵路工人、公路工人,以及天山天池、草原、戈壁、嘉峪關(guān)、克孜爾千佛洞、烏魯木齊等城鄉(xiāng)風(fēng)貌,畫面鮮活生動(dòng)鮮明。
澳門基金會(huì)出版的畫冊(cè),收集了他的120幅油畫、水彩畫、速寫、克孜爾石窟壁畫和敦煌壁畫的摹繪作品,有風(fēng)景畫,但更多的是人物畫,尤其是以新疆少數(shù)民族人物畫為主的西北少數(shù)民族人物畫。
無論是人物畫還是人景合一圖,還是純風(fēng)景畫,韓樂然都是寫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與現(xiàn)代派的結(jié)合,表現(xiàn)對(duì)象真實(shí)厚重而清晰,沒有想象人物,沒有模糊風(fēng)景,但并沒有因此而純客觀、冷靜地再現(xiàn)生活與風(fēng)景,而是充溢著他的感情,充溢著對(duì)火熱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真誠熱愛,對(duì)光明、和平的向往,對(duì)農(nóng)民、牧民、工人、手藝人等勞動(dòng)大眾的熱愛,對(duì)粗獷厚重的大西北的熱愛。他將飽滿的紅色革命理想與激情注入到釉彩、顏料和線條中,抒寫火熱的三四十年代這個(gè)革命歲月。他畫得大氣而蒼茫,渾厚而結(jié)實(shí)。
在這一點(diǎn)上他與塞尚很相像。塞尚雖是后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但反對(duì)印象主義那種忽視素描、把物象弄得朦朧不清的繪畫語言,而是強(qiáng)調(diào)畫中物象的明晰性與堅(jiān)實(shí)感。他認(rèn)為,倘若畫中物象模糊不清,那么便無法尋求畫面的構(gòu)成意味。因此,他立志要“將印象主義變得象博物館中的藝術(shù)那樣堅(jiān)固而恒久”。

庫車婦女賣鮮果酸奶(油畫,1946年)

天山腳下歌舞(油畫,1945年)
韓樂然與塞尚一樣,除人物肖像畫以外,其油畫和水彩畫創(chuàng)作,在極力追求一種能塑造出鮮明、結(jié)實(shí)之形體的繪畫語言,但同時(shí)筆調(diào)中注入了豐富的浪漫與激情,那粗線條的筆調(diào),那洋溢著大氣與豪情的條塊與色塊,并不是像自然主義那樣,勾勒出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每一個(gè)局部,他甚至為了凸現(xiàn)他的人物或中心風(fēng)景,有時(shí)將一些人的臉部的五官都作為不必要的細(xì)節(jié)或模糊或省略了,眼睛大多成一條細(xì)線,不讓觀眾的眼睛停留在那些細(xì)節(jié)局部上,而是停留在整體的畫面意蘊(yùn)和中心人物的生產(chǎn)、生活動(dòng)作上,或者主要風(fēng)景的姿態(tài)上。這一點(diǎn),與塞尚也很相似。塞尚在創(chuàng)作中排除繁瑣的細(xì)節(jié)描繪,而著力于對(duì)物象的簡化、概括的處理。另外,塞尚對(duì)風(fēng)景的描繪不僅簡約,而且富于幾何意味,用圓柱體、圓錐體和球體等幾何型來表現(xiàn)自然,韓樂然在表現(xiàn)大西北的風(fēng)景時(shí),有時(shí)也常現(xiàn)這幾種幾何形式,尤其在表現(xiàn)新疆的大山時(shí),有大量近景、遠(yuǎn)景類似圓柱體造型。
但韓樂然在用色上,卻不像塞尚那么豐富璀璨,而是簡單、明了,只是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光與色的構(gòu)成,尤其是他畫新疆、甘肅等地的畫作,從大塊、粗放、明快的色線與色塊上,欣賞到大西北熱烈的陽光,陽光下陽剛的大山與大地,鮮明的人物帽子、頭巾或身上的閃光,以及背光處褐黑色的暗影。如《流沙掩埋的古城》《哈薩克婦女搗米》《拉卜楞寺前歌舞》等等。
從整體上看,韓樂然的油畫作品色調(diào)偏暗,無論是畫青海的藏民生活,還是畫新疆南北疆的生活,都是大量使用了褐紅、褐黑色,畫面比較凝重、厚實(shí),有些壓抑,仿佛是黎明前的黑暗。而他的水彩畫,整體上卻顯得異常的陽光、明快、流利、清麗,也許與用的材料有關(guān),但可能不僅僅是材料,還有他畫水彩的技能和心態(tài),似乎他畫油畫時(shí)化不開,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并不能隨心所欲,而畫水彩時(shí)似乎找到了自己最好的表達(dá)方式,心情愉悅,神采奕奕,酣暢淋漓地表現(xiàn)那些山、草原和勞動(dòng)者。從韓樂然的大部分油畫中,可以品出苦澀苦悶,而從水彩畫中品出的是豁然洞開、明朗愉悅,痛快淋漓。
韓樂然的油畫為什么色調(diào)偏暗,大量使用褐紅與褐黑色?通過對(duì)比,我發(fā)現(xiàn),他吸收了佛教洞窟壁畫的色彩與技法,他曾臨摹過青海塔爾寺、拉卜楞寺的壁畫,甘肅敦煌莫高窟壁畫,新疆克孜爾千佛洞的壁畫,尤其是克孜爾千佛洞,韓樂然有緣數(shù)次長時(shí)間到那里,并主要以油畫的形式臨摹壁畫,留下了大量的油畫臨摹作品。佛教壁畫的褐色給了他深刻而持久的影響,也許他覺得那才是他油畫應(yīng)有的色調(diào)。
韓樂然的油畫與水彩畫在光色上有巨大的明暗差異,但其實(shí)在繪畫題材和繪畫內(nèi)容上,這二者卻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都是描寫大西北土地上的勞動(dòng)者和大西北干旱少雨的大自然的。
韓樂然眼中和筆下的大西北,主要是新疆、甘肅的河西走廊、青海三地,也有少數(shù)是畫陜西的。韓樂然沒有到過西藏,所以沒有畫西藏,他筆下藏民都是青海的。

向著光明前進(jìn)的藏民(油畫,1945年)

敦煌莫高窟86洞隋代飛天摹寫(水彩)
他的油畫和水彩畫,除了少部分是畫大山大河(黃河)、玉門關(guān)、莫高窟、克孜爾千佛洞、烽火臺(tái)、哈密王墳等自然風(fēng)景外,大量是畫人物的,自然風(fēng)景或人文景觀大多作為人物生活、生產(chǎn)背景出現(xiàn)。而這些人物,有現(xiàn)實(shí)生活情景,也有生產(chǎn)的場面,主人公都是普通勞動(dòng)者,如修筑寶天(寶雞至天水)鐵路、天蘭(天水到蘭州)鐵路的筑路工人,通過系列創(chuàng)作展現(xiàn)鐵路工人熱火朝天的勞動(dòng)場面;耕地或收割的漢族農(nóng)民,背水、浣衣、取草的藏民,蘭州黃河的賣水者,烤馕和燻皮子的維吾爾族人、纖夫和船夫、釘馬掌的男人,待雇的木匠,紡羊毛的婦女、賣鮮果酸奶的庫車婦女、女木工、搗米的哈薩克婦女、還有商人、考古者、樂師、舞蹈者、朝拜者、做禮拜的信徒、牧馬人和賽馬者等等,都是普通的百姓。他們過著普通、忙碌而富有意味的生活。與司徒喬的畫一樣,韓樂然筆下充滿著人間生活氣息,展現(xiàn)勞動(dòng)者的美,展現(xiàn)普通百姓辛苦、快樂自在的美學(xué)精神。
在20世紀(jì)40年代初,張大千以國畫的形式臨摹敦煌莫高窟壁畫之后,韓樂然也于1946、1947年兩次到南疆的克孜爾千佛洞,用西洋畫——油畫和水彩畫的形式臨摹那里的壁畫,這既有利于更好地保存、展現(xiàn)絲綢之路上新疆佛教石窟藝術(shù),使這一民族文化瑰寶得到更加廣泛的社會(huì)認(rèn)識(shí),也有利于進(jìn)一步研究克孜爾千佛洞的壁畫美術(shù)和佛教文化在中國大地上的歷史傳播。
韓樂然與那個(gè)時(shí)代許多中國西洋畫畫家一樣,是再現(xiàn)生活與時(shí)代的,不像現(xiàn)在,許多外國和中國的現(xiàn)代派畫家,都追求形式上的出奇變異,強(qiáng)調(diào)表現(xiàn)自我個(gè)人內(nèi)心的感受或夢(mèng)境,而忽視豐富復(fù)雜、五彩繽紛的社會(huì)生活,更不可能去再現(xiàn)底層的勞動(dòng)者生產(chǎn)、生活的場景。
……無論是傳統(tǒng)的古典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浪漫主義繪畫,還是不斷革新的什么印象派、野獸派、未來派、立體主義、達(dá)達(dá)主義、抽象主義、波普藝術(shù)等等現(xiàn)代派畫家,都要與時(shí)俱進(jìn),將新的生活、新的時(shí)代精神,通過一種適宜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達(dá)到一種高度概括的美(哪怕以丑為美)和崇高(撕掉偽崇高,也是一種崇高)。
韓樂然的繪畫,是粗線條的,是大刀闊斧地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但有時(shí)不免有些粗糙,有些簡單,甚至有些潦草。他的一些油畫人物畫臉部虛空,或以簡單線條描繪眼睛,沒畫人物鼻子或嘴巴,學(xué)習(xí)豐子愷漫畫“不要臉”之化繁為簡的虛擬手法,這是一種錯(cuò)誤,或是功力不夠的表現(xiàn)。豐子愷畫漫畫,可以通過簡單勾勒的辦法和一兩句言簡意賅的語言文字表達(dá)繪畫意蘊(yùn)和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油畫和水彩畫卻必須通過自身豐滿的繪畫語言來表達(dá)藝術(shù)的美,表達(dá)畫家的思想。
與此同時(shí),韓樂然表現(xiàn)時(shí)代精神方面,也明顯不夠,不僅是畫作還是畫作背后所隱含的美學(xué)意味,也都存在著一定的距離。這是韓樂然英年早逝這一生命體遺憾之外,作為革命藝術(shù)家在藝術(shù)上的遺憾。但不管怎樣,他與魯少飛、沈逸千、司徒喬、黎雄才、趙望云等畫家一起,不僅創(chuàng)作了大量新疆題材的畫作,而且也給新疆繪畫愛好者、美術(shù)青年以最早的啟發(fā),給新疆種下了美術(shù)的種子,讓新疆繪畫掀開了新的一頁。
韓樂然和他們都是新疆美術(shù)史上的先驅(qū)者。
(本文圖片由孤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