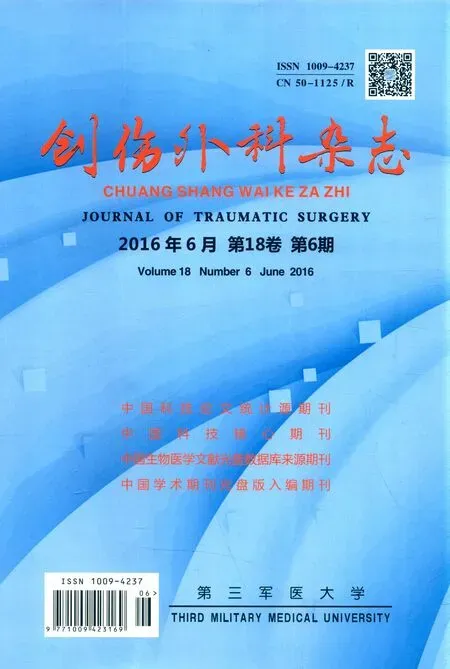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生物力學機制
趙 輝,朱 峰
?
·綜述·
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生物力學機制
趙輝,朱峰
隨著現代各種爆炸性武器尤其是各種簡易爆炸裝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IEDs)的出現,沖擊傷已成為一種常見傷類。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系沖擊波直接作用人體導致的顱腦損傷,其危害正受到廣泛關注。為研究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病因學和病理特點,以提高顱腦沖擊傷的防護和救治水平,迄今已通過多學科融合、多種研究手段相結合來開展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研究。本文對沖擊波物理特性、沖擊傷實驗方法、顱腦沖擊傷力學機制和閾值等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生物力學機制內容進行簡要介紹,以期引起更多關注。
顱腦損傷; 沖擊傷; 爆炸; 生物力學
人體沖擊傷常見于戰爭、恐怖襲擊、航空事故以及生產爆炸事故等,隨著現代各種爆炸性武器、尤其是各種簡易爆炸裝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IEDs)的出現,沖擊傷已成為一種常見傷類。原發沖擊傷是指沖擊波直接作用于機體所產生的損傷[1]。以往認為,聽覺系統和含氣臟器(肺臟和胃腸道)是沖擊傷的主要靶器官,頭顱因堅硬顱骨保護,沖擊波直接作用一般不會損傷腦組織。美軍統計發現,2001~2007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63%的傷亡人員與爆炸損傷有關[2];美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戰爭中52%的顱腦損傷(TBI)因爆炸沖擊所致[3]。當前,沖擊波直接作用人體導致的原發性顱腦沖擊傷正受到廣泛關注,國際學術界已通過多種手段開展了大量顱腦沖擊傷研究,本文就顱腦沖擊傷的生物力學問題進行簡要介紹。
1 沖擊波的物理特性
爆炸是一種極為迅速的物理或化學能量的釋放過程,其主要特征是在爆點周圍介質中出現突然的壓力釋放增高,或稱為壓力突變。典型的沖擊波通常是在爆炸過程中形成,沖擊傷常在爆炸時產生。爆炸導致的人體傷害除沖擊波直接作用外,還可能同時有破片穿透、熱燒傷、鈍性撞擊、微波和毒氣等多種傷害因素。沖擊波是介質(如空氣、水)中傳播的一種高速高壓波,具有與聲波相似的物理特性,還具有區別于聲波的熱力學特性:沖擊波傳播速度大于未被擾動介質中的聲速;沖擊波前界,即波陣面上,介質壓力、密度、溫度等狀態參數發生階躍性的突然增高;沖擊波速度與其強度有很大關系,強度越大,速度也越快;沖擊波無周期性,在介質中傳播會發生能量消耗。理想爆炸沖擊波波陣面空氣壓力、密度和溫度出現階躍式上升,然后壓力呈指數性衰減,并達負壓。理想爆炸沖擊波壓力曲線又稱為弗里德蘭德(Friedlander)曲線(圖1),該曲線常用超壓(overpressure)、超壓持續時間(duration)或超壓對持續時間積分,即沖量(impulse)來定義。

P0:正常大氣壓;ΔP:沖擊波超壓;ΔP-:沖擊波負壓;T+:沖擊波正壓持續時間;T-:沖擊波負壓持續時間
2 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實驗方法
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生物力學機制研究的關鍵是需要產生一爆炸沖擊波直接作用于試驗對象,以此研究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力學過程和病理生理變化,目前可以通過常規實驗或計算機模擬的方法來產生一理想沖擊波。
2.1自由場炸藥試驗(free-field explosives testing)該方法是在空曠環境中引爆爆炸物產生一真實爆炸沖擊波,直接作用于實驗對象進行爆炸沖擊傷研究。由于非理想沖擊波不易量化,還可能使待研究的沖擊傷模型復雜化,因此自由場爆炸試驗時爆炸物應置于空中,并避開周圍建筑物,以防止沖擊波因周圍復雜環境反射形成復雜波。為規范該試驗方法中爆炸物質量和動物布放位置差異對沖擊傷致傷參數的影響(如沖擊波超壓和持續時間),可以通過經驗曲線或霍普金森準則對爆炸當量或布放距離進行等效計算[4]。自由場爆炸試驗的最顯著優點是實驗沖擊波與真實爆炸一致,但缺點是試驗耗費大、耗時,環境控制困難,爆炸形成的破片或毒氣會使沖擊傷模型復雜化。
2.2激波管試驗(shock tube testing)激波管是由幾部分組成起來的長管,通常用膜片將長管分為兩段:一段充氣,叫做“高壓段”,另一段稱為“低壓段”,其工作原理是:當膜片承受不了高壓段內氣體壓力破裂時,管腔內立即發生氣體的高速流動。高壓段內形成稀疏波,其運動方向背離膜片側;低壓段中形成激波,其運動方向與稀疏波正好相反,朝向管尾側。當稀疏波趕上激波后,激波壓力迅速下降,稀疏波尾壓力低于大氣壓時,則可得到負壓相,由此得到近似于理想沖擊波的壓力曲線。與爆炸產生的沖擊波相比,雖然激波管壓力曲線有時波形上有所不同,但性質上卻相同。利用激波管所產生的激波可進行沖擊傷的實驗研究。作者單位采用“雙夾膜”方式成功研制了包括驅動段、夾膜段、擴張段、過渡段和實驗段的系列生物激波管,可進行大、小動物乃至細胞層面的沖擊傷實驗。用激波管理論上可復制各種爆炸沖擊波曲線,且該方法環境可控,實驗經濟,但與真實爆炸還是有區別,如不能反映出爆炸熱效應[4]。
2.3管道內爆炸試驗(blast tube testing)該方法類似激波管,試驗前將爆炸物放置在管道末端錐形筒或拋物線筒內,試驗時引爆管道內爆炸物,使爆炸產生的高溫高壓氣體在管道內傳播,以形成理想沖擊波。管道內爆炸試驗的主要缺點是爆炸產生的氣體或粉末可能對沖擊傷試驗結果有影響,且爆炸物的存儲和處理對實驗室還有特殊要求。
2.4計算機模擬(computer simulation)爆炸沖擊的計算機模擬隨著計算機技術和數值計算方法不斷進步而得到極大發展,現已成為常規沖擊實驗的一種有效補充。有限元法是爆炸沖擊計算機模擬的最常用方法,國際上已開發出多個版本的適宜于模擬沖擊傷的人和動物頭顱有限元模型。本文作者結合爆炸沖擊動力學理論和激波管工作原理,首先開發出經過嚴格實驗驗證的激波管有限元模型。該模型基于任意拉格朗日-歐拉(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算法,可以準確描述沖擊波在激波管中的形成和傳播,實現了激波管形狀和尺寸參數化的快速設計,并已集成在ETA公司全球發行的高性能計算分析軟件InventiumTM中,被世界多個學術機構用于沖擊波致人體損傷的模擬研究。計算機模擬方法與常規試驗方法相比,具有實驗效率高和耗費低的優點,但該方法亟待完善,如顱腦沖擊傷有限元模型中組織材料的率變特性、不同結構間的力學耦合以及經典沖擊實驗驗證等問題。
進行沖擊傷試驗的壓力測試方法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側面測量(side-on),即壓力傳感器敏感面垂直于沖擊波傳播方向測量沖擊波超壓;另一種是迎面測量(face-on),即壓力傳感器敏感面朝向正對沖擊波波源測量沖擊波總壓(超壓和動壓)。第二種測試方法其結果是第一種測試方法的2~8倍。因此,在引用比較已發表試驗數據或驗證計算機模擬結果時要特別注意。
3 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損傷機制
如前所述,嚴重顱腦爆炸傷可同時復合多種傷害因素,如沖擊波直接作用、頭顱被沖擊波掀起的物體撞擊或穿透、人體被拋擲而發生的撞擊傷、燒傷或其它環境污染傷害等;中輕度顱腦爆炸傷一般為沖擊波直接作用所致。沖擊波直接作用人體引起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力學響應過程持續時間由數十至數百毫秒,其損傷力學機制和損傷閾值是當前關注的重點研究內容。
3.1顱腦沖擊傷的損傷力學機制顱腦沖擊傷的力學過程異常復雜,可能既有沖擊波直接作用的人體內波傳播,又有頭顱對沖擊波動壓撞擊的響應——即頭顱加速運動,前者導致顱內壓力增加,后者則是顱內出現應力/應變。
3.1.1顱腦沖擊傷的波傳播效應人體遭受沖擊波作用時體內沖擊波傳播存在多條途徑。顱骨是應力波的“良導體”。顱腦沖擊傷的計算機模擬實驗研究表明,應力波在104~105Hz以內僅有很少的能量衰減[5]。沖擊波作用頭顱首先引起顱骨變形,壓縮波在顱骨變形初始階段比空氣中更快地穿過顱骨和腦組織[6]。與其它任何彈性物體類似,壓縮波通過后被壓縮沖擊的顱骨瞬間反彈,在腦脊液和組織內形成一拉伸波,該拉伸波與隨后傳到的沖擊波負壓部分疊加,可能使顱骨壓縮再次加劇[7]。壓縮/拉伸波在顱內以約為1 560m/s的速度傳播,由于顱腦組織材料的非對稱性和加載沖擊波的非均一性,顱內產生了剪切波。剪切波傳播速度慢(約10m/s),持續時間長,其傷害比壓縮波更明顯。離體和在體實驗均表明,拉伸應變對組織的傷害比壓應變更明顯[8]。本質上,顱內充盈腦脊液可以承受壓力載荷從而對腦組織結構起到支撐保護作用,但拉力卻可直接破壞弱或強的分子層面連接。此外,腦組織和腦脊液內的拉伸變化可導致空化效應,微泡空化可引起周圍組織出現拉伸損傷,但生理環境下是否會出現空化效應目前還存在爭議[7]。
沖擊波直接作用頭顱,應力波可通過顱骨腔隙或孔洞直接傳入顱內,如眼窩、篩骨、枕大孔和血管孔等[9-13]。作用于胸腹部的沖擊波由于腦與軀干通過大血管和脊髓槽相連接使爆炸沖擊波能量可能以彈性波的形式沿著血管傳入大腦[9-11],血管內的彈性波傳播慢,其通常在沖擊波直接作用頭顱后才抵達顱內,但引起的顱腦損傷仍被歸入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然而,彈性波是否能從血管傳入顱內還存在一些疑問[14],且目前廣泛使用的胸腹部防護裝具[15]似乎并未減少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發生率,也對該假說提出了質疑。
3.1.2頭顱加速效應沖擊波作用頭顱可致頭顱瞬間加速運動,因頭頸部約束還可使頭顱出現旋轉加速。實驗發現超壓峰值110~740kPa的沖擊波直接沖擊頭顱,頭顱加速度峰值在385~3 845g[16]。現已知道頭顱線加速或旋轉加速均可引起多種類型損傷,如彌漫性軸索損傷(diffuse axonal injury,DAI)、挫傷和急性硬膜下出血[17-18]。由于顱-腦復雜解剖結構的影響,究竟是線加速還是角加速引起了顱腦損傷還曾經在創傷生物力學研究領域引起長期爭論。一種觀點認為:撞擊頭顱的力量足夠大,顱腦之間就可能在加速運動過程中與撞擊點或對沖點發生接觸,以此導致腦挫裂傷或腦出血[19]。然而,因為腦組織與腦脊液的密度差異并不大,頭顱加速運動時兩者之間的相對運動速度低,顱腦之間需要一定時間才能接觸[20]。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顱內腦的旋轉運動沒有密度方面的約束條件,腦可以獲得較高旋轉速度,且因為顱骨不規則的幾何結構,更容易發生顱-腦之間的接觸。TBI的動物實驗已經證實腦的旋轉運動對動物的傷害很大,甚至在顱腦之間的相對中度旋轉都可能導致局灶性或彌漫性的損傷[17,21]。需要指出的是:頭顱直線加速運動與顱內壓變化有顯著關系,沖擊震動引起的頭顱瞬間線加速可引起顱腦損傷[22]。
3.2顱腦沖擊傷的損傷閾值明確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損傷閾值對顱腦沖擊傷防治研究有重要意義:從事沖擊傷救治的醫學研究人員需要掌握沖擊傷的致傷參數邊界條件,以復制出各種動物模型;沖擊傷防護研究人員需要明確知道顱腦沖擊傷的損傷閾值,以制定相應的防護標準,從而有效評價各種防護裝備防護效果。
以往建立顱腦撞擊傷損傷閾值時將力學輸入作為預測參數,如頭顱受撞擊時的加速度或對加速度的時間積分,但現在已知道若以頭顱對外力的響應來預測顱腦損傷則更準確,如用應力或應變。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頭顱瞬間加速,持續時間短;顱內壓是常見顱腦損傷評估力學指標之一,但該壓力究竟是沖擊波超壓引起,還是因沖擊波動壓撞擊頭顱引起的線加速所致,目前尚不明確。盡管計算機模型可以預測顱內應力/應變,但這些模型尚需要大量試驗數據來進行驗證。因此,顱腦沖擊傷的損傷閾值目前不是以響應,而是以輸入來評估,如沖擊波超壓和持續時間。
目前已有多種動物被用于沖擊傷實驗研究,如鼠、兔和豬,由于實驗選用動物模型和實驗方法差異,致傷參數也不完全相同。如Wistar大鼠激波管顱腦沖擊試驗研究發現,在超壓240kPa、持續時間2ms的沖擊波作用下未發現損傷[23];同樣通過激波管試驗,發現持續時間為3.5ms,Spague-Dawley大鼠在沖擊波超壓不超過126kPa未損傷,達到147kPa則出現顱內出血[24];激波管實驗還發現沖擊波超壓在414~655kPa,持續時間為0.5ms,Long-Evans大鼠出現了蛛網膜下腔出血[25]。Cheng等[26]用TNT爆炸試驗,發現持續時間均為3ms,沖擊波超壓200kPa以上動物出現腦挫裂傷,100kPa時卻未發現損傷。人與動物解剖結構和功能存在顯著差異,如何將動物的損傷閾值遞推到人也成為沖擊傷研究的重要內容。20世紀60、70年代研究人員建立了從動物到人的肺沖擊傷縮放比例關系。近年有學者以體重作為比例因子提出了動物與人關于能量吸收、壓力和顱內最大主應力的縮放關系。Zhu等[27]分析了爆炸沖擊試驗和激波管沖擊實驗的沖擊比例縮放關系,建立了基于沖擊波超壓和持續時間的顱腦沖擊傷比例縮放模型,并推導出從大鼠到豬、再到人的比例縮放曲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沖擊試驗的復雜性,相關比例縮放還需要大量試驗數據來進行驗證。
3.3顱腦沖擊傷的響應特點因頭顱結構復雜以及沖擊波能量具有高頻特性、作用持續時間短,盡管在體試驗中采集生物力學參數非常困難,但若干腦組織結構因吸收沖擊波能量而損傷卻是明確的,如腦血管、軸突、神經元樹突和突觸、細胞骨架和離子通道等。從力學觀點看,不同結構和屬性(密度和彈性)宏觀或微觀結合部在高應變率加載的沖擊波作用下是易損傷部位,包括血腦屏障、脈絡叢、腦-腦脊液銜接界面、神經元/軸索膜、樹突棘和郎飛結等;若這些部位的共振頻率與沖擊波的頻率一致,相應結合部特別易損傷。
爆炸性顱腦損傷因損傷環境復雜,應是多種沖擊波損傷疊加共同作用機體,機體整體、局部和腦組織又共同對沖擊波發生反應的結果;動物實驗和臨床研究表明,顱腦沖擊傷可引起神經生理、病理、生化及行為的改變[28]。對特別嚴重的顱腦沖擊傷,如顱骨骨折或顱內血腫,可通過CT或MRI影像檢測;但對于腦震蕩或中度腦損傷,如神經軸、微血管或突觸損傷,則即使是用高分辨率的影像檢測技術也很難進行診斷,因此由于沒有明顯創傷或僅有輕度不適,中輕度原發性顱腦沖擊傷易被漏診。
4 展望
爆炸沖擊傷的傷害因素多,頭顱結構和功能復雜,通過系列研究來闡明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病因學和病理學特點對提高顱腦爆炸傷的防護和救治水平有重要意義。盡管迄今已對顱腦沖擊傷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目前對顱腦沖擊傷的損傷機制和耐限仍不十分清楚,還需要綜合多學科知識,結合多種研究方法,在器官、組織和細胞等多層次結構上進行跨尺度生物力學研究[29-30],以進一步揭示顱腦沖擊傷的損傷機制,從而為顱腦沖擊傷的防護和救治提供理論指導。
[1] 王正國.原發沖擊傷的發生機制[J].解放軍醫學雜志,1995,20(4):316-317.
[2] Wojcik BE,Stein CR,Bagg K,et al.Traumatic brain injury hospitalizations of U.S. army soldiers deployed to Afghanistan and Iraq[J].Am J Preve Med,2010,38(1S):S108-116.
[3] Galarneau MR,Woodruff SI,Dye JL,et al.Traumatic brain injury during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avy-Marine Corps Combat Trauma Registry[J].J Neurosurg,2008,108(5):950-957.
[4] Bass CR,Panzer MB,Rafaels KA,et al.Brain injuries from blast[J].Ann Biom Eng,2012,40(1):185-202.
[5] Stefan S,Goode RL.Transmission properties of bone conducted sound: measurements in cadaver heads[J].J Acoust Soc(Am),2005,118(4):2373-2391.
[6] Przekwas A,Tan XG,Imielinska C,et al.Development of physics-based model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of helmet performance in blast wave TBI[C].ASME 2009 Summer Bioengineering Conferenc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2009:607-608.
[7] Gupta RK,Przekwas A.Mathematical models of blast-induced TBI: current status,challenges,and prospects[J].Front Neurol,2013,4:59.
[8] Xi X,Zhong P.Dynamic photoelastic study of the transient stress field in solids during shock wave lithotripsy[J].J Acoust Soc(Am),2001,109(3):1226-1239.
[9] Yudhijit B.Shell shock revisited: solving the puzzle of blast trauma[J].Science,2008,319(5862):406-408.
[10] Courtney AC,Courtney MW.A thoracic mechanism of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due to blast pressure waves[J].Med Hypoth,2009,72(1):76-83.
[11] Cernak I.The importance of systemic response in the pathobiology of blast-induced neurotrauma[J].Front Neurol,2010,1:151.
[12] Chavko M,Watanabe T,Adeeb S,et al. Transfer of the pressure wave through the body and its impact on the brain[C].HFM- 207 NATO Symposiumona Survey of Blast Injury Across the Full Landscape of Military Science(Halifax,NS),2011.
[13] Bass CR,Panzer MB,Rafaels KA,et al.Brain injuries from blast[J].Ann Biom Eng,2012,40(1):185-202.
[14] Saljo A,Arrhen F,Bolouri H,et al.Neuropathology and pressure in the pig brain resulting from low-impulse noise exposure[J].J Neurotrauma,2008,25(12):1397-1406.
[15] Wood GW,Panzer MB,Shridharani JK,et al.Attenuation of blast pressure behind ballistic protective vests[J].Inj Prev,2013,19(1):19-25.
[16] Shridharani JK,Wood GW,Panzer MB,et al.Porcine head response to blast[J].Front Neurol,2012,3:70.
[17] King AI,Yang KH,Zhang L,et al.Is head injury caused by linear or angularacceler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Ircob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n the Biomechanics of Impact Conference,2003.
[18] Rowson S,Duma SM.Development of the STAR evaluation system for football helmets: integrating player head impact exposure and risk of concussion[J].Ann Biomed Eng,2011,39(8):2130-2140.
[19] Smith DH,Meaney DF.Axonal damage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J].Neuroscientist,2000,6(8):483-495.
[20] Vanden Akker R.Influence of skull flexibility during closed head impact[D].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teborg,2010.
[21] Eucker SA,Smith C,Ralston J,et al.Physiological and histopathological responses following closed rotational head injury depend on direction of head motion[J].Exp Neurol,2011,227(1):79-88.
[22] Proctor JL,Fourney WL,Leiste UH,et al.Rat model of brain injury caused by under-vehicle blast-induced hyperacceleration[J].J Trauma Acute Care Surg,2014,77(3S2):S83-87.
[23] S?lj? A,Bao F,Haglid KG,et al.Blast exposure causes redistribution of phosphorylated neurofilament subunits in neurons of the adult rat brain[J].J Neurotrauma,2000,17(8):719-726.
[24] Long JB,Bentley TL,Wessner KA,et al.Blast overpressure in rats: recreating a battlefield injury in the laboratory[J].J Neurotrauma,2009,26(6):827-840.
[25] Kuehn R,Simard PF,Ian Driscoll,et al.Rodent model of direct cranial blast injury[J].J Neurotrauma,2011,28(10):2155-2169.
[26] Cheng J,Gu JY,Yang T,et al.Development of a rat model for studying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J].J Neurol Sci,2010,294(1-2):23-28.
[27] Zhu F,Chou CC,Yang KH,et al.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hreshold and inter-species scaling law for primary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semi-analytical approach[J].J Mech Med & Biol,2013,13(4):1484-1497.
[28] 寧亞蕾,周元國.原發性顱腦沖擊傷致傷機制及病理學特點[J].中華創傷雜志,2014,30(3):280-283.
[29] Panzer MB,Matthews KA,Yu AW,et al.A multiscale approach to blast neurotrauma modeling: part I-development of novel test devices for in vivo and in vitro blast injury models[J].Front Neurol,2012,3:46.
[30] Effgen GB,Hue CD,Rd VE,et al.A multiscale approach to blast neurotrauma modeling: part II:methodology for inducing blast injury to in vitro models[J].Front Neurol,2012,3:23.
(本文編輯: 郭衛)
The biomechanical mechanism of primary blast brain injury
ZHAOHui1,ZHUFeng2,3
(1.Department 4,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Daping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400042,China; 2.Bioengineering Center,Wayne State University,Detroit,Michigan48202,USA;3.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Daytona Beach,FL32114,USA)
With the increased utilization of explosive-type weapons, especially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blast-induced injury has been one of the injuries observed commonly. Primary blast-induced brain injury (PBBI) is caused by the blast wave loading on human body directly,whose hazardous outcomes are of great interest. To study the etiology and pathology for PBBI,and then improve the treatments and prevention for PBBI,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concerning PBBI have been performed by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s,the property of blast wave,research method for PBBI,mechanical theory for PBBI,and injury tolerance of PBBI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brain injury; blast injury; explosion; biomechanics
1009-4237(2016)06-0375-0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31470913);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啟動項目
400042 重慶,第三軍醫大學大坪醫院野戰外科研究所第四研究室(趙輝); 48202 美國密西根州 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生物工程中心(朱峰); 32114 美國佛羅里達州 戴托那,Embry-Riddle航空航天大學機械工程系(朱峰)
R 642;R 651.15
A
10.3969/j.issn.1009-4237.2016.06.017
2015-12-11;
201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