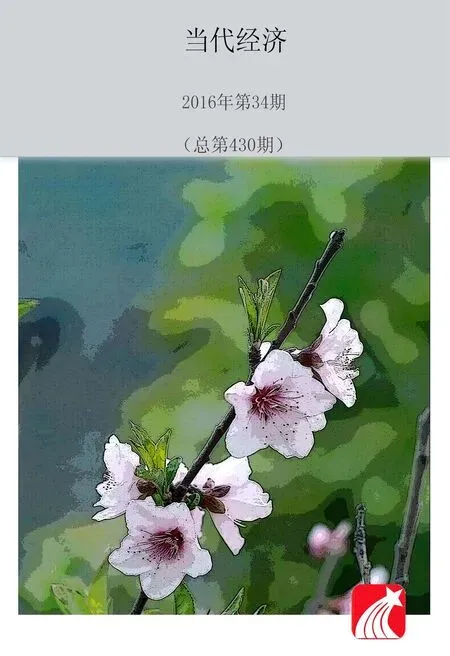比較福利體制框架及對中國福利體制研究影響
鄭彬睿
(英國約克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院)
比較福利體制框架及對中國福利體制研究影響
鄭彬睿
(英國約克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院)
比較福利體制框架改變了以往福利體制研究以發達國家為導向的視角,在原有分類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針對發展中國家福利體制的類別,即(類)發達國家福利體制、非正式保障體制和不保障體制。比較福利體制框架為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福利體制提供了模板,也為研究正在成長中的中國社會福利體制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模板應用與研究要緊跟全球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并要注重新的參與者的作用以及本國自身社會、政治、金融、經濟等政策的影響。
福利體制;非正式保障;不保障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將視野轉向了中國。中國福利體制目前處于什么階段?今后的發展方向是什么?中國與主流的福利國家之間的不同在哪?這些問題無一不吸引著大批西方學者的興趣。隨著西方理論的不斷推陳出新,本文將對比較福利體制的主要內容和研究方法進行簡要概括,再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對比較福利體制框架進行分析,最后對比較福利體制研究對中國福利體制研究的影響進行討論。
一、比較福利體制框架的主要內容
Gough et al (2004)在福利體制三分法的基礎上,根據九大標準對國家福利體制進行重新分類。九大標準是指:支配性生產方式;主要社會關系;主要生存資源;主要政治動員的形式;國家形式;制度;福利結果;路徑依賴的發展;社會政策的本質。Wood和Gough(2006)認為他們的新分類標準能有效地避免福利國家三分法的局限性。例如,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國家三分法(見表1)主要從四個方面對發達國家進行了分類比較:即社會政策在被研究國家的影響力;福利多元;去商品化指數;社會分層化指數。但以上這四個因素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同時相互之間常常存在沖突。這種沖突使得一些國家不能非常明確地被歸于某種特定的類別(Art and Gelissen,2002)。
針對這一缺陷,并且結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福利體制的一些特點,Gough et al(2004)在Esping-Andersen的發達國家福利體制分類上新增了三個新的福利體制類別:類似發達國家(Proto-welfare regime)、非正式保障福利體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和不保障體制(Insecurity regime)。對于東亞地區,Gough 等人直接采用了Ian Holliday(2000)的生產型福利體制(見表2)的概念,但中國被排除在了東亞生產型福利體制之外(見圖1)。
類似福利國家體制是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福利體制發展逐漸與西方發達國家福利水平非常接近的國家,例如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和一些東歐國家(Sharkh & Gough,2010;Gough,2013)。非正式保障體制是指人們不同程度地依賴社區、社會和家庭關系來滿足自身福利要求的制度安排。這些關系大多是等級制的、不對稱的。非正式保障體制是有一定問題存在的。例如對那些經濟基礎薄弱的群眾,這種制度安排只能給這些弱勢群體換來短期的救助,并不能從根源上改變他們的現狀。同時,由于接受了這種短期的救助,他們將在未來更為弱勢,并且對國家或者整個社會的救濟產生更多的依賴,底層的庇護關系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扭曲(Sharkh&Gough,2010;Gough,2013)。

表1 福利國家三個世界

表2 生產型福利體制

圖1 比較福利框架的基本設計邏輯
不保障體制(insecurity)是指,那些國家對社會福利總體不保障,僅僅對緊急事件有一些非正規的常態機制去緩解,但不會去修正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體制。這種體制常見于那些國外勢力與脆弱的國內勢力相勾結,不斷制造爭端和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不保障體制甚至沒有國家界限。無法預見的動蕩環境不僅破壞了穩定的庇護主義模式和社區中非正式的權利,也破壞了家庭應對機制(Gough et al,2004;Wood&Gough,2006)。同時,不保障體制使得整個社會除少數精英以外的絕大多數人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沒有保障、弱勢,還有生存歷經磨難。
綜上,比較性理論框架分類總結如表3所示。
二、比較福利體制對中國福利制度的影響
中國福利體制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其歷史的特殊性,中國是從封建社會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僅僅有資本主義萌芽。這種獨特的歷史軌跡讓中國的發展軌跡顯得尤為獨特。同時,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中國社會很早就有了社會福利的思想,甚至是一些制度。但是,對于現代社會福利體制的建設,中國的起步遠遠晚于其他國家。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加劇——全球化、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使得中國一方面不得不面對許多西方國家曾有過的發展問題(環境問題、城市病等);另一方面,也和西方國家一起面臨一樣的新挑戰(經濟增長變緩、人口老齡化等)。這些新老問題交織在一塊,加之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文化歷史與西方國家存在很大不同,以至于中國的福利制度所產生的福利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新老問題的交織以及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僅增加了中國社會福利體制研究的復雜性,也增加了中國案例在理論研究時的不確定性。這也就可以初步解釋,為什么許多西方學者在對待中國問題時會顯得尤為謹慎、小心。
Gough(2013)等人對待中國的福利體制的研究同樣十分慎重。為了增強研究的可行度,Gough(2013)等人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他們選取福利制度和福利效果作為兩個變量對福利體制分類。同時,Gough等人選取醫療和教育作為他們研究的重點領域,用65個國家和地區對他們的理論進行了檢驗。具體而言,他們從八個方面著手:即從人均補助水平與國民收入的比重;工人補助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醫療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社會捐贈占社會總收入的比重;初中學生入學率以及女學生的比重;兒童疫苗接種率;人均壽命;以及15—24歲年輕人的文盲率來分析各國的福利效果(見表4)。在這種計算標準下,中國被歸入了B類別。所謂B類別,又稱為成功的非正式保障體制。成功的非正式保障體制具體指的是,那些以很少的投入取得了較好的福利效果,但又離真正的福利國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的國家和地區。本文主要選取了A、B兩個類別,A類指的是發達國家或者與發達國家福利水平相似的發展中國家。

表3 比較體制研究分類標準

表4 福利效果的測量
Gough等人的這種定義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成功地肯定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取得的福利成果。以中國為例,近年來,中國在民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醫療保障領域,目前中國有三種醫療保險,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來看,2009年,至少有12.3億人參加了其中一種醫療保險,醫療保險的覆蓋率達到了92.5%。2010 年覆蓋率更是突破了94%。同時,近年來,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籌資水平不斷提高,醫療保險的支出總額也在逐年提高。為了降低人民醫療成本,政府鼓勵興辦私立醫院,以求打破公立醫院的壟斷地位。然而,醫療領域的挑戰仍然存在。首先,雖然公立醫院是中國醫療領域的絕對主力,但其公益性明顯不足。以藥養醫、過度醫療等問題仍然較為嚴重(Wong,2015)。其次,由于經濟雙軌制、戶籍制等因素的影響,農村和城市的醫療體系相對獨立,沒有形成合力。農民進城務工無法享受城市醫療福利;同時由于補助水平較低,農村醫療保險的抗風險能力仍有待提高。最后,初級醫療機構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由于初級醫療機構的投入不足,導致許多群眾一旦生病就往大醫院就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浪費。相比于許多老牌福利國家而言,中國的確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結論和啟示
Gough(1979)在對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和社會福利發展的關系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貢獻,其本人及同事在福利體制分類學上也做了不少的創新工作,較之于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體制分類學的思想,Gough把視野放大到了全球層面——不僅對發達國家進行研究,而且把視線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上。這說明Gough的比較福利體制研究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從一定程度上準確地把握了當代社會發展的規律,尤其是考慮了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福利建設的影響。當然,Gough的比較福利體制分類學仍有一些局限性。例如,Gough 等人的研究更多的是在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研究的基礎上再增加三個針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分類。事實上,對于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批評聲仍不絕于耳。這也就意味著Gough等人不可能完全保證自己的框架不受前人局限性的影響。這也使得比較福利體制框架的矛盾性依然存在。一方面,Gough等人認為東亞各國屬于生產型福利體制,但另一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將許多東亞國家如韓國歸入非正式保障體制內。換言之,Gough等人沒有說清楚新分類是否包含關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老的分類。
然而瑕不掩瑜,Gough(2001;2004)的福利體制分類學的研究對于我國社會政策以及社會福利體制研究仍有著重要的啟示。首先,比較福利體制框架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福利體制提供了模板。尤其是對于研究拉美和非洲地區提供了切入點。其次,要將福利體制研究看作是一個靜態的過程,而是特定時間段一個國家社會政策與政治、經濟文化的博弈的結果。福利體制不是永恒不變的,它會根據不同時期國內外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同時,這也說明在研究單個國家時一定要注意其特殊性。再次,全球化的影響下,對單一國家的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體制進行研究時,絕對不可以忽視新的參與者的作用,尤其是國家組織、跨國公司的作用。最后,社會政策研究不可以僅考慮傳統社會政策領域——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社保等政策對國家福利體制的影響,還應該對其他政策對社會福利發展的影響進行評估。尤其要對那些涉及國家發展戰略的根本之策諸如金融政策、經濟政策對民生的影響進行評估。
[1] Art,W.,and Gelissen,J.: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r more?A state-of the art report[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2(12).
[2] Esping,A.G.: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M]. Policy Press,UK,1990.
[3] Gough,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M].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9.
[4] Gough,I.: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Welfare Regimes:The East Asian Case[J].Global Social Policy,2001(1).
[5] Gough,I.Wood,G.Barrientos,A.Bevan,P.Davis,P.and Room,G.:Insecurity and welfare regimes in Asia,Africa and Latin America:Social Policy in Development Contex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6] Holliday,I.: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J].Political studies,2000,48(4).
[7] Hudson,J.,&Kühner,S.:Towards productive welfar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3 OECD countries[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2009,19(1).
[8] Hudson,J.,&Kühner,S.:Analyzing the productive and protective dimensions of welfare:looking beyond the OECD [J].Social Policy&Administration,2012,46(1).
[9] Jones,C.:Hong Kong,Singapore,South Korea and Taiwan:Oikonomic Welfare States[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1990,25(4).
[10]Jones,C.:The pacific challenge[J].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1993.
[11] Takegawa,S.:Japan’s welfare-state regime:Welfare politics,provider and regulator[J].Development and Society,2005,34(2).
[12] Takegawa,S.: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as factors in building a welfare state:welfare regimes in Europe,Japan and Korea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2009,18(1).
(責任編輯:張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