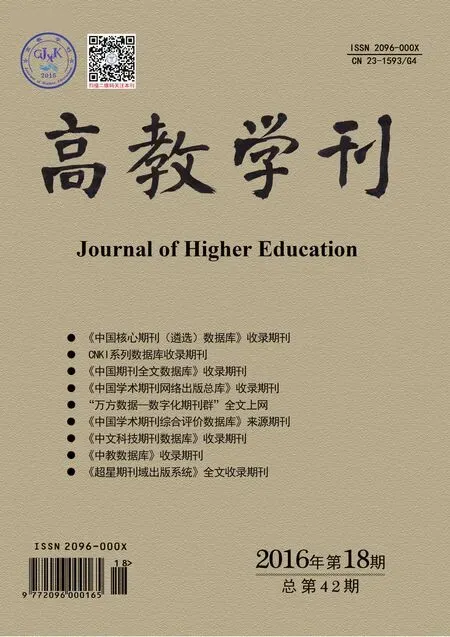社會學視角下的翻譯研究——以《飛鳥集》的翻譯為例
(遼寧對外經貿學院,遼寧大連116052)
(遼寧對外經貿學院,遼寧大連116052)
本文從社會翻譯學角度對泰戈爾的詩集《飛鳥集》的不同翻譯版本進行對比研究,分析鄭振鐸譯本和馮唐譯本的不同,從社會翻譯學的角度分析導致二者譯本不同的原因,從社會背景和譯者的慣習進行探討,從而揭示社會翻譯學研究對提高翻譯水平的促進作用,推動翻譯的發展。
社會翻譯學;譯者慣習;《飛鳥集》;鄭振鐸;馮唐
一、概述
《飛鳥集》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作品,當今國內出版的中文版的《飛鳥集》以鄭振鐸的譯本為主。鄭振鐸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是我國現代杰出的學者,在許多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其在翻譯領域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他對翻譯的主要貢獻在于對翻譯活動的大力倡導和對翻譯理論的積極探討。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詩集,有著廣泛的流傳和深遠的影響。鄭譯的《飛鳥集》最初的版本距今接近百年的時間,近來馮唐重新翻譯的《飛鳥集》出版后也受到社會各界的批判,最終出版社下架召回該書。兩人的翻譯截然不同。這與譯者本身的因素是分不開的。本文將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這兩種譯本不同的原因。
二、社會翻譯學的綜述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是法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近年來,翻譯研究逐漸從文化視角,到語言視角,進而過渡到了社會學的視角。譯界學者從社會學理論探討翻譯的問題已經成為焦點問題,促進并推動了社會翻譯學的理論建構。布迪厄所提出的關于習性、場域與資本的觀點,都可以應用到翻譯研究中,為社會環境制約下的譯者翻譯活動提供了新的解讀方法,為翻譯學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更為開闊的理論思維和視野,在翻譯研究領域可謂意義深遠。[1]
三、鄭譯和馮譯的風格以及其社會決定因素
鄭振鐸,出生于1898年12月19日,是中國現代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第一個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作品《飛鳥集》全譯本。鄭振鐸提出翻譯的兩種目的:一是能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二是能引導中國人到現代的人生問題,與現代的思想相接觸。鄭振鐸認為,翻譯應盡量忠實地呈現原作的原貌,他主張直譯為主,在必要的時候為了流暢則可采取意譯。鄭振鐸采用白話文來翻譯《飛鳥集》,為白話文的推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對我國新詩的改革與發展以及新文學的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今北京交通大學)學習。1927年旅居英、法。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這就是鄭振鐸的文化資本。鄭振鐸所倡導的是現實主義文學觀,他主張“為人生”的文學思想。他曾說過:“文學必須具有社會問題的色彩和革命的精神”。這便是文學場域和政治場域相互聯系的情況。
馮唐,1971年生于北京,詩人、作家、醫生、商人。曾經托福考過滿分。是一位優秀的中英雙語應用者,這是他做翻譯的文化資本。他在翻譯《飛鳥集》的過程中堅信民國時期的中文處于轉型期,而他現在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而且他固執的認為,詩應該押韻,并在翻譯過程中盡全力尋找最佳押韻。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場域之中的個體,內化了場域的規則,但沒有完全照搬了規則,而是學習了規則,在這種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馮唐有他自己的翻譯慣習,他的翻譯方法是以意譯為主,并沒有完全忠實于原文,反而加入了許多自我意識。馮唐在《飛鳥集》一書的后記當中寫到自己翻譯《飛鳥集》的譯者動機包含高額的稿費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在文學場域里的參與者們不能總是為了文學藝術而進行藝術創作,他們有時候也不得不考慮外在的許多因素,如名聲,經濟效益等,并且和其他的場域存在相互聯系。[2]
四、文本分析
1.原詩:I cannot tell why this heart languishes in silence.It is for small needs it never asks,or knows or remembers。
鄭譯:我說不出這心為什么那樣默默的頹喪著。是為了它那不曾要求、不曾知道、不曾記得的小小的需要。[3:24]
馮譯:我不知道,這心為什么在寂寞中枯焦。為了那些細小的需要,從沒說要,從不明了,總想忘掉。[4:37]
泰戈爾在詩中連用了三個并列的動詞短語,“never asks,or knows or remembers”,鄭振鐸將譯文也按照動詞短語來譯,他的譯文忠實于原文的語言風格,保留了原文的語言結構和表達方式,而馮唐譯詩偏愛押韻,所以他將這三組動詞詞組譯成“從沒說要,從不明了,總想忘掉。”末尾字押韻,且四字對等的詩文結構。體現了不同的譯者有著不同的慣習。從翻譯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如果原文語言文化規范與譯者自身慣習及譯文中相應主流規范不一致,則要從譯者自身慣習角度考慮其到譯語環境中相應規范的遵守與背離,及其相應的文化目的。鄭振鐸的目的是通過翻譯外國文學,把外國人的思想,情感和語言方式介紹給中國人,通過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化,豐富本國文化,提供新的語言素材,進而對白話文變革起到積極的作用。馮唐譯詩則是想體現個人的文學修養和文化水平,他將詩文押韻,使其讀起來更有語感和詩意。
2.原詩:That I exist is a perpetual surprise which is life。
鄭譯:我的存在,對我是一個永久的神奇,這就是生活。[3:18]
馮譯:我存在,是生命延綿不斷的精彩。[4:22]
鄭振鐸將這首詩的翻譯采用了“對譯”方法,即順序和原文一致。包括末尾的從句也是按照原有的順序來譯的。翻譯活動不會只發生在翻譯這一個場域之中,同時它還發生在其他場域中,與相關場域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在晚清時期,許多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注重文采,所以當時的翻譯風格以意譯為主,直譯則很少出現。到了鄭振鐸所在的五四運動時期,譯者同時也是新文學的建設者,他們的翻譯目的在于“西學東漸”。通過翻譯,傳播西方文化,進而改造中國的舊社會和促進新文學的發展。因此鄭振鐸認為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來翻譯西方文學,能夠忠實地反映西方文學的原貌,這樣更符合五四新文學建設者倡導翻譯文學的文化初衷和主要目的。而如今,在當下的文化場域中,已經不再是新文化運動的時期了。我們當下的譯文風格是以體驗多元文化為初衷,讀者在文化場域里也有訴求,希望提高翻譯作品的藝術欣賞性,馮唐的譯文便體現了這一點。同時,正因為現在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時期,所以馮唐有了一個自由翻譯的空間。兩位譯者身處不同的時代,翻譯目標不同,語言習慣也不同。
3.原詩:The world puts off it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鄭譯:世界對著它的愛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變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3:11]
馮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綿長如舌吻,纖細如詩行。[4:3]
譯者的慣習來源于翻譯場域中的規范以及譯者對自己在翻譯場域中的定位:是將自己定位為資深譯者還是年輕譯者,應該遵循傳統成名套路,還是有所創新、與眾不同。[2]鄭振鐸選擇忠實于原文,而馮唐認為翻譯更應該“有我”一些,他將自己的個人特色在翻譯中體現的很充分。馮唐將“mask”譯為“褲襠”,“揭下面具”改編成“解開褲襠”,這是馮唐對泰戈爾的理解,他認為對愛人表達愛意的方式就是這樣。馮唐已經突破了原有的翻譯語言的規范,甚至語言信息對等的規范,他沒有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中規中矩的譯者,而是把很多個人對詩人想要表達的情感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語言表達了出來。馮唐出版過很多書,但做翻譯還是第一次。作為一名資歷尚淺的譯者,馮唐在翻譯場域中沒有遵循原有的翻譯規范,他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顛覆傳統的翻譯之路,雖然很標新立異,甚至有點嘩眾取寵,但是這在翻譯當中不得不說是一種創新,一種突破。而這種創新也是譯者在翻譯場域中對自己的一種定位。
4.原文:The clouds fill the watercups of the river,hiding themselves in the distant hills。
鄭譯: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它們自己卻藏在遠山之中。[3:74]
馮譯:云把河的水杯斟滿,躲進遠山。[4:174]
從這首詩的譯文對比來看,我們能看出譯者的性格特點,鄭振鐸理性沉穩,馮唐感性抽象。兩版譯文都沒有翻譯意思上的問題,鄭振鐸認為“信”是翻譯的第一要義,所以他的譯文忠實于原文,譯句有點生硬,但是通俗動人。馮唐的譯句多了詩意,帶有個人色彩。從社會翻譯學研究方面來講,規范是被廣為接受的準則,而慣習則是譯者在翻譯以及其他各種場域之中培養而成的思維習慣和行為傾向。鄭譯忠實于原文,但現在已經不是“對等”的時代。翻譯活動不再是追求精確語言對譯的文化交流。在場域之中,競爭是最大的特點。想要在眾多譯本中脫穎而出,馮唐不僅要譯出自己的風格,也要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這種競爭也是場域得以形成、存在和發展的原動力。譯者將其本身的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以及名聲等象征資本。大眾對馮唐的這一版本的《飛鳥集》爭議較多,批評較多,贊譽聲也很多,這都可以使馮唐獲得名聲一類的象征資本。
五、結束語
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為我們開啟了觀察翻譯現象的新視角,以研究翻譯活動在國際社會文化背景之下的運作和規律以及在翻譯活動中各種參與者的行為表現和相互之間的聯系。借助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我們可以從一個更接近于翻譯本質屬性的角度來觀察和闡釋翻譯活動和譯者與社會、文化、全球化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2]社會上爭論馮唐《飛鳥集》的翻譯,不單單是對馮唐本人的批判,從另一種層面來講,這也是社會對文學的討論,對翻譯的討論。文化沖突和文學批評可以提高社會的創作與鑒賞水平,進而為提高中國翻譯水平做出貢獻。我們今天翻譯歷史的作品,首先有一個時代關系問題。譯者處在當今的社會文化中,應該要置身于原著及作者在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如不揣摩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作者的思想,譯者就不能準確掌握原作者的意圖,譯者作為一名再創作者,既要深刻了解原著的時代背景,也不能忽視現代社會環境和當今讀者心境的變化。翻譯經典也應該順應時代的潮流。
[1]李紅滿.布迪厄與翻譯社會學的理論建構[J].中國翻譯,2007(05).
[2]王悅晨.從社會學角度看翻譯現象:布迪厄社會學理論關鍵詞解讀[J].中國翻譯,2011(01).
[3](印)泰戈爾(Tagore,R).飛鳥集·新月集:漢英對照[M].鄭振鐸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1.
[4](印)泰戈爾.飛鳥集[M].馮唐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 7.
[5]劉立勝.文學翻譯系統規范與譯者主體性研究的社會學途徑[J].中州大學學報,2012(01).
[6]邵璐.翻譯社會學的迷思——布迪厄場域理論釋解[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3).
[7]張娟.從《飛鳥集》看鄭振鐸的翻譯理論與技巧[J].河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3).
[8]曾晶晶.以詩意入詩,翻譯理念的忠誠執行者——從《飛鳥集》看鄭振鐸的翻譯理念[J].科教文匯(下旬刊),2007(10).
[9]周桃元.譯者動機研究——以鄭振鐸譯《飛鳥集》為例[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4(06).
[10]靳哲.從譯本《飛鳥集》看鄭振鐸的語體歐化觀[J].科教導刊(中旬刊),2011(03).
[11]周心怡.鄭振鐸的翻譯精神及其理論[J].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5(08).
[12]王治國.譯介譯作并重,譯評譯論兼通——鄭振鐸翻譯理論研究[J].寧夏社會科學,2010(06).
社會學視角下的翻譯研究
——以《飛鳥集》的翻譯為例*
王乙涵 張麗敏
This paper makes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differ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agore's"Stray Bird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This paper analyze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Zheng Zhenduo and Feng Tang and discusses causes that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from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habits of translators,in hope of uncove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in improving translation level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habits of translators;"Stray Birds";Zheng Zhenduo;Feng Tang
I04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000X(2016)18-0261-03
本論文受遼寧對外經貿學院2015校級大創項目“英譯漢中制約譯者決策的社會因素”的資助(編號:B20150013),是該項目的成果之一。
張麗敏(1976-),女,遼寧大連人,遼寧對外經貿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漢語言文化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