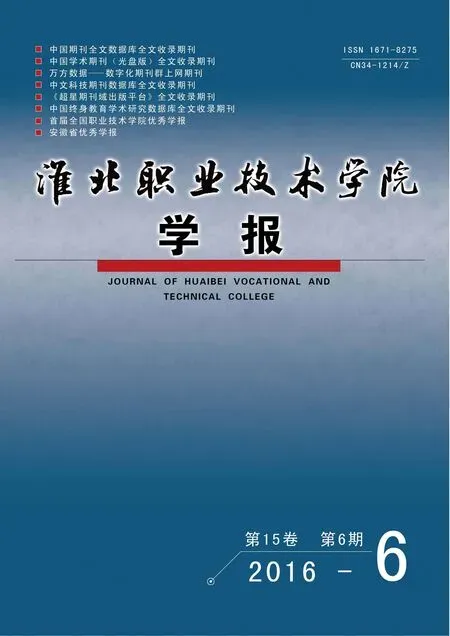“史”話人生
——魯迅與契訶夫作品中知識分子形象的新歷史主義解析
吳振華,程儒珺
(安徽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安徽 蕪湖 241003)
?
·文學(xué)與語言研究·
“史”話人生
——魯迅與契訶夫作品中知識分子形象的新歷史主義解析
吳振華,程儒珺
(安徽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安徽 蕪湖 241003)
在19—20世紀(jì)之交的中俄兩國,知識分子作為精英階層登上歷史舞臺,轉(zhuǎn)型期的他們也呈現(xiàn)出各式各樣的心態(tài)。他們生活困頓,卻思想活躍,比常人更敏銳地感受到來自社會的壓迫。新歷史主義注重研究文本產(chǎn)生的歷史文化語境,也注重考查文本對語境產(chǎn)生的影響。運(yùn)用新歷史主義來解讀魯迅與契訶夫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將文本與歷史相結(jié)合,從同而不同的人物類型中透析知識分子同而不同的生活狀態(tài)、心理狀態(tài),以期引起當(dāng)代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魯迅;契訶夫;知識分子形象;新歷史主義
魯迅與契訶夫,兩位文學(xué)史上的泰斗。他們同樣以現(xiàn)實(shí)主義為題材,擅長詼諧諷刺的藝術(shù)手法,文風(fēng)含蓄凝練、意味深遠(yuǎn)。魯迅也曾被譽(yù)為是“中國的契訶夫”。知識分子作為二者筆下的重要形象,具有符號化的個性特點(diǎn),值得引起當(dāng)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
一、同而不同的生活狀態(tài)
新歷史主義作為一門跨學(xué)科的實(shí)踐,模糊了文學(xué)與歷史、政治間的界限,它主張將文本當(dāng)做歷史著作來解讀一個時代的文化內(nèi)涵。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tǒng)理念下,知識分子一直是高雅文化的代表,理應(yīng)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然而,從魯迅與契訶夫的作品來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卻并非如此。他們不僅物質(zhì)上匱乏,而且精神上困惑,生活在社會邊緣,但潛意識里死守著固執(zhí)的地位意識,在痛苦與無奈里惶惶不可終日。
(一)物質(zhì)的匱乏與缺失
契訶夫在《柔弱的人》中借家庭教師尤利婭的行為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處境。結(jié)算工錢時,面對“我”的蠻不講理,她明知不公卻只是退讓妥協(xié),接過克扣后的工錢時還喃聲道謝“在別處根本一文不給。”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為了滿足生存而行竊,被打斷了腿,最終一命嗚呼;涓生與子君在金錢與現(xiàn)實(shí)面前分道揚(yáng)鑣;陳世成跟著幻覺里埋金的白光走上死路。
從新歷史主義強(qiáng)調(diào)的“文本的歷史性”來看,作品中反映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是以另一種方式來回歸歷史。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的中俄兩國都處于風(fēng)雨欲來的前夕,在改朝換代的背景下,知識分子不再是“四民之首”。轉(zhuǎn)型期的他們難以適應(yīng)社會變革,導(dǎo)致一部分人過上了食不果腹的生活。
適時,俄國的社會矛盾進(jìn)一步激化,革命運(yùn)動高漲。在戰(zhàn)火紛飛的狀況下肉體的滿足成了第一要義,知識分子這一精神職業(yè)就變得可有可無。且在19世紀(jì)下半葉,平民知識分子取代貴族知識分子占據(jù)文壇主導(dǎo)地位,他們又失去了背景的支持,所以才會出現(xiàn)《風(fēng)波》中女主人的胸針不知所蹤,家庭教師成為首要懷疑對象的情形。
當(dāng)時的中國和俄國有著相似的背景。《孔乙己》創(chuàng)作于1918年冬,“五四”運(yùn)動的前夕,辛亥革命雖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使得類似于孔乙己這樣的文人在新舊思想的夾擊下生存艱難。科舉制度的廢除也著實(shí)斷了一批知識分子的生路。“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shí)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生活實(shí)際,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官才能發(fā)大財(cái),發(fā)了財(cái)才能置田買地,榮宗耀祖。”[1]21而中國傳統(tǒng)文人則大多除了考據(jù)詞章、苦讀八股外一無所長,社會轉(zhuǎn)型讓他們成了無根之民,難以立足。
(二)精神的迷茫與困惑
十九世紀(jì)懶漢哲學(xué)在俄羅斯盛極一時。契訶夫創(chuàng)作了大批作品批評不思進(jìn)取、自甘平庸的社會風(fēng)氣,如戲劇《櫻桃園》《三姊妹》、小說《糖栗》《姚內(nèi)奇》等。《糖栗》中的尼古自從萌生擁有一座莊園的念頭開始,便極為吝嗇地生活,甚至為了錢和一個老寡婦結(jié)婚并把她逼上死路。當(dāng)他終于如愿以償后,在作者眼里他已經(jīng)變得像一頭豬“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見一條紅毛的肥狗,活像一頭豬。它想叫一聲,可又懶得叫……他老了,胖了,皮肉發(fā)松,他的臉頰、嘴唇、鼻子,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豬那樣咕咕叫著鉆進(jìn)被子里去了。”[2]744契訶夫尖銳地批判了無意義的庸常生活:“只需要三俄尺地的不是活人而是死尸。”“人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三俄尺土地,也不僅僅是一個小莊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3]285,286呼吁人們從莊園中跳出來,去追尋精神上更廣闊的天地。
相較于尼古這一類無所事事的人,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則“更勝一籌”。他們不僅無法實(shí)現(xiàn)抱負(fù),更與原先的理想背道而馳。
《孤獨(dú)者》中的魏連殳本是一名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當(dāng)他剛毅不屈、堅(jiān)持本真時,他過得窮困潦倒。當(dāng)他無可奈何成了軍閥的顧問時,又立刻成了人人口中的魏大人。“我已經(jīng)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jīng)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4]103魏連殳身上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的依附思想。依附或寄生于外在體系,如古代靠依附皇權(quán)來生存的“士大夫”等。“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沖突的尖銳化,又使得許多知識分子樂意充當(dāng)某個階級或利益集團(tuán)的‘代言人’,與社會有了某種固定的精神或物質(zhì)利益上的有機(jī)聯(lián)系,這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有機(jī)的’知識分子。”[5]8,9但同樣是精神上的困惑,契訶夫與魯迅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又采取了不同的態(tài)度來面對。
契訶夫筆下的知識分子,大多如上述所言索性不管不顧,這類人中典型的有尼古、姚內(nèi)奇等。一部分有著清醒覺悟的知識分子,則無力面對社會的黑暗而走向極端,呈現(xiàn)出明顯的兩極化傾向。“矛盾、好走極端、搖擺的性格在俄羅斯人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乃至整個俄羅斯文化都呈現(xiàn)出以“二元論”為基調(diào)的雙重性。”[6]這與俄國的社會歷史密不可分。動蕩和間歇伴隨著俄國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反復(fù)性。長此以往,俄國民眾對社會改革和劇變習(xí)以為常,形成了極強(qiáng)的適應(yīng)能力。同時,俄國的地理位置又決定了它注定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具有強(qiáng)烈的自我意識,使得“俄羅斯民族在溫順和反抗中勢必要走向極端。”[6]
而魯迅作品里的知識分子則更具有復(fù)雜性。同樣以魏連殳為例,他先是為了自己而活,后是為了“愛我者”而活,最后為了敵人,那些不愿他活著的人而活著。他不惜以丑對丑,以惡抗惡,以自我毀滅為代價(jià),在臨終前用生命發(fā)出報(bào)復(fù)似的反抗。哪怕到死他也“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4]110他嘲笑眾人,嘲笑社會,也在嘲笑著他自己。這是一種飛蛾撲火似的毀滅性的復(fù)仇,滲透出善惡交錯的復(fù)雜人性。
(三)社會話語權(quán)的轉(zhuǎn)變
19世紀(jì)的俄國文學(xué)中出現(xiàn)了以貴族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多余人”形象。他們家境殷實(shí),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渴望用西方的理論來救亡圖存,可由于貴族階級的局限性讓他們以失敗告終。19世紀(jì)下半葉,平民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就一定能扭轉(zhuǎn)局面嗎?契訶夫就顛覆了這一主流觀點(diǎn)“根據(jù)這一切就足以做出一個結(jié)論:大小酒館不可取消,至于要不要學(xué)校,倒是要考慮考慮。[7]48
而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則呈現(xiàn)出波浪式變化的特點(diǎn)。在古代,士在各方面都享有一定特權(quán)。一方面科舉制讓讀書人有機(jī)會步入仕途,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又賦予他們使命感,讓他們在潛意識里不自覺地處于社會中心。到了近代社會,士逐漸被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取代。“五四”時期,西學(xué)滲透,陳獨(dú)秀提出“以歐化為是”,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新式學(xué)堂盛極一時。隨著印刷業(yè)的發(fā)展,報(bào)刊雜志大量發(fā)行,文學(xué)社團(tuán)林立,呈現(xiàn)出一片繁榮的景象。但到“五四”落潮之后,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則又急劇下降。原因在于這些啟蒙者如同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一樣,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少數(shù)文化精英,而被啟蒙者則大多是沒受過太多教育的勞苦大眾,這就在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形成一層隔膜。此外,“五四”運(yùn)動本身的“全盤西化”與民眾固有的傳統(tǒng)思想間又形成一個斷層。這不僅預(yù)示著五四運(yùn)動的失敗,更預(yù)示著得不到民眾支持的知識分子注定會走上被邊緣化的道路。
二、同而不同的人物類型
新歷史主義認(rèn)為歷史并非連續(xù)的,而是充滿了斷裂、張力與偶然。人的本質(zhì)也是不穩(wěn)定的,是一個不斷塑形的過程。按照人性不斷進(jìn)步的動態(tài)歷程,本文從兩個角度,四個類型來敘述魯迅與契訶夫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展現(xiàn)他們殊途同歸的悲劇命運(yùn)。
(一)昏睡者
適時,中俄兩國的悲劇在于一方面這是一個充滿壓迫的時代,另一方面又由于國民的昏睡,反過來延長了封建社會的壽命。契訶夫和魯迅筆下的昏睡者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代表,封建思想早已內(nèi)化在他們腦中,使他們沉沉睡去,不愿醒來。
1.恐懼變革的封建知識分子
《套中人》是契訶夫?yàn)槿朔Q道的名篇之一。他用夸張、漫畫的筆調(diào)創(chuàng)造了一個終日惶惶不安的希臘語教員——別里科夫的形象。但凡出門,他總是隨身攜帶雨鞋、雨傘,把頭縮進(jìn)衣領(lǐng)里。除了把肉身藏起來,他還把思想也藏在一個套子里。他害怕看見一切新事物,生怕出什么亂子,成了一個死心塌地維護(hù)沙皇統(tǒng)治的典型。除了套住自己,他還想套住別人,要求別人和他一樣躲進(jìn)套子里去。
無獨(dú)有偶,1919年的中國,科舉制度雖然早已廢除,但封建倫理道德早已內(nèi)化在國民的腦海里。魯迅寥寥數(shù)筆刻畫了一個被建科舉制度異化了的孔乙己形象。“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bǔ),也沒有洗。”[8]458他堅(jiān)信科舉是唯一出路,整天滿嘴誰也聽不懂的之乎者也。他的之乎者也,是他死守的人生信仰,也是他在現(xiàn)實(shí)面前挽救尊嚴(yán)的救命稻草。但他的存在只是為了使人快活,沒有他別人也是這么過。
別里科夫、孔乙己都是被封建思想異化了的代表,但從新歷史主義的角度來看卻又存在極大的不同。權(quán)力、強(qiáng)化、顛覆是新歷史主義探討的永恒的話題。“強(qiáng)化主要指統(tǒng)治秩序?qū)で蠓€(wěn)固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手段;顛覆則針對這一秩序;而含納指對明顯的顛覆力量的包容。”[9]52別里科夫作為一位古希臘語教員,有著自給自足的社會地位,他依靠政府來自保。表面看來荒謬只是他的個人行為,但他背后卻站著更多的人,他隱喻著封建農(nóng)奴制。所以他不斷采取“強(qiáng)化”的手段來鞏固自身意識形態(tài)。而孔乙己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使人快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背后缺少有分量的社會話語的支持,所以他成了別人肆意嘲弄的對象。
2.道貌岸然的偽君子
在眾多昏睡者中,除了恐懼變革的封建知識分子,還有一批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們滿嘴仁義道德,實(shí)際上卻是復(fù)古的封建衛(wèi)道士。
《偽裝的人》里,律師在法庭上宣稱“如果她(被告)被宣判有罪,那他會因悲痛而死去。”心里卻又想著“要是原告給我的錢比她多一百盧布,我就把她送進(jìn)監(jiān)獄。”[7]48《高老夫子》中的主人公模仿高爾基改名為高爾礎(chǔ),實(shí)際卻是個不學(xué)無術(shù)的市井小民。《肥皂》里的四銘高呼女學(xué)和女人剪頭發(fā)不成體統(tǒng),實(shí)際卻是男盜女娼的思想在作祟。
這三者的出現(xiàn),具有鮮明的社會烙印。以《高老夫子》為例,它完成于1925年——女師大風(fēng)潮迅速激化的時期,一批女大學(xué)生勇敢地走向街頭尋求個性解放,卻遭遇了嚴(yán)厲的打擊。所以小說中的人物都感慨女大學(xué)生“不成體統(tǒng)”。且在二十年代,中國曾掀起了一陣復(fù)古的潮流。以學(xué)衡派為代表,大力提倡“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主張文學(xué)復(fù)古。五四運(yùn)動的爆發(fā)雖已掃清了一大批封建主義,但仍有部分封建殘余穿著西化的表皮,成為阻撓革命的主要力量。正如魯迅在《破惡聲論》里提出“偽士”的觀點(diǎn):他們本是“無信仰之人士”,卻又“以他人有信仰為大怪,舉喪師辱國之罪,悉以歸之。”[12]30自身無信仰,卻又阻礙別人的信仰,并表演出一副有信仰的姿態(tài),甚至妄圖建立起一套他人都必須尊崇的“信仰”。他們一方面高喊著仁義道德、一面卻借機(jī)來滿足個人私欲。他們不斷表達(dá)對民不聊生的痛心疾首,實(shí)際卻延緩了社會進(jìn)步的步伐,成了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的代表。
(二)清醒了卻無處可走的人
1.彷徨、動搖、不斗爭的知識分子
有一部分清醒了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卻如哈姆萊特般困惑與彷徨。他們既受到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能夠清醒地認(rèn)識到時代的弊病,但對本國文化又有著狂熱的依戀。夾縫中的他們延宕不安,在矛盾與掙扎里含恨而終。
契訶夫的代表作《第六病室》講述了一位被分配到第六病室工作的醫(yī)生拉京的遭遇。可當(dāng)他第一天就職時就發(fā)現(xiàn)這個慈善機(jī)關(guān)糟透了。醫(yī)院不僅陰森如監(jiān)獄一般,還不時發(fā)生向病人勒索錢財(cái),毆打病人、強(qiáng)奸女病人的情形。但不久,他對此就麻木冷漠了。性格懦弱的他不相信憑借一己之力能改變環(huán)境。生活厭倦的拉京,慢慢沉溺于哲學(xué)、文學(xué)無法自拔,整天說一些誰也聽不懂的大道理。漸漸地,人們認(rèn)為他瘋了,最終將他也關(guān)進(jìn)了第六病室。
拉京的形象有符號化的特點(diǎn)。他心知肚明醫(yī)院的不合理,卻用息事寧人來茍活于世。他寧可研究空洞的理論,假裝看不見現(xiàn)實(shí)來逃避精神上的自責(zé),也不愿做出點(diǎn)實(shí)事。他所熱衷的哲學(xué)理論是他自我逃避、自我安慰、自我救贖的借口,以此掩飾他彷徨動搖的事實(shí)。
《第六病室》的創(chuàng)作與社會環(huán)境密不可分。適時俄國普遍流行托爾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惡”的觀點(diǎn)。民粹派失敗,大肆鼓吹時機(jī)尚未成熟需要等待。契訶夫借拉京這一形象表達(dá)了他的態(tài)度,即一味退讓容忍只會助紂為虐,自食惡果。他曾寫道:“為什么要等待……我一個有思想的活的人站在一道溝前,本來我可以跳過去,或者架一座橋走過去的,可我偏要等著他自己合攏,或者等著淤泥把他填滿,這樣做有什么規(guī)律和合法性可言呢?[3]294《在酒樓上》的呂韋甫,也曾是新文化運(yùn)動的傳播者,在革命落潮后只得感慨人生就像蒼蠅“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diǎn)。”[4]27相較于拉京還未革命就打退堂鼓,呂緯甫的彷徨則是在窮途中顯現(xiàn)。魯迅在這里選取了文學(xué)與歷史重疊的部分,表現(xiàn)了一批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五四運(yùn)動前被各種思潮吸引而投身革命。但當(dāng)革命走向低潮時,他們心中的熱情也逐漸減少,變得隨隨便便、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在自我嘲諷、自我申辯又自我否定中度過一生。
從新歷史主義的角度來看,拉京和呂韋甫的結(jié)局似乎早已注定。因?yàn)楫?dāng)他在表達(dá)沉默的時候,就已經(jīng)在無形中站到了敵對的那邊。《第六病室》里醫(yī)生和病人之間是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哪怕病人身體健康甚至有著遠(yuǎn)見卓識,也處于被統(tǒng)治狀態(tài)。拉京作為一個可能存在的顛覆力量,卻又成了權(quán)力的產(chǎn)物,延長了權(quán)力的壽命。呂緯甫也是如此。正如H.阿蘭穆·威瑟所言:“揭露、批判和樹立對立面時所使用的方法往往都采用對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淪陷為自己所揭露的實(shí)踐的犧牲品。”[10]1
2.奮力抗?fàn)巺s走投無路的知識分子
除卻昏睡者和具有妥協(xié)性的知識分子外,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勇于沖破牢,籠奮力抗?fàn)帲豢上觳凰烊嗽浮?/p>
《新娘》中整日無所作為的安德烈伊奇腰纏萬貫,追求自由生活的新青年薩沙卻成了別人眼中的浪子。《精神錯亂》里的法律系學(xué)生在與同學(xué)一起參觀了幾家妓院之后,對妓女和嫖客們的麻木大失所望,然而朋友卻以為他患了精神病。
20世紀(jì)初,魯迅受到《第六病室》的啟發(fā),創(chuàng)作了《狂人日記》與《長明燈》。《狂人日記》里的狂人患有被迫害妄想癥,無時無刻不在懷疑周圍人想加害于他。《長明燈》里的瘋子想要熄滅代表封建文化的長明燈不成而被囚禁起來。狂人和瘋子都是有著進(jìn)步思想并對社會有深刻認(rèn)識的知識分子,但從“狂人”“瘋子”的稱呼來看就暗示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所受到的對待。
《第六病室》《狂人日記》《長明燈》都描寫一個有病的時代,展現(xiàn)了思維僵化甚至病態(tài)的人們在外面自由行走,而有著進(jìn)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卻被關(guān)了起來的社會情形。但三者又截然不同。
《狂人日記》的小說開頭,已介紹了狂人“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bǔ)矣。”[8]444狂人的痊愈,是他已被同化的體現(xiàn)。且《狂人日記》采取了日記體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當(dāng)一個狂人開始書寫瘋癲,他卻是已經(jīng)站在了理性的立場。“瘋癲的每一次再現(xiàn),每一次刻畫瘋癲對理智的抵抗的嘗試,都是站在理智的角度書寫的……看起來是從瘋狂的角度對瘋狂的再現(xiàn)來威脅和顛覆理智,但事實(shí)上卻是復(fù)制了理智統(tǒng)治瘋癲的語言結(jié)構(gòu)。”[11]94,95而《長明燈》則很好地避免了這一點(diǎn),所以瘋子比狂人的抗?fàn)幐油笍亍?/p>
由此看來,在時的中俄兩國,受到思想啟發(fā)的知識分子即便已經(jīng)覺醒并渴望拯救社會,也面臨四面八方的阻礙,舉步維艱。
首先他們會受到反動政府當(dāng)局的壓力,以官方意識形態(tài)限制他們思想和行為。其次,深受封建思想侵害的民眾如《長明燈》中全屯里的人們,《傷勢》中的“雪花膏”等也會施加影響。魯迅稱他們?yōu)闊o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tuán)。他們依靠固有觀念,憑習(xí)慣行事,將新事物作為異端扼殺在搖籃里,這也從側(cè)面反映出一定時期內(nèi)的接受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舊思想迷了心的民眾有時候有著更大的力量。他們以“祖宗之法”和“救你于水火”的理由,于潛移默化之中放無刃的冷箭,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再次,不同政治觀點(diǎn)的知識分子之間也會相互阻礙,甚至造成兩敗俱傷。最后,知識分子要面對來自他們自身的考驗(yàn)。清醒之后,貧困、孤獨(dú)都將接踵而來。就像子君在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之后,因無法面對愛情的缺失與生活的困頓,只能回到家中走向死亡。綜上,諸多種種,都讓知識分子即便在清醒之后仍然舉步維艱。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和契訶夫都深深認(rèn)識到無法僅靠知識分子來改革社會。
三、當(dāng)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
新歷史主義認(rèn)為,文學(xué)與歷史是一種互文的關(guān)系,社會環(huán)境不僅能對文學(xué)產(chǎn)生影響,文學(xué)作品也能傳遞某種意識形態(tài),從而改造社會。這是一個相互纏繞循環(huán)的過程,所以統(tǒng)治者常常嚴(yán)格控制文學(xué)作品的出版。
無論是魯迅、契訶夫或是其他作家,他們創(chuàng)作的初衷,都是希望通過作品在文本與歷史的互動中構(gòu)建一個更為明朗的社會。就像魯迅先生把自己定義為“歷史的中間物”,“自己背著因襲的重?fù)?dān),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8]135透過他們的作品,更能讓當(dāng)代知識分子自我反思,為當(dāng)下遇到的問題尋找出路。
首先,從定義來看,當(dāng)下知識分子已成了教授、院士、最起碼以大學(xué)生為底線的一類群體的代名詞。這反映出知識分子學(xué)院化的傾向加劇。而當(dāng)下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尤其是農(nóng)民階級之間的隔膜太深,普通民眾對知識分子抱有敬畏而“望而卻步”,知識分子自身專注于學(xué)術(shù)研究而缺乏公共性。久而久之知識分子被“隔離化”甚至“神魔化”,如將“女博士”作為一個帶有調(diào)侃色彩的詞語,知識分子被割裂開來,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
其次,知識分子是否敢于發(fā)聲,成了如今關(guān)注的又一焦點(diǎn)。自古以來的知識分子似乎都扮演著流亡者的角色,從屈原到陶淵明,再從杜甫到魯迅,知識分子理應(yīng)擁有獨(dú)立的人格和批判的思想。但他們內(nèi)心的爭吵、纏繞和消解又確實(shí)存在。《孤獨(dú)者》中“我”和魏連殳的三次辯論,不如說是作者和自我的三次辯駁。“我不應(yīng)該將真實(shí)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yīng)該永久奉獻(xiàn)她我的說謊。”[4]130這除了是愛與不愛的抉擇外,更是知識分子在虛偽和真實(shí)之間徘徊而獲得的道德譴責(zé),然而無論是說與不說,真實(shí)還是說謊,帶來的都不是卸下重?fù)?dān)的自由,而是另一種虛空的存在。批判,是知識分子的本質(zhì),但這發(fā)聲與否完全得靠自愿,任何人都沒有資格站在道德的制高點(diǎn)上去勸解或指責(zé)別人。“但我并不想勸青年得到危險(xiǎn),也不勸他人去做犧牲,說為社會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鐫起銅像來。自己活著的人沒有勸別人去死的權(quán)利。”[12]229
四、結(jié)論
19—20世紀(jì)之交的中俄兩國,知識分子演繹了一曲跌宕起伏的時代悲歌。作為文化精英的他們,理應(yīng)比民眾站得更高,比政府看得更遠(yuǎn),可實(shí)際上他們卻逐步走向邊緣化的道路,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是對歷史的反映和回歸。透過知識分子形象,契訶夫更加注重對社會制度的批判,魯迅則更多地暴露了傳統(tǒng)文化的弊端,但二人都深深認(rèn)識到無法僅靠知識分子來改革社會。魯迅與契訶夫所處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但他們的作品與精神永垂不朽,透析魯迅與契訶夫的作品,希冀能引起當(dāng)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思考與自我探索,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1] 任建樹.陳獨(dú)秀大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契訶夫.契訶夫小說選[M].汝龍,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9.
[3] 契訶夫.契訶夫短篇小說集[M].央金,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
[4] 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5] 許紀(jì)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5.
[6] 田晶.俄羅斯“雙重性”民族性格研究:以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為例[D].蘭州:蘭州大學(xué),2010.
[7] 契訶夫.契訶夫作品集[M].左少興,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
[8]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9] Jonathan Dollimore.Shakespeare,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m[M]//in Richard Wilson and Richard Dutton,eds.,New Historicim and Renaissance Drama.Harlow:Longman,1992.
[10]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M].London:Routledge,1989.
[11] 石堅(jiān),王欣.似是故人來:新歷史主義視角下的20世紀(jì)英美文學(xué)[M].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08.
[12] 魯迅.魯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責(zé)任編輯:之 者
2016-08-02
本文系2015年安徽師范大學(xué)國家級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訓(xùn)練項(xiàng)目計(jì)劃“‘史’話人生——魯迅與契訶夫作品中知識分子形象的新歷史主義解析”(編號:201510370090)階段性研究成果。
吳振華(1964—),男,安徽宿松人,教授,博士,碩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中國文學(xué)及詩學(xué);程儒珺(1994—),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漢語言文學(xué)(非師范)專業(yè)2013級學(xué)生,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I042
A
1671-8275(2016)06-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