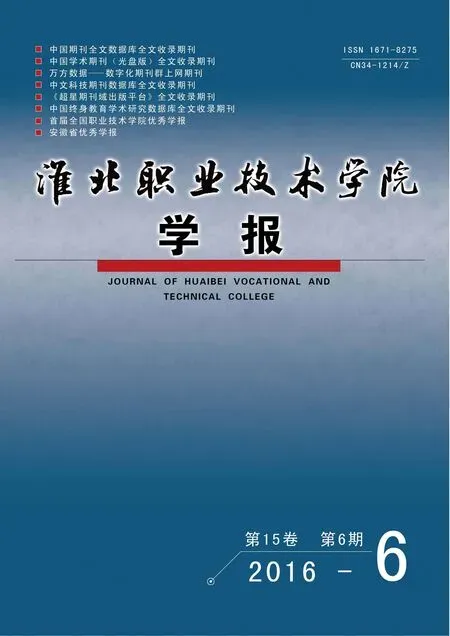事實、程序與公正
——基于“雷洋事件”的反思
張璇孟
(中共湖州市委黨校 法學研究所,浙江 湖州 313000)
?
事實、程序與公正
——基于“雷洋事件”的反思
張璇孟
(中共湖州市委黨校 法學研究所,浙江 湖州 313000)
備受輿論關注的“雷洋事件”,給社會公眾帶來了又一次深刻的集體記憶。公眾關注“雷洋事件”,應當遵循“追問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的邏輯。只有事實,才能支撐起公正的目標。事實真相、公平正義也是刑事司法的兩大核心價值。而公平正義是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統一。這兩者的地位原本是并重的,但在當下的中國,或許應當給予程序正義更多的關注,因為我國已發現和糾正的冤錯案幾乎都是“刑訊逼供”的苦果。由此,實現公平正義,不僅要關注執法依據的正當性,也不能忽視執法程序的正當性。
雷洋事件;事實;公正;正當性
2016年5月7日晚21時左右,公民雷洋離家前往首都機場,迎接預計當晚23點30分到達的幾位親戚,他們專程來看望雷洋剛出生半個月的女兒。此后,雷洋手機一直處于無人接聽狀態,直到2016年5月8日凌晨1時,雷洋家人再次撥打雷洋手機,接電話的卻是昌平東小口派出所警察,要求他們趕赴該派出所。1時30分左右趕到后,雷洋親屬被警方告知,雷洋因涉嫌嫖娼,在被警察帶往派出所的途中因心臟病突發死亡。[1]“雷洋事件”迅速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接受不了這個現實,死亡過程接受不了,我希望警方公布執法儀,讓我們了解整個過程。”在2016年5月10日的央視新聞中,雷洋妻子簡短的話語道出了普通公民對刑事司法最基本的需求——事實與公正。這個冷靜的明確表態,去除了媒體的浮躁,也促成了社會公眾對“雷洋事件”事實真相以及程序是否正義的理性追問。
一、無事實即無公正:“雷洋事件”中警察執法所依據的事實不確定
雖然雷洋事件的完全真相仍在逐漸還原過程中,但在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官方微博上,可以看到兩份關于“雷洋事件”的情況通報,是目前為止對這起事件來龍去脈最初的官方信息,值得關注、分析。
(一)一般違法行為應有與其性質相當的治理結構
從昌平警方的通報中可以得知,雷洋的涉黃行為并沒有抓到現行,僅是警方的一個懷疑。可即便是涉黃,也只是一般違法行為。涉黃行為尚未開始或已經完結、或涉黃行為正在進行,其執法方式應當有所區別。涉黃行為尚未開始即因警察的執法行為而放棄的人,屬于涉黃未遂,應當著重口頭教育;而涉黃行為在警察執法時已然終止的,剩下的就是對涉黃當事人進行處罰,即便當事人有逃脫的行為,是不是務必使用暴力將其制服呢?就像雷洋,假設警方的懷疑最終被認定,雷洋的確有涉黃行為,但歸根結底,他違反的只是《治安管理處罰法》,是不夠刑事處罰的輕微違法行為。雷洋是北京市民,不是流竄犯,不會消失;不是暴力犯,對他人沒有直接的社會危害。他今天逃脫了,警方就沒有抓他并依法處置的機會嗎?再者,按照警方的通報,警方對雷洋采取了“強制約束措施”。可是,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約束性保護”只能針對有危害性的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況且,此案執法當時,警方含協警在內一共五個人,并帶有警械。這些受過專門擒拿訓練的人,面對一介書生,怎用得著如此大動干戈?
(二)治安管理處罰應以何種“事實”為依據
作為國家法律強制力的具體實施者,警察是國家暴力的合法使用者,但暴力程度的選擇必須與違法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以及行為性質相適應。對此,《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條有明確規定,“治安管理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應當公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辦理治安案件應當堅持教育與處罰相結合的原則。”的確,倘若警察執法的暴力程度得不到有效控制,難免人人自危。
實際上,就事實而言,前面說的都只是一種假設,警察的判斷還有錯誤的可能,雷洋根本就沒有涉黃,只是很不幸走進了警方為掃黃而設立的蹲點圈。一個守法公民因此而死在抗拒警察執法的名義下,豈不是嗚呼哀哉。由此可見,警察依據自己的主觀判斷進行涉黃執法的模式讓警察陷入了困境。警察判斷錯誤的可能性或許很小,可一旦發生,對行政相對人及其親人卻是100%的傷害,同時也會傷及執法警察自身和警察隊伍的公信力。從這個角度看,筆者理解,“治安管理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中的“事實”應當是“客觀事實”,而非“法律事實”,更不是“主觀事實”。司法行政人員依法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應當達到與案件客觀的本源事實相一致。沒有客觀事實即行執法,何談公正?
二、無程序即無公正:“雷洋事件”中警察作為的程序缺陷
結合昌平警方發布的兩份情況通報和《雷洋死亡當晚到底發生了什么?央視記者專訪當事民警》的相關報道,公眾輿論反應強烈,提出了許多質疑,尤其是針對警察執法的程序有諸多疑問。
(一)如何看待警察執法時身著便衣和突擊審查
根據昌平警方發布的兩份情況通報,經辦民警當時是身著便衣,在盤問時遭到雷洋質疑。不穿警服、不戴警號、不開警車,沒有明顯的執法標識、在車上“突審”、和處于明顯弱勢的行政相對人發生激烈的肢體沖突等等,這些都不符合治安行政執法的法定程序。社會安定離不開警察,警察職業的艱辛性和高風險性眾所周知,他們的確需要基本的職業安全保障。警察著便衣可能有利于自身的安全和行政執法、刑事偵查的效率,但客觀上也容易造成公民認知上的混亂,有悖于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因此,相關法律應當明確哪些特殊類別案件的偵查可以著便衣,否則,從事行政執法、刑事偵查行為時,一律著警服。
(二)警察執法過程是不是應當多方記錄
雷洋事件發生在晚上,但是在公共場合,應當會有記錄。可現在,案發時的細節之所以得不到還原的重要原因,據說是因為警察沒有帶執法記錄儀。而北京市公安局早在2010年就全面推行執法記錄儀制度,每一次出警都必須使用執法記錄儀記錄出警全過程,這是民警執法時必須遵守的程序和必須履行的義務。更匪夷所思的是,雷洋出發小區和經過小區的視頻監控據說都被損壞,就連用于拍攝的警察的手機和雷洋的手機據說也在沖突時被摔壞。事實真相無法還原,如何能證警方清白呢?再加上雷洋已死,上述這些“據說”都只是涉案警方的一面之詞。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檢察”發布,檢察機關對北京明正司法鑒定中心作出的鑒定意見進行了審查,組織了專家審查論證、文證審查,確定死者雷洋符合胃內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涉案警務人員在執法中存在不當行為,昌平公安分局東小口派出所副所長邢某某、輔警周某起主要作用,且在案發后有妨礙偵查的行為。根據其行為性質和辦案實際需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已報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批準變更強制措施,對邢某某、周某以涉嫌玩忽職守罪依法決定逮捕。此信息對前期公眾的部分判斷予以了確認,相信正義不會等待太久。
(三)涉案警方發布雷洋事件信息的行為缺乏法律上的正當性
雷洋涉嫖和雷洋意外死亡是兩起案件。即便雷洋涉嫖,作為一位已逝的普通公民,警方沒有任何發布其涉嫖細節信息的必要。涉案警方如此罔顧雷洋個人隱私及其親屬的悲痛、自尊,不避嫌疑地、大張旗鼓地通過各種媒體,多方佐證雷洋涉嫖這種違背社會道德的事情,使雷洋的家人在承擔其猝然離世的悲痛之外,還可能面臨來自社會不屑的另外一份壓力。這種明顯缺乏人文關懷的做法難免令社會公眾反感。而倘若雷洋涉嫖不成立,那么涉案警察對雷洋涉嫖案來講,就是涉嫌濫用職權的當事人。對雷洋之死來講,就涉嫌故意或過失傷害他人致死。涉案警察是兩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眾所周知,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昌平警方第一次發布情況通報尚可,在“昌平區人民檢察院已介入并開展偵查監督工作”之后不僅不應當再單方面通過媒體向公眾發聲,更應當主動回避偵查。由此,涉案警方第二次公開發布雷洋事件信息的行為因明顯缺乏法律上的正當性而主動把自己送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警察作為專業刑偵人員,同樣具有極強的反偵查能力和輿論的引導能力。通報二提到的“經審查并依法提取、檢驗現場相關物證,證實雷某在足療店內進行了嫖娼”,這些偵查行為都是雷洋死后進行的,公眾完全可以合理懷疑這是故意地反偵查行為。更何況,就涉案警方自己多次公布的信息來看,本身也存在著一些細節上的模糊和前后的不一致,其結局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三、“雷洋事件”對實現刑事司法價值的有益啟示
依據哲學上對價值的主客觀關系的定義方法,刑事司法的價值就是刑事司法對客體此方面最基本需要的滿足。它是一個多元與沖突共存的體系,有著鮮明的層次性。比如自由與秩序,公正與效率等。通過上述對“雷洋事件”的相關分析,筆者以為,公平正義是公眾對刑事司法最基本的需求,而要實現公平正義,必須最大限度地還原事實真相。所以,事實和公正是刑事司法價值的核心追求。還原事實真相,實現公平正義需要一系列的條件,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法制的良善性是前提
針對“雷洋事件”,公眾輿論也探討了一些有爭議的制度。首先是涉黃違法行為的特殊處理機制。許多人質疑,在查處黃賭毒之類的治安違法行為之時,警方為什么常常會選擇像對待暴力犯罪分子一樣強烈的執法方式,而且熱情頗高、屢禁不止呢?實際上,這或許和警察職業內在的矛盾密切相關。從法社會學的角度看,警察是公共安全服務的提供者。可是,警察這類服務人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此類服務者提供服務的手段是監督、管制、甚至是強制那些享受其服務的人們,并以暴力作為服務工具。實際上,警察在提供服務、履行職責的過程中風險很大,甚至會失去生命。但作為國家暴力的行使者,很難消除他人對警察暴力本能地恐懼,這也決定了警察的公共服務很難總是贏得公眾的滿意。這種尷尬身份反過來又容易激發警察某種潛意識的抵觸情緒,一旦遇到反抗,就可能失去對暴力程度的掌控。這種矛盾在對雷洋事件的社會回應中也得到體現。警方及其家屬的宣言是,沒有警察,看以后誰來執法保護你們?而公眾的宣言是,警察怎能不僅不保護我們,反而帶頭傷害我們呢?如此,警民關系的惡化,再加上警察系統“重限期破案率、重降低犯罪率,輕程序瑕疵和手段正當性”的評價考核體系,都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警方越軌行為的產生。經雷洋事件,社會公眾又提出了一種觀點,警察之所以對黃賭毒之類的治安違法行為樂此不疲,并熱衷于使用暴力,是因為有可能帶來高昂的罰款收入以及各種不菲的利益。對涉黃行為的懲罰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涉黃者不僅要受到罰款,還要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以及由于親人的失望而帶來的羞恥自責,更可怕的是還可能有來自單位的諸如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之類的處罰,個體的命運甚至由此發生根本轉折。如此,涉黃行為一方面給涉黃者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警察作為執法者對涉黃者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處罰邏輯也帶來了雙方之間難以化解的敵意。因此,除了就雷洋之死給個事實真相之外,更重要的是建構對涉黃之類的一般違法行為合適的處罰方法和適當的執法方式及其落實的保障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既保護警察,又保護社會公眾。
其次是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廢之爭。2013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已實施50多年、備受詬病的勞動教養制度終于被依法廢止。可與勞動教養相類似的收容教育制度卻仍在實施,引發爭議。收容教育制度雖然被定義為行政強制教育措施,但收容教育期間被處罰人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從這點看,它和拘留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問題的關鍵一是收容教育的主管部門只有公安機關,獨此一家,自己做決定,自己執行,沒有任何監督制衡的機制。再加上收容教育缺乏可操作性的執行標準,各個省份針對同類的行為,處罰尺度大相徑庭。同等情況不同處罰,明顯違背了處罰公正原則。二是《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也規定,對賣淫、嫖娼人員,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六條的規定處罰外,對尚不夠實行勞動教養的,可以由公安機關決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期限為六個月至二年。可以由公安機關決定收容教育的前提條件是“尚不夠實行勞動教養的”,也就是從情節和處罰力度上都輕微于勞動教養。現在勞動教養都已經廢除了,收容教育當然也屬于自然廢除的行列。所以,在現階段收容教育無論是在程序方面,還是在實體方面都支撐不了公平正義,理應廢除。
“相應于城邦政體的好壞,法律也有好壞,或者是合乎正義,或者是不合乎正義。[2]148亞里士多德非常關注法制的良善性,將其作為法律制度內在的精神要求。由此,筆者以為,法制的良善性是實現刑事司法價值的前提。
(二)程序的法定性是基礎
不可否認,“重實體、輕程序”仍是我國現階段不可忽視的一種刑事司法理念。只要結果是公正的,不論通過什么手段實現。事實上,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應當是并重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但就我國司法實踐看,已發現和糾正的冤錯案幾乎都是“刑訊逼供”的苦果。由此,在當下的中國,或許應當更加重視程序正義的構建。比如有限地肯定“沉默權”。源自于古羅馬法中“罪案有疑,利歸被告”的思想以及“對任何人都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理念的沉默權,被廣泛地認為是嫌疑人用以自衛的、最重要的一項刑事司法權利。美國1966年通過判例確定的“米蘭達規則”,將“審判沉默權”擴展到“審訊沉默權”。而在當前中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執法、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對嫌疑人口供還具有一定的依賴性。“沉默權”制度的確立將會有利于這個問題的解決。[3]此外,為避免更多的司法失當,正當程序將會為刑事司法活動設置許多程序關卡,這就需要舍棄司法活動最大效率的追求。
(三)手段的節制性是關鍵
權利的救濟和權力的制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需要執法手段的節制性來支持。手段的節制性是對執法行為內在必要性的要求。由此,刑事司法的制度設計既要關注有效地打擊違法犯罪,也要充分關注嫌疑人的權利保障。從力量的對比來看,尤其需要重點防范處于強勢地位的,諸如警權之類的公權力的濫用。有必要設定與一般違法、輕微犯罪、暴力犯罪相適應的治理結構。在什么情況下可以使用警械,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盤問,盤問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情況下必須窮盡一切可能迫使公權力的行使者必須選擇給相關當事人造成最小損害的手段。
在雷洋事件發生十幾天之后的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再次堅定一個信念,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執法活動、每一起案件辦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4]接警、盤問、傳喚、立案、強制措施、調查取證,等等,每一個環節的權力運行都應確保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事實上,公眾之所以如此關注“雷洋事件”,是源自心底對警察濫用警權的深層恐懼。只有清晰地設定警察執法的邊界,建立起外部對警察權的有效制約機制,才可能避免出現刑訊逼供、濫用警權等違法行為。
(四)普遍的服從性是根本
“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199所以,除了有良法作為前提之外,還必須有普遍的服從,全民守法才是法治的關鍵。雷洋事件一方面提醒我們要防范公權力的濫用,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必須樹立一種與法治相適應的社會思維模式。無論是執法、維權,還是輿論監督的質疑,都應當依法行使。比如備受爭議的公眾輿論,有人把它視為司法獨立的攔路虎,也有人把它視為促進司法公正的利器。在筆者看來,滔滔輿情,不僅關乎公平正義,也反映公道人心。輿論不能忽視,獨立公正的審判同樣為法治中國所需要。兼顧二者的方法就是, 法律的歸法律,
輿論的歸輿論。 裁判不是輿論的長項和專業,輿論就不應當事先就個案做法律上的裁判和預測,更不能以道德的名義進行主觀裁判,以此才不會干擾司法的獨立審判。輿論的長處是找尋真相,所以,輿論要做的就是在實事求是這個基本原則的指導下,以追問事實真相為己任,幫助公眾追問事實、提出合理質疑。具體到官方回應輿論的問題,筆者認為,要重塑公信力,公權力有必要堅守三個要點:第一時間、誠懇主動、合法有效。第一時間就是要快,絕不能拖延,一拖延就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誠懇主動是態度,絕不能撒謊掩飾。合法有效是內容要求,必須有效回應,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違背法律、倫理,否則將會是眾矢之的。
無論如何,雷洋事件只是一個個案,不能就此否定一個群體,更不能就此懷疑中國的法治建設。我們之所以分析它,只是希望更加有力地推動我們的法治建設進程,不斷增強中國的法治自信。
[1] 文峰.關注“雷洋事件”,愿真相來快一點[N].長沙晚報,2016-05-11(A02).
[2]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3] 何家弘.沉默權制度及刑事司法的價值取向[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0(4):32-45.
[4] 姜赟.法治,須從程序通往正義[N].人民日報,2016-06-02(005).
責任編輯:仲耀黎
2016-09-26
張璇孟 (1974—),女,江西九江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法社會學。
DF84;DF793
A
1671-8275(2016)06-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