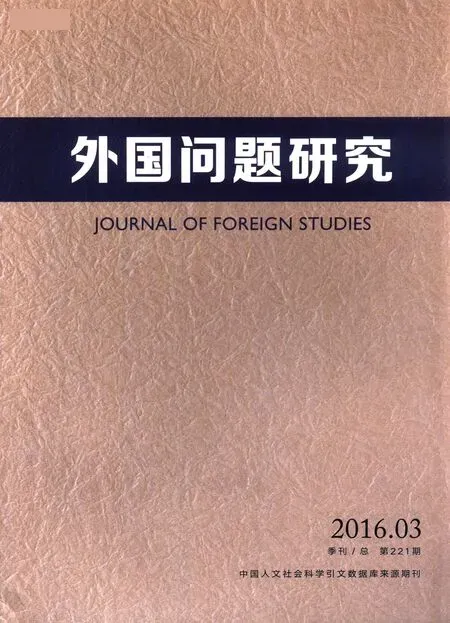中東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
——相關概念的認知與歷史經驗的審視
哈 全 安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
中東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
——相關概念的認知與歷史經驗的審視
哈 全 安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伊斯蘭世界的歷史傳統在于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的錯綜交織,中東現代化進程在政治層面的運動軌跡普遍表現為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長。中東諸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化改革通常與自上而下之威權政治的強化呈同步趨勢,所謂“發展的獨裁模式”和威權政治的膨脹導致民眾參與和民主政治的缺失,致使世俗國家與宗教社會形成明顯的悖論傾向。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的消長,具有宗教社會對抗世俗國家的濃厚色彩,其特定內涵在于政治發展進程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劇烈轉換,所謂“伊斯蘭是出路”則是現代伊斯蘭主義代表民眾意志和動員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標志。
中東;現代化;民主化;世俗化;現代伊斯蘭主義
一、中東現代化
所謂現代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民主化和世俗化,涉及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在內諸多學科的研究領域。由于不同學科視角各異,關于現代化以及民主化和世俗化之內涵的界定千差萬別,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政治學家通常關注國家層面的歷史運動,強調現代化的實質在于理性化、世俗化和民主化成為國家權威的合法性來源,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普遍的政治認同感和國家權力的整合是現代化的歷史基礎,國家功能的集權化、官僚機構的效率化、公職人員的文官化、大眾參與化和公民影響力則是現代化的標志性符號。經濟學家則著眼于技術的變革、生產的進步和經濟的增長,注重物質財富之增長、分配和消費的量化分析,強調現代化的基本脈絡在于產業結構的轉化即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以及第三產業的長足發展,將工業革命的肇始視作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起點,而將現代化的歷史變革視作工業化的最終結果。社會學家所關注的是社會的變遷,認為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在于社會結構的分化和整合、社會組織的開放化、社會成員的非等級化、社會職業的流動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和生活福利化,甚至將社會行為動機和社會觀念取向直至人格特質和國民心理素質的轉化視作現代化進程的標志性元素,所以馬克斯·韋伯將現代化定義為理性化的過程。
相比于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歷史學的特點在于側重長時段的動態考察,關注個案的實證分析,強調從具體到抽象和從個別到一般的思維邏輯,進而從貌似雜亂無序的歷史現象中探討人類社會演進的客觀規律。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現代化、民主化和世俗化皆為具有豐富內涵的歷史現象,亦是歷史長河劇烈運動的必然產物。
如若從宏觀角度審視,所謂的世界歷史,無疑是人類社會不斷走向解放的漫長過程。人類社會在走向解放的漫長過程中先后經歷兩次深刻的轉變。人類社會的第一次解放,發生于自野蠻向文明過渡的歷史階段,其核心內容在于原本僅僅從屬于氏族部落和作為“整體的肢體”的個人逐漸擺脫血緣群體的束縛,成為獨立存在的社會成員,是為文明化。人類社會的第二次解放,發生于自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歷史階段,其核心內容在于獨立存在的社會成員逐漸擺脫依附狀態而走向自由的時代,是為現代化。*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
所謂的現代化,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可謂世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現代化并非人類社會之無序的演變抑或漸進的發展過程,而是具有特定的歷史內涵,表現為革命性、內在同質性、不可逆轉性和全球普遍性的明顯特征。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包含相互關聯之諸多因素的矛盾運動,其實質在于新舊社會形態的更替即現代文明否定傳統文明的深刻變革。個體生產、自然經濟、鄉村農業的統治地位、社會生活的封閉狀態、廣泛的超經濟強制、普遍的依附傾向和思想的束縛無疑是傳統文明的基本要素,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主要表現為從個體生產向社會化生產的轉變、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從農本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從封閉向開放的轉變、從奴役向自由的轉變、從專制向民主的轉變。生產的社會化、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人身的自由化、社會秩序的法治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意識形態的個性化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構成了現代化的普遍趨勢和基本方向。生產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增長,則是現代化進程的深層物質基礎。*哈全安:《中東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頁。
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緣起于西方的沖擊。自16世紀開始,傳統的農本社會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漸衰落。伴隨著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重商主義的實踐和工業革命的完成,西方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實力劇增。相比之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歷史進程處于停滯的狀態,農本社會長期延續。西方的崛起和中東歷史的相對停滯狀態,導致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力量對比的失衡。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崛起,無疑標志著現代文明的誕生。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停滯狀態,其特定內涵在于傳統秩序的根深蒂固。不同文明之間的巨大落差導致西方沖擊的歷史浪潮,現代化進程隨之自西方基督教世界向中東伊斯蘭世界逐漸延伸。進入19世紀,西方列強的戰爭威脅促使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埃及的帕夏和伊朗的國王致力于自上而下的新政舉措,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由此拉開歷史的序幕,傳統社會的冰山開始出現溶化的跡象。*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4頁。
西方諸國自15、16世紀之交開始的新航路開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其后爆發的一系列政治革命,可謂現代化進程早期階段的歷史坐標。工業革命并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起點,卻是西方現代化進程早期階段諸多層面劇烈變革特別是自然經濟解體和市場化程度提高的邏輯結果,堪稱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里程碑,標志著現代化進程步入新的階段。另一方面,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終極目標無疑具有同一性,然而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卻不盡相同,可謂殊途同歸。歷史的發展表現為否定與繼承的雙重過程,傳統文明的特定背景賦予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特定的歷史印記。現代化并非等同于所謂的西化、歐洲化和美國化,亦非東方后發現代化國家復制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即便在西方世界和發達國家,其現代化模式亦千差萬別,形態各異。中東地區的現代化作為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定內涵在于封建主義的衰落、傳統秩序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傳統的封建主義與新興的資本主義兩者之間的矛盾運動貫穿中東現代化的進程。伊斯蘭傳統文明與中東現代化進程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和歷史聯系。西方的沖擊固然構成深刻影響中東地區現代化進程的外部因素,而伊斯蘭傳統文明的特定歷史背景從根本上決定著中東現代化進程之區別與其他諸多地區現代化進程的特殊道路。*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
二、中東民主化
人類社會在經歷從文明化到現代化之歷史轉折的同時,亦在政治層面經歷從去民主化到回歸民主的劇烈運動。作為現代化在政治層面的歷史坐標,民主化具有特定的政治屬性,包含特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民主化的實質在于政治權力的歸屬,而民主化的歷史進程表現為政治權力從世襲性向公共化的轉換、從壟斷性向開放化的轉換和從封閉性向程序化的轉換。民主化意味著政治權力的重新組合和政治領域的深刻變革,具有明確的歷史方向性。實現民眾主權的政治原則、公共權力的制衡和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抑或所謂的民眾政治化,無疑是民主化的核心內涵。公共權力之合法性來源的轉換,則是民主化的首要標志。常態化的選舉政治提供了民主政治框架下公共權力的合法性來源,而多元化的政黨政治則是民主政治的必要載體和運作媒介。
所謂自由化與民主化無疑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系,卻未必處于同步的狀態。自由化通常表現為自上而下的過程,抑或源于統治者的恩賜,而民主化往往表現為自下而上的過程,需要民眾的艱苦抗爭。自由化的內涵在于官方給予民眾以相對寬松的私人空間,而民主化的內涵在于民眾政治參與的擴大。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官方主導的政治改革大體上局限于自由化的范疇,而民主化的進程明顯滯后于自由化的進程;統治者通常致力于以自由化改革作為民主化運動的替代,而官方操縱和控制的自由化改革,其主要目的在于緩解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有學者認為,民主政治可以區分為原生型和移植型,北美西歐可謂原生型民主政治,而其他地區則為移植型民主政治,“在這些國家,本土社會和傳統中原本不存在民主的因素”,這樣的看法顯然缺乏歷史常識。縱觀世界歷史,所謂民主并非現代社會的特有現象,非民主的專制統治亦非前現代化時代的唯一政治形態。漫長的原始社會曾經盛行民主制,而在文明社會的早期階段,原始民主制的傳統對于國家形態和政治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與民主密切相關的共和制政體,不僅存在于地中海世界的雅典和羅馬,而且遍及古代東方世界初入文明的諸多國家。在伊斯蘭主義者極度推崇的早期伊斯蘭時代,麥地那國家作為伊斯蘭國家的原生形態,即為具有濃厚民主色彩的共和政體。國家的形成無疑是人類社會步入文明的標志,而國家政體從民主向專制的過渡和從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轉變,抑或所謂的去民主化進程,則是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
所謂的民主并非超越時代的抽象政治原則,其與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社會環境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不同時代的民主具有不同的歷史內涵和政治特質,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則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民主化發端于北美和西歐,繼而在全球范圍內蔓延,已然成為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普世性而不可抗拒的歷史發展方向。然而,民主化并非美國化抑或西方化的邏輯結果,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和現代化的必要元素,植根于經濟社會領域深刻變革的土壤之中,以新舊經濟結構的興衰和新舊社會秩序的更替為前提條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歷史環境決定了不同國家之民主化的特定道路,民主國家的政治形態亦各具特色而表現為明顯的多樣性。所謂的西方民主,即便在西方世界各國,其外在形式亦不雷同。至于西方世界之外的諸多國家,民主形態亦千差萬別。
自由與民主可謂現代政治文明的兩大主題,主權在民與憲法至上構成現代國家的政治基礎。現代國家之區別于傳統國家的本質要素,在于成熟的自由民主。民眾廣泛政治參與的基礎上國家意志與民眾意志的吻合,可謂現代國家的核心標志。有學者從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歷史經驗出發,強調現代化進程在政治層面的歷史坐標是國家權威的強化以及效忠國家的政治認同,而前工業化時代抑或所謂原工業化時代統一民族國家的建構則是現代化進程的起點。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縱觀世界歷史,傳統社會不乏強有力的國家權威,亦不乏效忠國家的政治認同。具有悠久歷史的古代中國堪稱傳統文明的典范,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發達的文官體制、世俗的政治理念、忠君愛國的政治認同可謂一應俱全,卻無諸如人權、自由和民主的現代政治元素,唯見至高無上的皇權、亦主亦奴的官紳和任人宰割的民眾充斥于文獻典籍的記載。歷史經驗充分表明,傳統社會之農本經濟與國家權威的強化以及效忠國家的政治認同并非截然對立,現代社會之經濟市場化進程與國家權威的強化以及效忠國家的政治認同亦未必表現為必然的邏輯聯系。
傳統社會政治模式的特有現象在于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之間的深刻對立,表現為依附與強制的明顯傾向,而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之間的尖銳對立通常表現為民眾與國家之間的暴力沖突。農民戰爭貫穿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進程,規模之大堪稱舉世無雙;此起彼伏的農民戰爭固然與其貧困的生活境況不無聯系,更是中國傳統社會之專制主義極度膨脹的特定政治環境下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尖銳對立的邏輯結果。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傳統政治制度,建立在傳統經濟秩序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之上,其突出特征在于君主的至高無上和臣民的絕對順從,國家意志與民眾意志之間亦表現為明顯的對立狀態。相比之下,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的趨于吻合無疑是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構成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趨于吻合的歷史基礎。*哈全安:《中東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第18頁。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作為人類社會走向解放的標志性環節,根源于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農業的統治地位和自然經濟的廣泛存在,構成傳統政治模式賴以存在的客觀物質環境。工業化的發展、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交換關系的擴大,排斥著依附與強制的傳統傾向,進而導致傳統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現代政治模式的逐漸成熟。*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民眾政治參與的程度,決定著相應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政策,進而體現民眾作為社會主體之解放的程度。民主化進程的實質,在于民眾通過廣泛政治參與而獲得政治層面上的解放。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的日臻完善,構成聯結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趨于吻合的橋梁和紐帶。
政治的穩定通常表現為兩種基本的歷史模式,一種是通過排斥民眾參與和強化獨裁專制而實現的傳統政治穩定,另一種是通過否定獨裁專制和擴大民眾參與而實現的現代政治穩定。*哈全安:《中東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第19頁。現代化進程中的民主化實踐通常與政治的非穩定性處于共生狀態,正如亨廷頓所言:政治穩定是政治發展的指標,現代性意味著穩定而現代化意味著動蕩。現代化進程在政治層面的歷史運動,表現為傳統政治穩定的衰落和現代政治穩定的逐漸確立,劇烈的政治動蕩則是聯結傳統政治穩定與現代政治穩定的中間環節。威權時代之政治氛圍的平靜和穩定無疑是政治風暴的前奏,變動的經濟社會秩序與明顯滯后的政治制度之間的深刻矛盾則是政治風暴的源頭所在。脆弱的政治基礎和內在的悖論傾向,是威權政治之區別于傳統君主政治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明顯特征。獨裁的鐵幕只能掩蓋和壓制社會矛盾和政治對抗,卻不能消除社會矛盾和政治對抗的根源。在獨裁的鐵幕掩蓋下,社會矛盾和政治對抗不斷加劇。民眾力量的增強導致民眾的政治崛起,民眾的政治崛起挑戰著威權政治的統治模式,進而形成民主與專制激烈抗爭的動蕩局面。*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938—939頁。
有學者認為,民主與暴力革命之間并無必然聯系,在暴力革命中產生的民主往往難以長久延續,此話在理論上似乎不妥,亦與歷史事實不盡相符。統治模式決定反抗模式,特定的政治環境塑造著相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縱觀世界歷史,民主化的政治實踐無疑是極其艱難和充斥著暴力的漫長歷史過程。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毀獨裁專制,進而推動政體轉換并為民主化進程開辟道路,在諸多國家的政治發展中并非鮮見。
民主化進程與公民社會的成長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成熟的公民社會可謂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所謂公民是相對于傳統文明時代的臣民而言的法律概念,其核心內涵在于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哈全安、張楚楚:《從選舉政治到廣場政治:埃及穆拉克時代的民眾政治參與》,《西亞非洲》 2013年第3期。所謂的公民社會,緣起于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秩序的變動和新舊社會勢力的消長。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秩序的變革和新階層的興起,提供了公民社會成長的客觀環境。公民社會的成長既是經濟市場化和私營經濟活躍的歷史產物,亦與自下而上的民眾政治參與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與民主化進程表現為同步的趨勢。公民權的完善是公民社會走向成熟的法律基礎,而公民社會的本質特征在于公共空間的公眾參與和公眾分享,其核心功能在于制約國家權力,溝通民眾意志與官方意志,具有民間性、自主性、多元性、開放性和公眾參與性之諸多要素的非政府組織則是公民社會的載體形式。另一方面,中東伊斯蘭世界之公民社會的內涵,不應簡單套用西方概念。在西方世界,現代化與世俗化表現為同步的過程,世俗性構成公民社會的鮮明特征。相比之下,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公民社會的成長往往表現為程度不同的宗教色彩,現代伊斯蘭主義的實踐與公民社會的成長兩者之間并不存在根本的對立,反之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公民之權利與義務的失衡是世俗威權政治的突出特征,公民社會的缺失則是制約中東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現代伊斯蘭主義與世俗自由主義貌似水火不容,皆致力于挑戰世俗威權國家的獨裁統治,具有異曲同工之處,構成推動公民社會成長歷程的兩大意識形態。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尖銳矛盾,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深刻對立,特別是挑戰世俗威權國家和推動民主化進程的共同政治目標,提供了現代伊斯蘭主義與世俗自由主義求同存異進而建立廣泛聯盟的歷史基礎。*哈全安:《世紀之交埃及伊斯蘭主義的新動向》,《世界宗教研究》 2013年第6期。公民社會的成長提供了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重要條件,現代伊斯蘭主義與世俗自由主義之政治立場的趨同可謂中東政治發展和民主化進程的歷史方向。
三、中東世俗化
世俗化一詞源于歐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領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領域的非宗教化,強調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原則。多數學者通常將目光聚焦于歐洲基督教世界中世紀的歷史環境和近代早期之社會轉型的歷史實踐,依據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歷史經驗,援引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現代化模式,將教俗二元體系視作傳統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將宗教領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領域的非宗教化即教俗分離視作現代政治的特有形態,強調現代化與世俗化兩者之間具有普世的同步性和必然性,具有西方中心論的明顯色彩和歷史痕跡,結論尚顯武斷。
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會現象,而是與相應的歷史環境密切相關。教俗關系的核心內容是權力的角逐,而教俗雙方的力量對比決定著教俗關系變化的走向和權力角逐的結局。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世界,教會與國家長期并立,宗教生活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處于二元狀態,羅馬教廷和天主教會可謂最具影響的政治勢力和傳統秩序的集中體現。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旨在否定教會權威和擺脫教廷控制的宗教改革構成歐洲基督教世界現代化進程早期階段的重要內容,而世俗化進程集中體現世俗與宗教之間的權力爭奪,包含爭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權國家進而實現民眾解放的明顯政治傾向,與歐洲基督教世界現代化的政治發展進程呈同步的趨勢。
然而,所謂的世俗化并非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現象。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長期伴隨著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改革,緣起于西方宗教沖擊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西化色彩,其主要舉措包括引進西方的世俗法律、興辦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關閉宗教法庭、取締宗教學校、剝奪宗教地產、削弱宗教組織的自主地位和克服宗教勢力的離心傾向。與歐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進程相比,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并非嚴格遵循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原則,而是強調國家和政府對于教界的絕對控制,表現為宗教機構的官僚化和宗教意識形態的官方化。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往往與威權政治的膨脹趨于同步,包含公共權力模式之重新建構的政治傾向,系官方強化控制民眾社會進而完善威權政治的必要舉措,其實質在于威權政治自世俗領域向宗教領域的延伸,而與民主化的政治進程背道而馳。官僚化的教界和宗教機構處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并未脫離政治領域、喪失政治功能,而是成為威權政治的御用工具。*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949頁。國家意志與民眾意志的差異,往往表現為官方宗教學說與民眾宗教思想的對立和沖突。官方化的宗教學說極力維護現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無異于麻痹民眾的精神鴉片。
綜觀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世俗政治并非現代社會的特有現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歷史階段,自古有之。另一方面,宗教與政治的結合抑或所謂的神權政治并非傳統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歷史模式,而宗教與政治的分離亦非從傳統政治模式向現代政治模式轉變的必要條件和必然過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在政治層面的核心內容無疑是民主化的歷史運動,其實質在于實現主權在民的政治原則和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民主化的政治進程取決于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刻變革,而不是取決于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950頁。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無疑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卻非存在根本的對立。傳統世俗政治與傳統宗教政治長期處于共生狀態,兩者無疑具有異曲同工之處,皆強調依附和順從的傳統政治原則。相比之下,現代世俗政治與現代宗教政治皆屬現代文明的范疇,倡導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理念,與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具有同步性和內在邏輯性。至于所謂的世俗化,并非政治現代化的必要組成部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華夏世界素有世俗政治的歷史傳統,世俗君主凌駕于社會之上,世俗皇權極度膨脹,宗教政治微乎其微,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變革局限于世俗的領域,表現為不同世俗勢力之間的激烈抗爭,而所謂的世俗化進程則無從談起。強調現代化進程與世俗化進程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系,將世俗化視作現代化的歷史坐標,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現代化的發展水平,進而將宗教政治挑戰世俗政治視作現代化進程的負面因素甚至是現代化進程的逆流,實在令人費解。
四、自上而下的世俗威權政治與“發展的獨裁模式”
根據伊斯蘭教的傳統理論,溫麥是伊斯蘭國家的原型和經典形態,是凝聚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形式,伊斯蘭教構成維系溫麥的信仰基礎。在傳統的穆斯林看來,世俗的民族主義是西方的舶來品,是分裂溫麥和離間穆斯林的異教意識形態,而沙里亞即伊斯蘭教法則是規范穆斯林行為的唯一法律準則,因此純粹的世俗思想和異教的法律均不可接受。換言之,在傳統的伊斯蘭世界,超越宗教界限的世俗民族主義與溫麥的原則大相徑庭,并無存在的空間。
中東伊斯蘭世界之世俗化改革的肇始與現代化進程的啟動大體上呈同步的趨勢。自19世紀開始,伊斯蘭世界逐漸步入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歷史階段,溫麥作為教俗合一的國家形態不復存在,地域性的世俗民族國家初露端倪,世俗化風行一時。*哈全安:《伊斯蘭世界的宗教與國家》,《史學理論研究》 2006年第1期。然而,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改革與政治民主化進程并未表現為同步的趨向,卻與威權政治的強化具有內在的邏輯性,表現出明顯的歷史同步性。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根源于威權化的政治模式,服務于威權化的政治需要,而世俗化的邏輯結果則是威權政治的強化。在君主制的政治框架下,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君主、伊朗愷加王朝和巴列維王朝的國王,皆曾致力于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排斥傳統宗教勢力的政治影響,強調世俗的順從原則,旨在強化君主集權的國家體制,世俗政治、君主政治和威權政治表現為三位一體的歷史模式。在共和制的政治框架下,在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和納賽爾時代的埃及,世俗化與威權化處于共生的狀態,世俗威權政治達到巔峰,傳統宗教勢力在政治舞臺銷聲匿跡。
中東現代化進程的啟動緣起于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之間的巨大歷史落差和西方的沖擊浪潮,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擴張和由此形成的尖銳民族矛盾導致中東現代化進程早期階段之民族主義的高漲。特定的歷史環境塑造了諸多世俗威權國家之濃厚的民族主義傾向,所謂的世俗化改革包含著民族主義的歷史內核,而爭取民族解放和主權獨立成為中東現代化進程早期階段在政治層面的突出現象。中東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政治思潮,從奧斯曼主義到巴列維主義,從凱末爾主義到納賽爾主義,無不具有民族主義的濃厚色彩。擺脫從屬于西方的政治地位和依附于西方的經濟地位,是中東伊斯蘭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客觀需要。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至高無上,堪稱諸多世俗威權國家遵循的首要準則。民族主義的廣泛勝利,提供了真正實現經濟進步和財富增長進而使民眾獲得權利、自由和尊嚴的前提條件,*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斯。標志著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步入嶄新的發展階段。
所謂世俗政治,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內涵。*哈全安:《伊朗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史學理論研究》 2008年第3期。在現代化的歷史背景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威權國家既不同于傳統專制國家亦區別于現代民主國家,兼有現代與傳統的雙重屬性和悖論傾向。一方面,世俗威權國家作為所謂“發展的獨裁模式”,致力于推動經濟社會領域之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革,無疑成為中東現代化進程的始作俑者和重要實踐者;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長足進步以及鄉村社會的劇烈變革,標志著世俗威權國家在中東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歷史地位。另一方面,世俗威權國家盡管標榜西化道路,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現代化模式作為典范,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全盤西化,而是在政治改革領域止步不前,抵制西方崇尚的現代民主之政治理念,奉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則,極力強化獨裁專制,壟斷公共權力,排斥民眾的政治參與,阻礙民主化進程。從西方引進的憲政徒有虛名,憲法如若一紙空文,憲法規定的政治制度與現實的政治生活大相徑庭,議會形同虛設,君主和總統凌駕于憲法和議會之上,憲法之關于主權在民、自由平等和保障公民權利的相關條款只是欺騙民眾的美麗謊言,形同虛設的議會和政府操縱的選舉則是獨裁專制的點綴和遮羞布,民眾長期徘徊于政治舞臺的邊緣地帶,政治發展方向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民主化進程背道而馳,政治秩序長期滯后于經濟社會領域的劇烈變革,直至深陷矛盾危機之中而無法自拔。經濟社會的變革與民眾政治參與的排斥,以及財富的增長與貧富分化的加劇,構成世俗威權國家之現代化進程的普遍現象。以犧牲政治層面的自由和民主作為代價推動新舊經濟社會秩序的更替,則是所謂“發展的獨裁模式”之實質所在。*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938頁。
五、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理念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階級社會的諸多宗教作為階級對抗的產物和體現,具有雙重的社會功能。一方面,階級社會的宗教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秩序和壓迫民眾的精神枷鎖,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頁。另一方面,在階級社會,“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宗教為民眾反抗現實的苦難提供神圣的外衣,進而構成社會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過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體現和發揚,在歷史長河中亦非鮮見。*哈全安:《正統信仰與異端神學》,《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通常認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現象,基督教通過宗教改革而由傳統的意識形態轉變為適應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至于伊斯蘭教則未曾經歷過宗教改革,系傳統范疇的保守意識形態,是制約伊斯蘭世界社會進步的負面因素,所謂“宗教對抗國家”則是伊斯蘭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難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眾所周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的變化必然導致社會意識的相應變化。*哈全安:《伊斯蘭世界的宗教與國家》,《史學理論研究》 2006年第1期。諸多宗教盡管根源于特定的社會現實,卻非處于靜止的狀態,而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經歷著滄海桑田的變化,尤其是在不同的時代經歷著性質各異的思想變革過程。*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基督教誕生于古代地中海世界,早期基督教包含下層民眾反抗羅馬帝國統治的政治傾向,在中世紀的歐洲成為長期構成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理論基礎,15世紀以后逐漸演變為適應現代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伊斯蘭教,根源于公元7世紀初阿拉伯半島從野蠻向文明過渡的特定歷史環境,無疑是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改造阿拉伯社會的重要理論武器。在中世紀的漫長歷史時期,伊斯蘭教作為官方的學說趨于保守和僵化,逐漸演變為具有濃厚傳統色彩和捍衛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論。然而,伊斯蘭教并非孤立存在和靜止不變的意識形態。現代化進程中客觀物質環境的劇烈變化,不可避免地導致伊斯蘭教作為意識形態的相應變化。隨著新舊經濟秩序的更替和新舊社會勢力的此消彼長,伊斯蘭教經歷了深刻的裂變過程,進而形成新舊宗教理念的明顯對立。*哈全安:《中東國家現代化歷程》,第458—459頁。自19世紀以來,伊斯蘭世界之宗教理念的變革,從文化層面延伸到政治層面,從精英層面延伸到大眾層面,其歷史路徑與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相比可謂異曲同工。
伊斯蘭教的傳統宗教理念與傳統社會長期處于共生的狀態,包含傳統社會的固有屬性,恪守傳統的意識形態,極力維護傳統秩序的合法地位,是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的輿論工具,而傳統宗教學者既是傳統社會秩序的歷史參與者,亦是傳統社會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衛者。相比之下,現代伊斯蘭主義強調《古蘭經》和“圣訓”的基本信仰原則以及早期伊斯蘭教的歷史實踐,崇尚穆罕默德和麥地那哈里發國家之共和政體的社會秩序,具有倡導自由民主和民眾參與的特定政治內涵。*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另一方面,復古與變革貌似截然對立,實則不然。伊斯蘭教素有假借復古之名而行變革之實的歷史傳統。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加傳布啟示的初期,似乎無意創立全新的宗教,而僅僅是恢復易卜拉欣時代的信仰,呼喚世人追尋遠古的前輩所崇奉的真理。“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種表面上的反動,是一種虛假的復古和返樸”。*哈全安:《麥加貿易與伊斯蘭教的興起》,《史學集刊》 1994年第1期。現代伊斯蘭主義不同于伊斯蘭教的傳統宗教理念,具有宗教政治化的濃厚色彩,強調真正的伊斯蘭教并非遠離政治的個人信仰和僵化的神學理論,而是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民眾利益的體現,其核心內容在于借助回歸早期伊斯蘭教傳統的宗教形式而倡導平等和民主的現代政治原則。現代伊斯蘭主義貌似復古,實為強調擴大民眾政治參與,表現為挑戰世俗威權政治的明顯傾向,其思想內涵已與伊斯蘭教的傳統宗教理念相去甚遠,無疑屬于現代政治理念的范疇,頗具革命的傾向,可謂“被壓迫生靈的嘆息”和被剝奪權利之下層民眾的政治宣言,蘊含著動員民眾政治的巨大潛力。現代伊斯蘭主義的興起,根源于伊斯蘭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的裂變和諸多因素的矛盾運動,集中體現世俗威權政治的條件下民主與專制的激烈抗爭,標志著嶄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初露端倪。*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951頁。
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理念,兼有民眾性和民主性的雙重屬性,其思想內涵與西方現代之世俗民主政治理念貌似水火不容,實則并無根本的對立,皆以擴大民眾參與和實現自由民主作為思想宗旨,可謂殊途同歸。所謂宗教與世俗的對抗,在中東諸國并非“現代化的難題”,亦非體現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沖突,而是包含民主政治與威權政治激烈抗爭的明顯傾向。*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將現代伊斯蘭主義的興起視作傳統的回歸抑或現代化進程的逆向運動即所謂“反現代化基調的和傳統主義的意識形態”,顯然存在商榷的余地。
六、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實踐與自下而上的民眾政治參與
伊斯蘭教屬于信仰的范疇,而伊斯蘭主義則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傾向,兩者概念不可混淆,內涵亦不盡相同。另一方面,伊斯蘭教與伊斯蘭主義具有密切的內在關聯性,伊斯蘭教信仰和伊斯蘭價值觀在中東伊斯蘭世界具有根深蒂固的歷史傳統,進而提供了現代伊斯蘭主義之政治實踐的深層社會基礎。威權政治的膨脹和民主政治的缺失,導致世俗國家與宗教社會形成明顯的悖論傾向,官方意志與民眾意志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而所謂“伊斯蘭是出路”成為現代伊斯蘭主義代表民眾意志和動員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標志。
相比于自上而下的世俗威權政治,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實踐表現為自下而上的歷史運動。世俗領域和國家體制的非民主性,催生了宗教領域和社會層面的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世俗與宗教的沖突,折射出世俗威權國家與宗教色彩的民眾社會之間的深刻矛盾。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的角逐,根源于現代化進程中新舊勢力的消長和諸多因素的矛盾運動。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的消長,具有宗教社會對抗世俗國家的濃厚色彩,其特定內涵在于政治發展進程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劇烈轉換,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由于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的差異,中東諸國的民主化進程表現為明顯的非同步性。民主化的原因在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內源性矛盾,民主化的動力在于民眾政治的崛起,而民主化的進程取決于民眾社會與威權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土耳其自1950年起通過議會選舉的形式實現不同政黨之間的權力更替,率先完成政治領域的歷史性轉變,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于民眾的選擇成為此后政治生活的基本準則。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標志著以君主制為核心的傳統政治制度壽終正寢,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和普選制的常態化實踐奠定了民眾廣泛參與的政治框架。埃及自薩達特當政期間開始一黨制向多黨制的轉變,長期壟斷國家權力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作為唯一合法的政黨不復存在,多黨制政治進程的啟動導致民眾政治參與的相應擴大。
政治環境、政治理念與政治實踐三者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特定的政治環境,塑造著相應的政治理念,進而決定著相應的政治實踐。*哈全安:《世紀之交埃及伊斯蘭主義的新動向》,《世界宗教研究》 2013年第6期。縱觀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諸多國家,由于國情不同,政治環境各異,政治實踐通常表現為政治革命、議會選舉、街頭示威和極端暴力的不同外在形式,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實踐亦然。高壓的政治環境導致激烈和激進的政治反抗,寬松的政治環境則是政治實踐趨于溫和的沃土。
在巴列維國王統治下的伊朗,世俗威權政治極度膨脹,官方長期操縱議會選舉,排斥世俗政黨的政治參與,禁止民眾的自由結社,世俗反對派政治勢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立足之處,宗教幾乎是民眾反抗的僅存空間,宗教的狂熱則是民眾發泄不滿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哈全安:《伊斯蘭世界的宗教與國家》,《史學理論研究》 2006年第1期。巴列維王朝之自上而下的高壓政策,導致伊朗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激進政治傾向。阿里·沙里亞蒂和霍梅尼闡述的現代伊斯蘭主義宗教政治思想,可謂巴列維當政期間的伊朗之世俗威權政治和高壓政策的邏輯結果,直至演變為政治革命的意識形態。伊斯蘭革命的勝利和所謂的“頭巾取代王冠”,埋葬了伊朗君主獨裁的傳統政治制度,進而為伊朗民主政治的發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952頁。伊斯蘭共和國憲法具有宗教與世俗的雙重屬性,強調法基赫至上的政治原則。盡管如此,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后30年間,選舉政治日漸活躍,常態化的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成為實現民眾政治參與的基本渠道,國家意志與民眾意志趨于吻合。
埃及的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主要表現為穆斯林兄弟會的宗教政治實踐。穆斯林兄弟會的社會基礎是徘徊于政治舞臺邊緣地帶的下層民眾,支持者遍及城市和鄉村。*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賽義德·庫特布崇尚政治暴力,強調“戰斗的伊斯蘭”作為穆斯林兄弟會的意識形態,其頗具激進色彩和極端傾向的現代伊斯蘭主義理論,可謂納賽爾當政期間世俗威權政治極度膨脹的產物。后納賽爾時代,政治環境逐漸寬松,世俗威權政治出現衰落的征兆。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政治,被西方學者稱作“自由化的威權體制”,區別于納賽爾時代的“絕對威權體制”,即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賜予民眾以有限的自由和公民權,賜予反對派以有限的政治空間。官方主導的自由化政治改革進程,提供了穆斯林兄弟會通過合法方式擴大政治影響的重要條件。穆斯林兄弟會作為埃及政壇最重要的政治反對派,致力于推動體制內的政治改革進程,尋求現存秩序框架內的政治參與,力爭取得作為政黨的合法地位,致力于在憲政框架下推動政治改革進程和多黨制基礎上的議會選舉,試圖在議會選舉的框架下尋求新的政治空間和實現政治參與,直至逐漸淡化伊斯蘭主義的宗教色彩,試圖彌合反對派陣營的教俗分歧,進而擴大與世俗反對派的政治合作,政治立場趨于溫和。*哈全安:《世紀之交埃及伊斯蘭主義的新動向》,《世界宗教研究》 2013年第6期。與此同時,長期致力于政治暴力的伊斯蘭主義極端派別在世紀之交亦出現溫和化和去暴力化的明顯趨勢。2011年春,街頭政治自首都開羅蔓延至埃及各地,挑戰官方主導的所謂“無參與的政黨政治”和“無民主的選舉政治”,缺乏民主的選舉演變為拋棄選舉的民主。從官方操縱的選舉政治演變為自下而上的街頭政治成為導致埃及政治深刻變革的歷史路徑,而穆斯林兄弟會作為埃及現代伊斯蘭主義的主流派別無疑是“倒穆運動”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哈全安、張楚楚:《從選舉政治到廣場政治:埃及穆巴拉克時代民眾政治參與》,《西亞非洲》 2013年第3期。
土耳其共和國前期的世俗化改革緣起于凱末爾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表現為自上而下的過程,包含世俗國家與宗教社會的悖論傾向,世俗化進程與政治民主化進程并未表現為同步的趨向。自由在傳統社會原本是相對于奴役狀態的法律概念,在現代社會成為與公民權密切相關的政治概念。民主化無疑是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宗教權利構成人權的要素之一,宗教自由則是公民自由的組成部分。隨著民眾的政治崛起和政治參與程度的提高,民眾對于宗教自由的訴求上升到政治層面。自80年代開始,自下而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土耳其趨于高漲,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影響不斷擴大。*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952頁。然而,土耳其自二戰結束后長期實行多黨制的政治體制,政治環境相對寬松,宗教政治與世俗政治的權力角逐在土耳其并未表現為尖銳的對抗和激烈的沖突,尤其是沒有形成否定現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蘭政體的激進政治綱領。*哈全安:《伊斯蘭教傳統文明的基本特征與中東現代進程的歷史軌跡》,《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第1期。政黨政治的活躍、議會政治的完善和選舉政治的成熟,決定了土耳其現代伊斯蘭主義之政治實踐的溫和色彩。包括民族秩序黨、救國黨、繁榮黨、賢德黨和正義與發展黨在內的諸多宗教政黨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活動,以及宗教政黨與世俗政黨的廣泛合作,構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顯特征。現代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的消長和并存,以及世俗政黨與現代伊斯蘭主義政黨之間的權力角逐,體現了戰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與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歷史走向。在民主化的歷史背景和多黨制議會選舉的政治框架下,現代伊斯蘭主義政黨兼顧民眾的宗教訴求和世俗訴求,旨在廣泛動員民眾、爭奪選票和競選議會席位,其競選綱領和施政理念在諸多領域與世俗政黨可謂異曲同工。進入新世紀,正義與發展黨異軍突起,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和現代化進程經歷了繼凱末爾時代之后的第二次飛躍。
現代伊斯蘭主義既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亦非渾然一體和靜止不變,而是與特定的政治環境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政治內涵千差萬別。剖析現代化進程中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環境不盡相同,政治民主化進程參差不齊,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實踐在靜態的層面包含激進與溫和的不同模式,在動態的層面經歷從激進到溫和的轉變過程,表現各異。另一方面,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環境的寬松與伊斯蘭主義的溫和傾向表現為同步的趨勢,三者之間具有明顯的內在邏輯聯系。現代伊斯蘭主義的廣泛政治實踐,無疑是構建公民社會、活躍選舉政治、完善政黨政治和擴大自下而上之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催化劑,與現代民主政治一樣都表現出明顯的同質性和兼容性,可謂推動中東伊斯蘭世界民主化進程的有力杠桿。致力于多黨制基礎上的議會選舉進而實現推動民主化進程的政治理念,則是現代伊斯蘭主義之政治實踐的主流發展方向。
結論
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的錯綜交織普遍存在于現代化進程啟動以來的中東伊斯蘭世界,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的激烈博弈對于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走向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在20世紀后期直至世紀之交的中東伊斯蘭世界,挑戰威權統治和推動政治改革的呼聲,往往并非來自世俗陣營,而是來自現代伊斯蘭主義陣營,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就埃及和土耳其而言,現代伊斯蘭主義者通常來自世俗領域,具有世俗教育背景,以世俗知識界人士作為中堅力量,代表新興中產階級和社會下層民眾的政治訴求;現代伊斯蘭主義者并非等同于伊斯蘭教神職人員抑或宗教學者歐萊瑪,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實踐亦非以建立教法至上和宗教學者歐萊瑪主導的神權國家作為最終目標,相比之下,伊斯蘭教神職人員抑或宗教學者歐萊瑪大都長期游離于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之外,無意謀求政治權力,且與官方保持密切的聯系,持相對保守的政治立場。就伊朗而言,伊斯蘭共和國實行法基赫制,賦予教法學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廣泛的政治權力。然而,究其原因,所謂教法學家的統治并非在于什葉派的神學思想和教派特質,而是在于伊斯蘭革命期間伊朗特定的政治環境,可謂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特例。阿里·沙里亞蒂作為伊朗什葉派現代伊斯蘭主義的先驅,并非具有歐萊瑪的宗教身份,卻有留學西方的教育背景,深受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的影響。霍梅尼早年盡管倡導宗教學者參與國家事務,卻并不主張實行教法學家直接統治下的國家體制。伊斯蘭革命后的30余年間,即便在什葉派歐萊瑪內部,亦存在明顯的政治分歧,阿亞圖拉蒙塔澤里公開質疑現行法基赫制的合法性,可謂最具影響力的持不同政見者。選舉政治的常態化和民主化,則進一步挑戰著現行法基赫制的政治權威。
此外,在土耳其和伊朗,官方曾經對于女性的服飾予以頗為嚴格的限制。在土耳其共和國,自凱末爾時代開始實行的世俗化舉措之一,是官方通過立法的形式,嚴格禁止女性披帶具有伊斯蘭教傳統色彩的頭巾。無獨有偶,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霍梅尼時代實行的伊斯蘭化舉措之重要內容是官方強制女性披帶具有伊斯蘭教傳統色彩的頭巾。公民權是現代文明的社會基礎,自由則是公民權的基本要素,亦是現代文明之區別于傳統文明的重要標志,而服飾自由構成公民自由的組成部分。官方對于女性服飾的清規戒律,無論是土耳其共和國之禁止女性披帶頭巾抑或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強制女性披帶頭巾,皆屬剝奪女性的服飾自由權,進而侵犯女性之公民權,與現代文明之公民自由相去甚遠,而所謂世俗化與民主化之非等同性,亦由此可見一斑。進入世紀之交,在土耳其共和國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官方關于女性服飾的禁令引發民眾的廣泛關注,解除服飾禁令和爭取服飾自由成為女權運動的強烈訴求,而女權運動的高漲反映出民眾政治參與程度的提高和民主化的長足進步,代表著現代文明的歷史發展方向。
(責任編輯:郭丹彤)
2016-09-01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東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編號:12BSS014)。
哈全安(1961-),男,吉林市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A
1674-6201(2016)03-0048-11